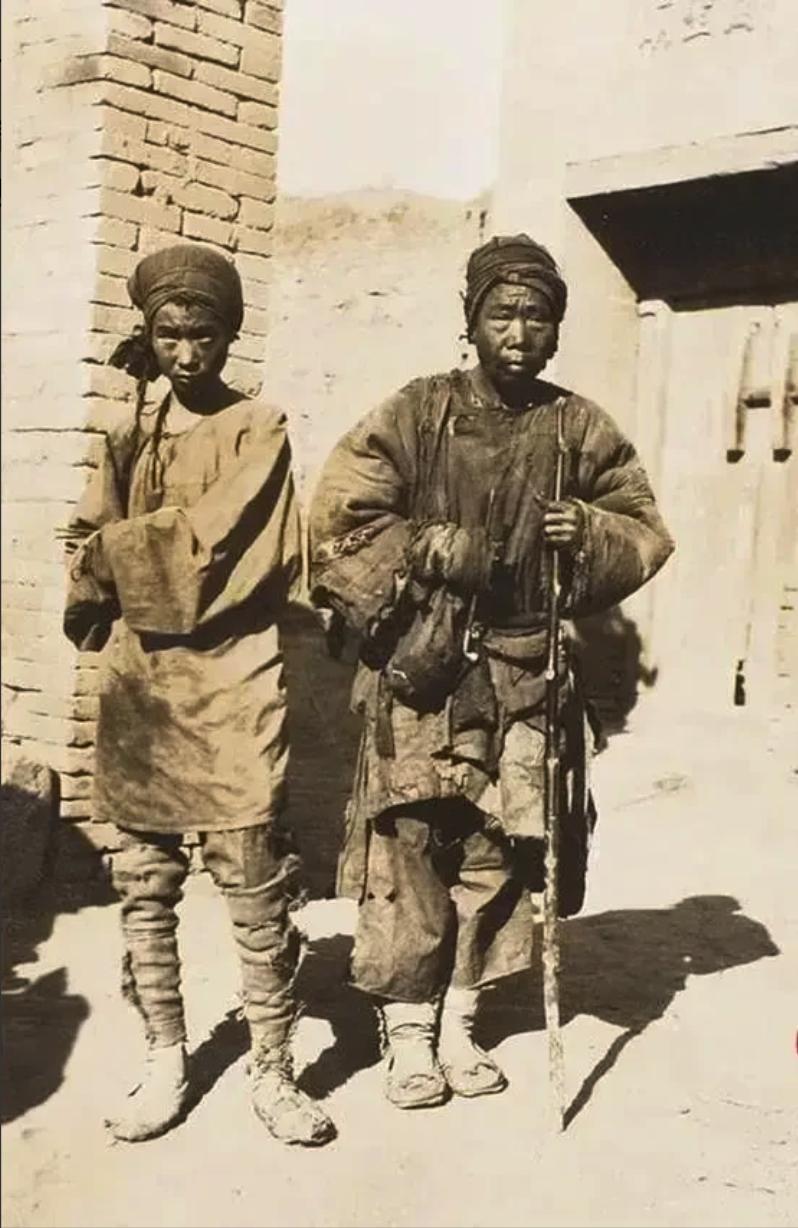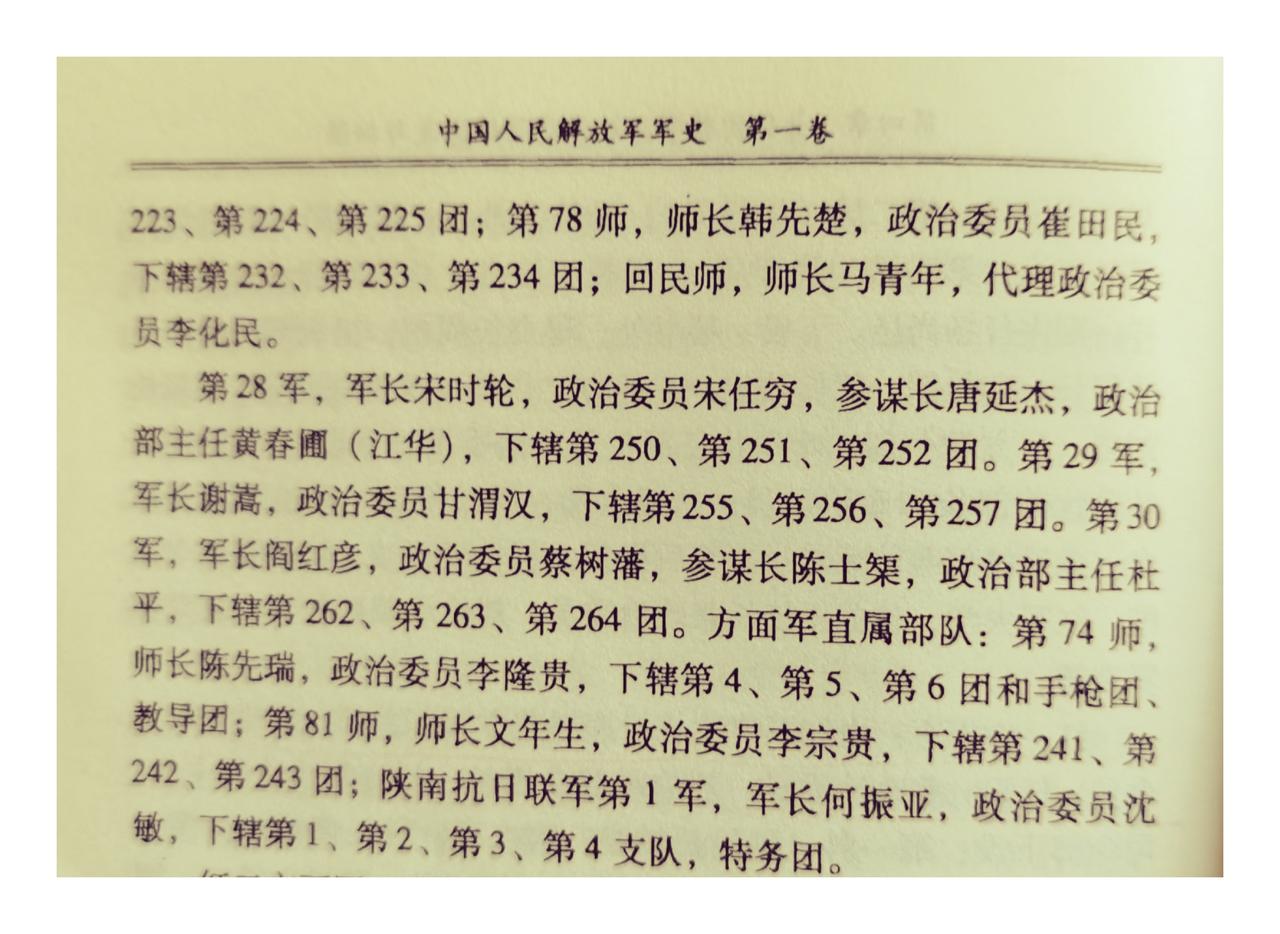萧向荣去国防科委任职,妻子:军科院更适合!张爱萍后来很内疚! “老萧,这回真要你在两个地方之间下决定了。”——1975年3月,北京玉泉山,一通深夜电话在安静的营房里划开了口子。 当时的张爱萍刚刚复出不到一年,身兼副总长与国防科委主任。电话另一端的萧向荣沉默片刻,只简单应了一声“好”。挂断后,他把时间写进日记:凌晨一点三十五分。 新中国成立后,萧向荣在中央军委办公厅一干就是十五年。文件堆、首长会、军委例行简报,样样离不开他。1959年升任副秘书长,仍兼办公厅主任。那几年,军委系统的很多规范就是在他手里落笔定稿。 1965年,他被卷入漩涡。两份批判材料、三次群众大会之后,临时通知下达:离岗。萧向荣没再踏进办公厅大门,外界消息也被隔绝。直到1972年秋,警卫员把放行条递到手里,他才算“自由人”。 1975年1月,总政发来任命:军事科学院副政委。消息传开,老部下说“终于等到您”。萧向荣摆摆手:“哪儿需要,就去哪儿。”此刻,他并不知道这道任命只是序章。 农历二月初,总政干部部又派人登门:“张副总长建议您去国防科委。”一句“建议”实则已成定论,级别不动,岗位换了。军科院偏学术,国防科委则直面尖端武器与体制矛盾,两种环境天差地别。 妻子耿绍兰听完,脱口而出:“军科院更适合,你那身书卷气,放在科委不顶用。”她了解丈夫——性子直,遇到不合理就要掰扯。萧向荣却笑了笑:“机关老兵,还挑阵地?”话虽轻松,眉间并未舒展。 三月初,他到中关村东路报到。接待干事递上门牌:“副主任,暂借三楼小办公室。”楼里气氛紧绷,七机部的派性冲突每天在走廊里发酵。张爱萍索性把指挥部搬到现场,白天调度科研进度,夜里整理材料。 萧向荣的工作方法仍是“磨”,先摸底,再召集对立双方对话。前三周效果不错,几项停摆方案重新启动。有意思的是,技术人员对这位“老秘书”颇为信服,觉得他说话不夹官腔。 然而五月下旬,风向突然改变。两张大字报贴在科委礼堂门口,指名道姓。次日,外单位串联人员进楼对质,场面一度失控。张爱萍被堵在办公室里五小时。萧向荣赶来协调,人群却越聚越多。 6月2日深夜,张爱萍打电话劝他暂时别来:“局面已超出技术范畴,他们要的不是解释。”对方只回一句:“会议定了,就得去。” 第二天清晨,他照常进楼。九点半,造反小组要求他写检查。他写了三页,字迹依旧工整。十一点左右,胸口剧痛袭来,急救车把他送进总医院。抢救四小时,终因急性心梗离世,时年六十三岁。 噩耗传到国防科委指挥室,张爱萍拍案而起,嘶吼一句:“让他别去,他偏去!”随后陷入长久的沉默。后来每逢谈起老同事,张爱萍总要停顿,眼圈发红:“是我把他请来的,他替我挡了那一枪。” 事情过后,科委内部有人议论:如果萧向荣留在军科院,或许仍坐在阅览室研究军事史。猜测没有意义,但一个细节被反复提及——那份尚未启用的军科院任命文件,仍静静夹在他最后一本日记里。 萧向荣葬于八宝山,无碑文评功,只刻姓名与生卒。送别当天,老战友私下议论:“老萧不懂拐弯,可他知道什么是职责。”话音不高,却落在每个人心里。 多年后,国防科委改革为新体制部门。有人提议编写口述史,张爱萍第一时间把萧向荣的名字列入。档案馆留存的那份笔记上,夹杂一句手写批注——“做事要有人,讲究要命。” 历史并不浪漫,选择也从不轻盈。那通凌晨电话,两种岗位,一条生命,最终落在石板似的时间刻度上,再无法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