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傅雷跟情人在书房约会,傅雷的妻子突然推门进来。只见她只是轻轻放下两杯茶水,又默默地走了出去。随后在客厅站住,对正在玩耍的儿子说到:“爸爸在忙,别打扰到他。” 傅雷1908年出生在上海南汇一个地主家庭,小时候日子过得还算殷实。可惜好景不长,四岁那年父亲被人诬告入狱,后来病死,家里就剩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对他要求特别严,小时候学私塾,稍不认真就得挨罚。有回他复习功课打瞌睡,母亲直接拿热蜡烫他,疼得他叫出声,邻居都跑来劝。甚至有次为了磨炼他,还把他扔进河里学游泳,差点没上来。这些经历让傅雷从小就养成了凡事追求完美的性格。 长大后,傅雷学习特别优秀,尤其对语言和文学有天赋。1928年,他20岁,去了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和卢浮宫艺术学院学文学和艺术史。那几年,他在巴黎到处跑博物馆、听讲座,还认识了不少文化名人,比如哲学家雅克·马里坦。他特别喜欢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受了很大启发,开始琢磨怎么把法国文学翻译成中文。1931年回国后,他先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了几年艺术史,后来干脆专心翻译。 1932年,傅雷跟表妹朱梅馥结了婚。两人从小就认识,感情基础挺好。婚后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傅聪,次子傅敏。朱梅馥性格温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傅雷才能安心搞翻译。他的翻译可不是随便弄弄,每句都抠得特别细,翻译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些名作,文笔流畅又忠实原意,读者和学者都夸他。到1939年,傅雷在翻译界已经是大咖了,他的作品让中法文化靠得更近。 1939年的一个夏日下午,傅雷在上海家里的书房跟一个叫成家榴的女人见面。这位成家榴是朱梅馥的朋友,职业是歌手,长得挺漂亮,气质也不错。那天她来傅宅,俩人就在书房聊上了。书房是傅雷工作的地方,平时堆满了书和译稿,气氛安静又有点私密。两人聊得挺投入,离得也近,气氛明显不一般。 就在这时候,朱梅馥端着两杯茶推门进来了。她一眼就看到傅雷和成家榴坐一块儿,气氛不对。她没说啥,也没发作,就那么静静地把茶放下,转身走了出去。之后她去了客厅,当时五岁的傅聪正在那儿弹钢琴玩,小儿子傅敏在地上摆木块。她停下来,跟傅聪说爸爸在忙,别去打扰,然后继续收拾东西,像啥也没发生过。 这事儿过后,书房里也没再起波澜。成家榴很快就走了,傅雷一个人留在那儿,盯着桌上的茶杯发呆。那一刻,他估计心里也不平静,但表面上啥也没变。 1939年这事儿之后,傅雷跟成家榴的联系慢慢少了。他把心思又放回翻译上,后来几年陆陆续续翻译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还有罗曼·罗兰的其他作品。他的翻译特别讲究细节,有时候为了一句词儿能琢磨好几天,力求把原作的感觉全带出来。这些作品出来后,反响特别好,不少人说看他的译本就像在读中文原创。 家里这边,傅雷对傅聪管得越来越严。傅聪从小就显出钢琴天赋,傅雷给他找了最好的老师,每天逼着他练好几个小时。有回傅聪偷懒没好好练,傅雷气得拿东西砸他,弄得他鼻子都流血了。傅雷对儿子要求高到不行,不光是技艺,还得品格也得完美。1958年,傅聪去波兰学音乐,后来干脆留在了英国。父子俩靠书信联系,傅雷在信里苦口婆心,教他怎么做人怎么搞艺术。这些信后来整理成了《傅雷家书》,成了好几代人爱读的书。 朱梅馥这边,表面上看还是老样子,管家带娃,默默支持傅雷。她从没拿1939年那事儿出来说过啥,家里也还算平稳。可到了1966年,傅雷和朱梅馥一起走上了绝路,俩人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他们走得让人惋惜,但留下的东西却没被忘了。傅聪后来成了世界有名的钢琴家,尤其擅长弹肖邦,提起父亲总是说影响太深。傅雷的译作和家书也一直在流传,成了不少人精神上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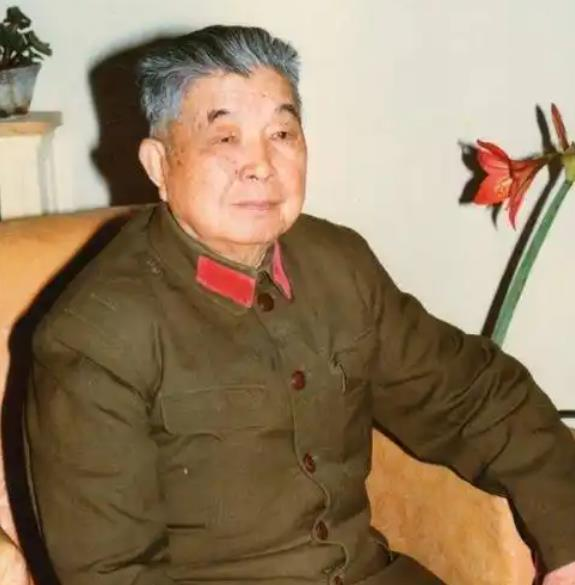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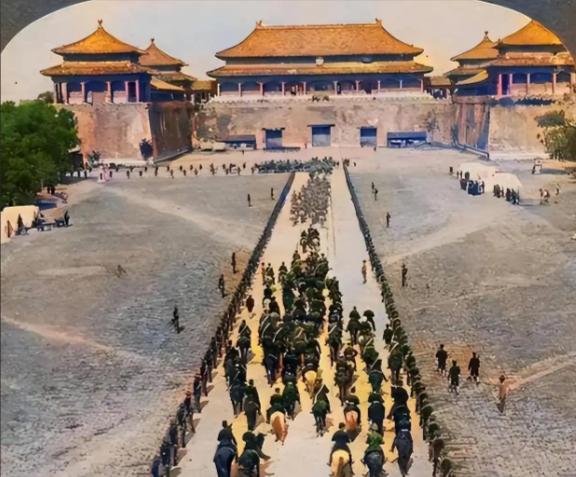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