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9年,被人民解放军打败的国民党军队,这些国军的女兵正在吃她们在大陆的最后一顿饭,饭后她们就要跨过台湾海峡前往台湾岛。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张桂兰出生在鲁南一个小村子,村里人都说她手巧,能一针一线绣出花来,她的母亲常说,姑娘家的活计要从小练,哪怕将来不种地,也要有点拿得出手的本事,张桂兰记住了这话,十三岁那年就能绣出一整幅牡丹,她最喜欢在黄昏时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针线,边绣边哼小曲,那时候她从没想过,这只绣花针会被她带进部队,也从没想过,会在炮火连天的战地医院里,用它缝补沾了血的制服。 她不是自愿参军的,那年春天,征兵队进村,说是招“女青年”,说得好听,像是去当护士、当文书,张桂兰想着能穿上制服,见见外面的世界,也算长见识,她没多想,跟着就走了,第一站是济南,从家走的那天,她偷偷把那根绣花针藏在了鞋底下,她不敢让家人知道她带了它,怕母亲哭。 部队生活远没有她想象中光鲜,她被分去做卫生兵,背着医药箱在阵地间跑,炮弹在头顶炸响,泥土和血混在一起,常常一天下来,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她开始后悔,也想过逃,但每次从包里翻出那根针,心里就多了一点坚持,那是她唯一的故乡记忆,也是她那个世界里最后的温柔。 1949年秋,战局越来越紧,张桂兰跟着部队一路南撤,他们从安徽到江西,又从江西走到福建,每一段路都有人掉队,每一个夜晚都听得见哭声,她的鞋底磨穿了三层,绣花针却一直没丢,她用它补衣服、缝行李袋,甚至在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一夜,还绣了一朵莲花在手绢角上,那是她唯一一次,主动提起针线。 离开大陆的前一天,张桂兰坐在营地的木板凳上,手里捧着军营发的铝饭碗,碗里是稀饭和一点咸菜,热气冒得厉害,她却没动筷子,她知道,这是在家土里吃的最后一顿饭,那只饭碗她舍不得扔,登船的时候偷偷装进了包袱,后来在台湾的眷村里,她每天还是用它吃饭,时间久了,碗边起了裂纹,颜色也变了,但她从不换,她说,这碗里盛过的是故乡的米,有家味。 张桂兰不是一个人上船的,身边还有很多女兵,有的比她年纪小,有的已经做了母亲,她们都带着各自的行李,有的人把嫁妆背在身上,有的人只带了一本书,船出发的时候,天开始下雨,码头上乱作一团,叫喊声、脚步声、汽笛声混在一起,她站在甲板上,背对着大陆,望着海面出神,她没回头,怕一回头就不敢走了,那一刻,她心里很清楚,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 到台湾后,张桂兰被分派到一个军医院,继续做护士,医院建在山坡上,四周是芒草和铁皮房,她住在一个小间里,屋顶下雨就漏,墙上贴着用旧报纸糊的补丁,她把绣花针藏在抽屉最里面,偶尔拿出来看看,就像看看自己从前的影子,饭碗被她小心地洗干净摆在床头,照片则夹在一本旧书里,那张照片是她十八岁参军前拍的,穿着村里的粗布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睛里还有光。 那些年,她试过写信回家,信地址是老家的村名加上乡里的邮政所,她不知道父母还在不在,也不知道信有没有人收,每次寄出去一封,她就盼一个月,有时两个月,有时更久,可从没收到过回信,后来,她慢慢停了,她说,也许家早就没了。 时间过去几十年,张桂兰渐渐老了,她从医院转业,做过小学保健老师,也在眷村里带过邻居的孩子,她没结婚,也没生孩子,她说,太多东西已经留在了那片海的对岸,自己再没多余的力气去重新开始,身边的姐妹一个个老去,有的离世,有的去了美国探亲再没回来,她开始学会一个人过日子,习惯了听广播、种盆栽、泡茶,也习惯了每晚一个人坐着看天黑。 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张桂兰办了手续,一个人坐船回大陆,她拎着一个旧皮箱,箱里装着那只饭碗、那根绣花针和那张泛黄的照片,船靠岸时,她站在甲板上,第一次抬头看向大陆的方向,她以为自己会哭,可眼泪却怎么也流不出来。 她回到老家村子的时候,村口的老槐树没了,村子也换了样,她问了好几个人,没人知道“张桂兰”是谁,她走到村东头,原来家在那边,可现在是一家化肥厂,厂门口水泥地上,她站了很久,一直没找到当年那棵枣树的位置,她蹲下来摸了摸地,说不出话,也找不到家的方向。 那次探亲之后,她再没回过大陆,她说,回去一次就够了,她的饭碗后来摔碎了,洗碗时不小心掉在地上,裂成三瓣,她把碎片用布包起来,埋在了院子角落的竹子旁边,绣花针她放进了相框,和那张老照片一起挂在墙上,每次有人来家里,她就说,那是她年轻时候的自己,是她从大陆带来的全部。 信息来源:央视新闻《1949大迁徙》纪录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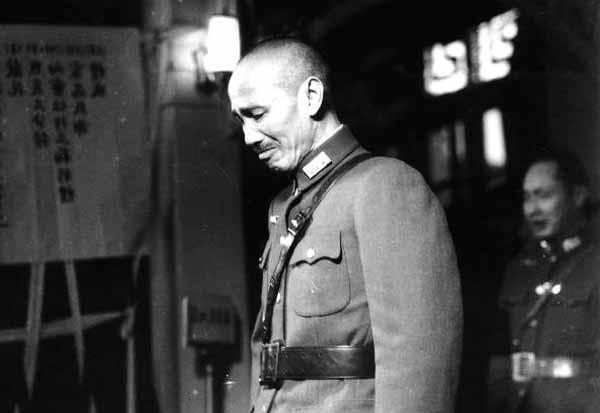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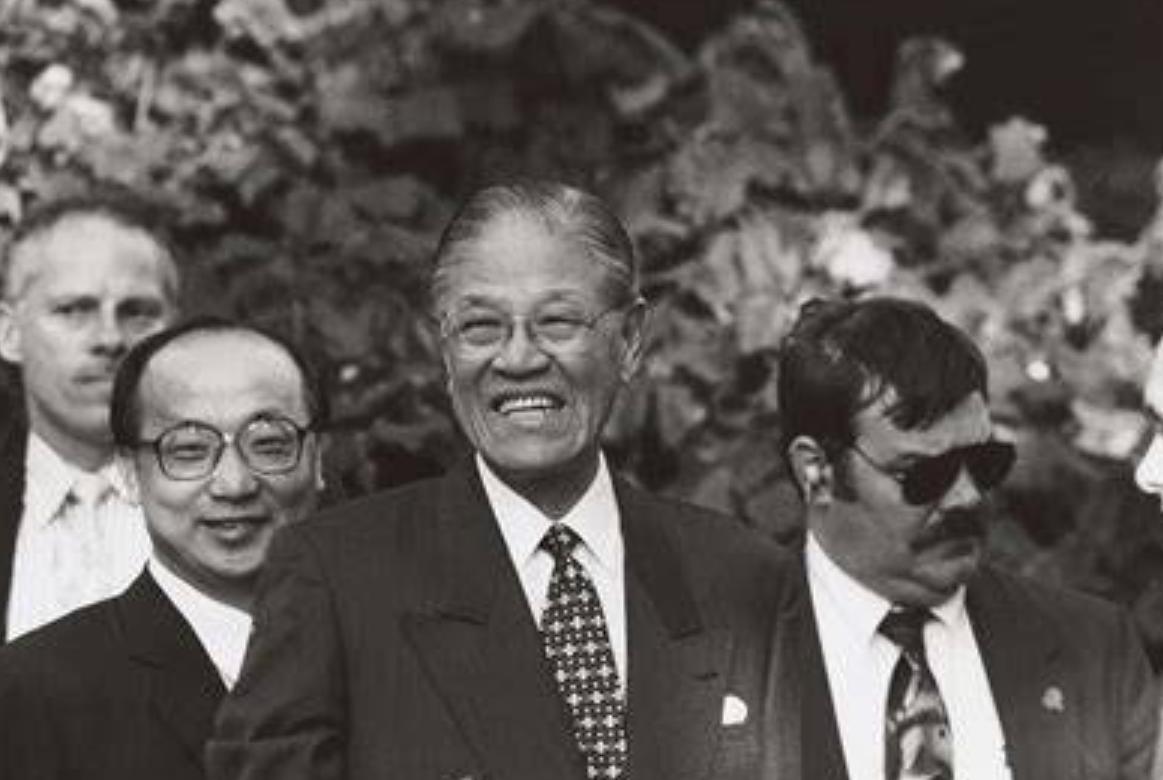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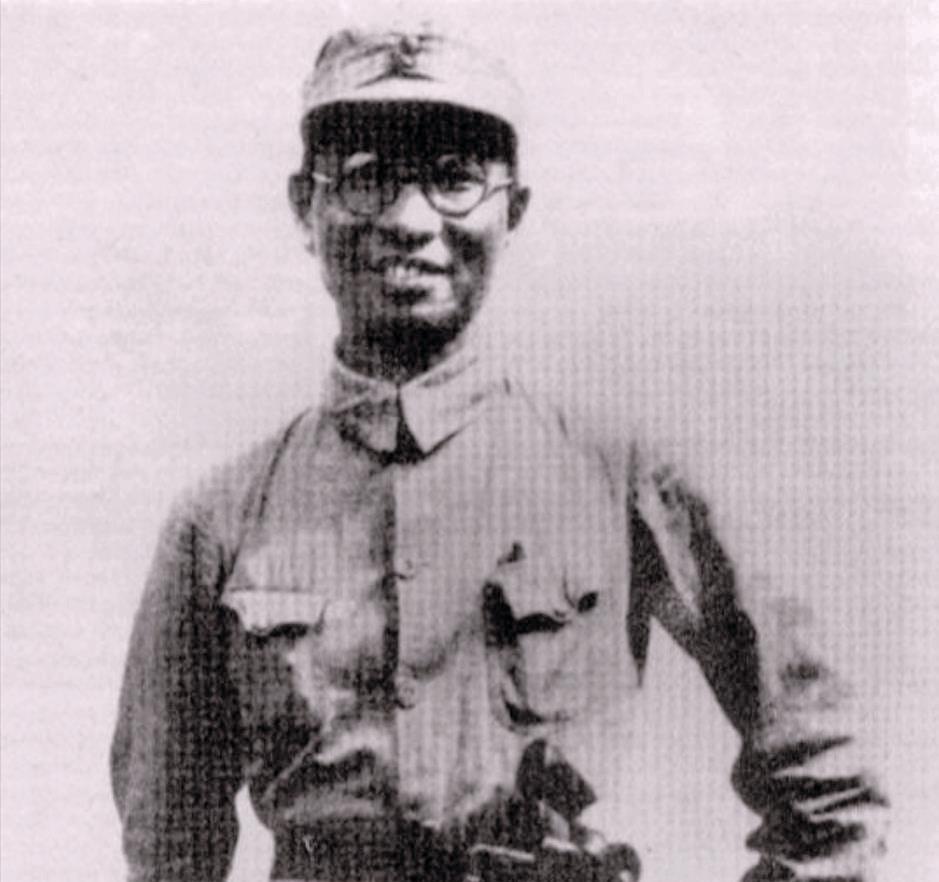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