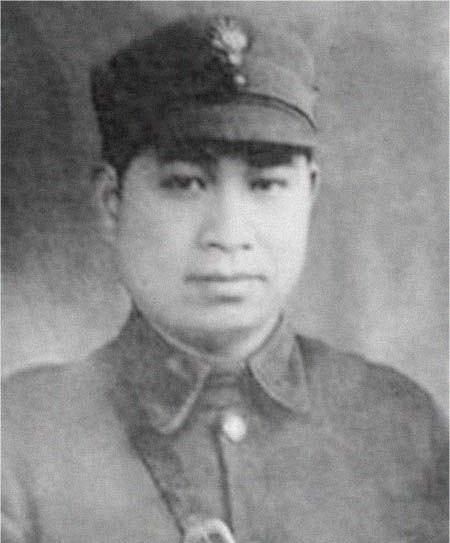1983 年,郑洞国的前妻想复婚,郑洞国的子孙都同意,但郑洞国却摇头拒绝:"她来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十天就被她花掉,不复婚!" 1934 年南京新婚后的第一个月,郑洞国发现抽屉里的军饷不翼而飞。 陈碧莲抱着刚买的西洋座钟笑盈盈地说:"你的饷银换了这钟,以后就不会误了操课时间。" 座钟的铜摆晃出清脆的响,而他放在枕头下的派克钢笔却不见了。 那是古北口战役后军部奖励的战利品。后来他在她的梳妆台抽屉里找到钢笔,笔帽上还沾着法国香水的黏腻,旁边是张未撕掉价格的香水票据,数额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军饷。 1943 年加尔各答的军营里,陈碧莲用空投罐头改造成花瓶,插着野花的罐头旁,是她托人从孟买带回的香水瓶。 郑洞国某次查岗回来,看见她正用香水擦拭手枪套筒,"这样就不会生锈了"。 她拧开瓶盖的动作优雅,而他注意到罐头里的野花上凝着水珠 —— 那是她用饮用水喷的,当时驻印军的淡水配给每天只有半壶。 军需官后来偷偷告诉他,夫人每周都要托运输机带化妆品,运费足够买两箱急救包。 1952 年郑洞国调任水利部参事前,在家收拾行李时,发现衣柜里多了件英国呢料大衣。 陈碧莲说是 "朋友送的",但他在大衣内衬摸到张百货公司的发票,金额相当于他三个月的干部津贴。 那天晚上,他看见她对着镜子试穿大衣,呢料摩擦的沙沙声里,他想起 1945 年收复柳州时。 她非要用缴获的日军罐头换上海来的丝绸旗袍,说 "胜利了要穿得体面",而当时伤员们还在用盐水清洗伤口。 离婚后的陈碧莲嫁给商人钟老板,1953 年的上海报纸曾刊登她出席酒会的照片,她挽着钟老板的手臂,耳垂上的钻石耳钉在闪光灯下晃眼。 郑洞国在水利部的同事指着报纸说:"这不是您前妻吗?" 他默默收起报纸,想起 1950 年家里断粮时,陈碧莲却把单位发的救济米换成了进口巧克力,理由是 "孩子们要吃有营养的"。 而 1962 年她住在亭子间时,邻居看见她把救济金买的蜂窝煤卖掉一半,换了瓶过期的雪花膏,说 "脸不能脏了"。 1983 年郑洞国的工资条上,368 元的数字被他反复看了又看。 这相当于他 1933 年在南京当团长时的两倍军饷,但他记得 1952 年两人最后一次共同生活时,陈碧莲十天内花掉了他一个月的工资 。 三天买了台进口收音机,两天请牌友吃了顿西餐,剩下的钱全买了当时稀罕的奶糖。 "她不是过日子的人。" 他对孙子说这话时,想起 1949 年长春起义后,她把组织发的棉衣拿去典当,换了条狐皮围巾,说 "干部服配狐皮才好看"。 政协老同事后来告诉郑洞国,陈碧莲在弄堂里常说 "郑先生的工资够花"。 但他知道,1983 年的 368 元要负担保姆费、医药费和孙辈的学费,而陈碧莲 1953 年离婚时带走的那只翡翠镯子,1980 年代初在上海拍卖行能拍出天价,她却宁愿变卖首饰也不愿节省。 当孙子拿出陈碧莲的求助信,信里写着 "每月八块救济金不够买煤",他却在信笺背面发现隐约的香水印 —— 那是他熟悉的法国牌子,1934 年她用过的同一款。 郑洞国最终没同意复婚,却偷偷给陈碧莲安排了文史馆的工作。 42 元的月薪足够买蜂窝煤,却不够买一瓶好香水。他在汇款单附言里写 "省着用",想起 1934 年送她玉镯时,工匠说 "翡翠能压箱底,日子要精打细算"。 而陈碧莲收到第一笔工资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理发店烫了头发,花掉了半个月的薪水,理发师说她 "还是有当年官太太的派头"。 1986 年陈碧莲拿到文史馆员聘书那天,特意戴上了那只玉镯。镯子内侧的刻字 "洞国赠" 已被岁月磨平,却在阳光下映出奇妙的光斑。 像极了 1943 年加尔各答机场,她带来的香水瓶碎在地上时,阳光透过玻璃碴子洒在他军靴上的样子。 而郑洞国直到 1991 年去世,抽屉里始终锁着张 1952 年的购物清单,上面记录着陈碧莲十天内花掉的 342 元,数字旁用红笔打了个叉,像极了他在战场上标记 "危险地带" 的符号。 当郑洞国的孙子整理遗物时,发现爷爷夹在《我的戎马生涯》里的一张便签,上面写着:"她要的是香水瓶,我只有军用水壶。" 便签纸的边缘,有几滴模糊的水渍,像极了 1983 年那个春天,他看完复婚信后,悄悄擦掉的眼泪。 而上海弄堂里的陈碧莲,直到晚年还在对邻居念叨:"他当年的军饷,够买好多香水呢。" 她没说的是,1953 年离婚时,她藏在箱底的,除了首饰,还有郑洞国 1943 年在印度写给她的信,信里说:"等打完仗,我用军饷给你买一屋子香水。" 参考来源:人民出版社《郑洞国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