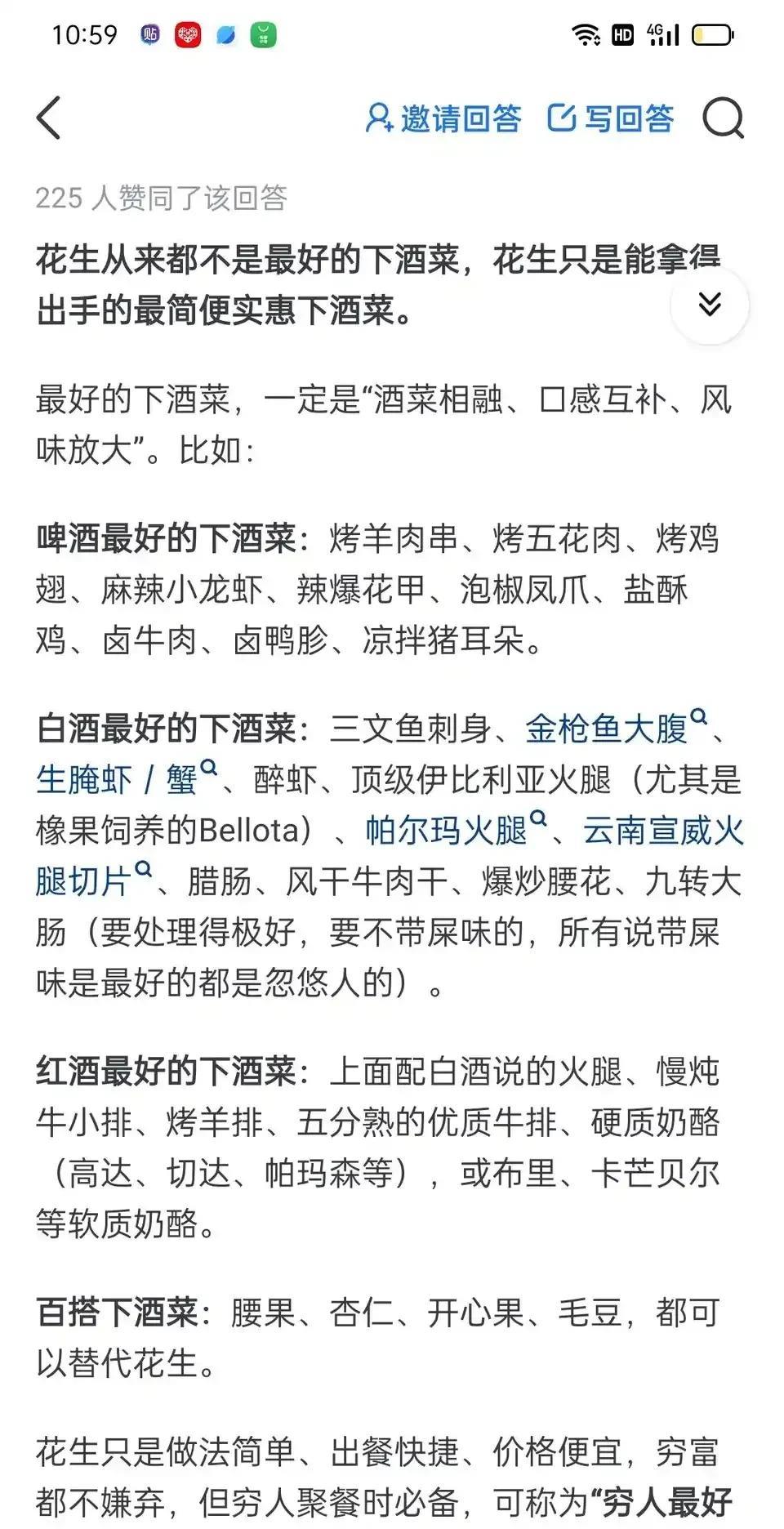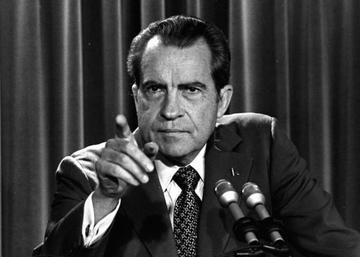二战美军最痛恨的就是午餐肉,这主要是因为午餐肉最开始是碎肉,后面不停的增加猪油和淀粉,到战争快结束时已经变成了边角肉、内脏、猪油、淀粉和大豆的混合物,虽然量大脂肪蛋白管够,但美军士兵可看不上。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二战的战地回忆里,有一种罐头几乎随处可见,它跟着军舰跨越海洋,堆在前线补给仓库的木箱里,也出现在野战厨房和壕沟的餐桌上,它方方正正,粉色发亮,打开就能吃,看似是士兵的福音,却在美军中名声狼藉。 对于很多身经百战的士兵来说,子弹和炮火不足为惧,最让人皱眉的,是一日三餐里那块油腻腻的午餐肉。 它的故事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时美国深陷经济大萧条,猪肉销售滞缓,屠宰场和加工厂里堆满了没人要的猪肩和火腿边角料,为了处理这些库存,一家名为荷美尔的公司将这些碎肉与土豆淀粉、盐混合,加工成肉糜压入金属罐中,并用亚硝酸钠保持诱人的粉红色。 它的售价只有新鲜肉类的三分之一,在许多人连一口荤腥都难得吃上的年代,这种便宜、耐放的肉罐头迅速赢得了市场,最初的配方里肉含量不低,切开还能看到明显的肉纤维,入口虽称不上精致,但在贫民家餐桌上已算是奢侈。 战争爆发后,它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对军方来说,这种罐头的优势显而易见,不需冷藏,保质期长达数年,热量充足,运输方便,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入全球战局,数百万士兵被派往太平洋岛屿、北非沙漠和欧洲严寒地带,如何稳定供应肉类成了后勤难题。 午餐肉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成为军粮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军大量订购,生产线昼夜运转,成批的肉罐头被装上火车和轮船,送往各个战区。 在战争初期,士兵们对这种罐头并无太多怨言,和单调的硬饼干、干咸鱼相比,它至少柔软、易食,还带着点肉香,然而当采购数量急剧上升、原料供应吃紧时,产品质量开始下降。 为了压低成本、满足庞大的需求,生产商减少了猪肉比例,加入更多猪油、动物内脏和淀粉,甚至掺入大豆等填充物。 到了战争后期,罐头里的“肉砖”已与最初大相径庭,切开后油脂泛光,结构松散,偶尔还能见到不规则的颗粒,味道也愈发单一而厚重,咸味掩盖了肉香,口感黏滞,咀嚼间带着糊嘴的粉感。 士兵们与它的关系由勉强接受转为厌倦,再发展到彻底反感,前线饮食条件有限,早餐、午餐、晚餐几乎都离不开它,无论是煎、煮、炖,还是夹在面包里,都难以摆脱油腻和单调。 有人干脆把罐头换给当地人,以换取水果或其他食材,也有人用它当作鞋油,涂在皮靴上防水,即便在饥饿时能充饥,它带来的满足感也被腻味抵消,久而久之,这种罐头成了军营里最不受欢迎的口粮。 同一批午餐肉在别的地方却是另一番光景,彼时的英国长期遭受海上封锁,肉类供应极其紧张,普通家庭一年中能吃到肉的次数屈指可数,节日期间开上一罐来自美国的午餐肉,配上土豆和蔬菜,足以让一家人觉得丰盛。 在苏联前线,它更是救命的存在。德军占领乌克兰粮仓后,食物匮乏到极点,美国援助的肉罐头成为红军维持体力的关键口粮,士兵会将它薄薄切片,铺在粗糙的黑面包上,配以少许盐直接入口。 在战后的朝鲜半岛,百废待兴、百姓贫困,不少人从美军废弃物中翻出过期的午餐肉,加上泡菜、辣椒煮成锅,渐渐演变成当地流行的部队锅。 这种反差耐人寻味,在资源稀缺的国家,这种罐头象征着珍贵的营养与节日的气氛,在供应充足、选择多样的美军后勤系统中,它却沦为士兵抱怨的对象。 美国的工业能力,使他们在全球战场上保持持续供应,也让士兵有了挑食的余地,别国士兵为一口带油花的肉感到幸福,美国士兵却因为天天面对它而意兴阑珊。 午餐肉的味道并没有改变战争的走向,但它背后的生产和运输能力,却在战争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能在短时间内制造并运送数以亿计的罐头食品,体现的是庞大的工业体系与高效的后勤调度。 这种力量不仅养活了前线,也支撑了盟友,成为战争胜利中不为人熟知的基石,战争结束后,它在美国本土的形象逐渐转向廉价食品,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却留下了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从夏威夷的午餐肉饭团到韩国的辣汤火锅,它在和平年代找到了新的位置,也在记忆中留下复杂的味道,既是饱腹的象征,也是那个时代物资不平衡的注脚。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界面新闻——午餐肉借二战成就传奇 盟军士兵居然用来擦枪


![这算贵吗?一个人的晚餐[并不简单]](http://image.uczzd.cn/17344293272614545446.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