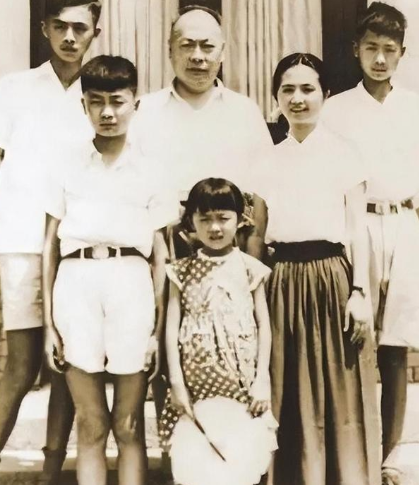1974年,知青李根生返城。父亲说:"我已再婚,给你20元,别再回城!"李根生含泪告别父亲。没料到,16年后,李根生却对父亲说:"感谢你当年的决定。”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云南户拉傣族村寨迎来一批知识青年。
有个叫李根生的昆明小伙,背着半旧的帆布包站在竹楼前。
他脚上的解放鞋沾满红泥,裤腿还留着火车上蹭的煤灰印子,这个场景成为他往后二十多年扎根边疆的起点。
事情要从五年前说起,那年李根生刚满十八,在昆明读完初中。
他父亲是纺织厂锅炉工,母亲早逝,继母带着女儿嫁过来后,家里总飘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
有天李根生看见继妹碗里卧着荷包蛋,自己碗里只有腌菜汤,就明白该往哪儿去了。
1969年冬天特别冷,火车站月台上挤满戴大红花的年轻人。
李根生揣着父亲塞给他的搪瓷缸,那是家里唯一像样的物件,跟着队伍来到滇南边陲。
同来的知青里有个叫玉罕的傣族姑娘,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在村寨的第五年,李根生收到父亲来信。
信纸皱巴巴的,像是沾过水渍,信里说继母又生了弟弟,家里实在住不下,让他暂时别回城。
信封里夹着两张十元纸币,被汗浸得发软。
那天李根生在橡胶林里蹲到天黑,工装裤膝盖处洇湿两大片。
1976年,公社书记看中李根生能写会算,调他去邮电所当学徒。
玉罕也因为"知青家属"的身份,被安排到公路养护队。
小两口住在养护队值班室,竹板床挨着养路机械配件柜,夜里能听见老鼠啃麻袋的声响。
日子像澜沧江水般流淌,1985年邮电所改制,李根生凭着十几年勤勉当上副所长。
玉罕也成了养护队里公认的"铁娘子",能扛着十字镐连续工作八小时。
他们在寨子西头盖起三间瓦房,房前种着玉罕从山里移来的野兰花。
1990年开春,玉罕收拾行李时翻出个蓝布包。
里头整整齐齐叠着二十张汇款单,最早那张日期是1975年3月。
原来这些年李根生按月往昆明寄钱,金额从五块慢慢涨到二十块。
玉罕这才知道,丈夫每年春节都往北方磕三个头。
清明前夕,夫妻俩踏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
玉罕特意换上节日才穿的绣花筒裙,背篓里装着酸笋、普洱茶和野生天麻。
列车穿过横断山脉时,她发现丈夫总盯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电线杆,那些都是他们养护过的线路。
昆明城比记忆里拥挤许多,老纺织厂宿舍拆了大半,几经打听才在城郊找到父亲。
老人独居在十平米的杂物间,墙上还贴着李根生小学时的奖状。
玉罕二话不说开始收拾锅碗瓢盆,李根生蹲在地上给父亲穿新布鞋,鞋底纳得厚实,最适合走石板路。
回程的列车上,老人摸着儿媳准备的棉褥子,说起多年前的往事。
原来当年那封绝情信,是继母逼着写的。
老头儿偷偷跑过三次火车站,想看看儿子回来没有,有回被雨淋得高烧三天。
李根生握紧父亲树皮似的手,窗外的梯田正泛着新绿。
如今在户拉寨,人们常见到这样的画面:退休的老所长带着父亲巡线,八旬老人拄着竹杖走在前面,时不时弯腰捡起路上的碎石子。
玉罕跟在后面抿嘴笑,筒裙上的银饰叮当作响。
寨子口的界碑重新刷过漆,那抹红色在亚热带阳光里格外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