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前,姑父赌光了家底,跪着向我妈借了3000块,揣着钱去了包头。 刚到包头
二十八年前,姑父赌光了家底,跪着向我妈借了3000块,揣着钱去了包头。
刚到包头那阵子,姑父揣着那3000块钱,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蹲了三天。看着窗外人来人往,他把钱缝在内裤里,夜里睡觉都攥着拳头。听说倒腾烟酒能赚钱,他揣着500块去批发市场,结果被人用三箱假茅台坑得血本无归。那天晚上他在黄河边坐了一宿,棉鞋冻成了冰疙瘩,愣是没掉一滴泪——男人的眼泪,早在跪着借钱时流干了。
"要不说人得逼到绝路呢?"后来姑父总拿这事当笑话讲,"当时兜里就剩俩钢镚,买了个烤红薯揣怀里,走着走着闻着一股香味儿。"那是家卖羊杂的小店,老板正往锅里扔辣油,滋啦一声把姑父馋得直咽口水。他一拍大腿:"老子别的不会,调味可是祖传的!"
第二天一早,姑父用仅剩的钱买了口铁锅,在菜市场角落支起摊子。没有招牌,就挂块木板写着"安徽风味辣油饼"。他揉面时总使着赌钱时的狠劲,"啪嗒"把面团摔在案板上,惊得旁边卖豆腐的大妈直捂心口。没想到这股子野劲儿揉出来的饼,外酥里嫩,加上他秘制的辣油,竟真有人排队买。
有回城管突击检查,姑父抱着铁锅就跑,慌不择路冲进死胡同。眼看就要被逮住,墙根下蹲着的流浪汉突然起身,指了指旁边的狗洞。姑父二话不说,连人带锅钻了过去,膝盖磕出老大一块青。后来他每天收摊,总会给那流浪汉留两个热饼,看着对方狼吞虎咽,"慢点吃,不够还有"。
那年冬天特别冷,姑父的饼摊前支起了小煤炉。有个穿校服的小姑娘每天放学都来,站在炉边烤半天手,却从不买饼。姑父瞅见她冻得通红的耳朵,塞给她个刚出炉的糖饼:"吃吧,不要钱。"小姑娘咬着饼,眼泪吧嗒掉在雪地里,说她爸生病住院,妈妈在医院陪护,家里没人给她做饭。姑父心里一揪,第二天开始,每天给小姑娘留两个菜饼,用塑料袋层层裹好。
开春后,小姑娘的爸爸来道谢,原来是附近中学的校长。他非要给姑父在学校食堂谋个差事,姑父摆摆手:"我这人手脏,怕教坏孩子."校长叹着气走了,没过几天,却带了十几个老师来买饼,说"这饼里有股过日子的实在劲儿"。
生意渐渐好起来,姑父租了个小门面,把姑姑和表哥接了过来。姑姑第一次见他时,差点没认出来——原先油头粉面的赌徒,黑瘦得像根晒焦的柴火棍,手上全是裂口,却笑得露出白牙。表哥半夜起夜,看见姑父在灯下给人写信,凑近一看,是给我妈寄钱,汇款单附言写着"嫂子,这钱您收着,当年那3000块,我十倍还您"。
现在姑父的"安徽辣油饼"开成了连锁,在包头有五家店。去年我去考察,发现每个店门口都贴着张红纸,上面写着"学生党半价,环卫工人免费"。有个戴眼镜的小伙正在排队,说是当年那个小姑娘的同学,"我妈说当年要不是这饼,她可能就辍学了"。
姑父今年六十了,还是每天五点起床揉面。有回电视台来采访,记者问他成功秘诀,他正往油锅里扔饼,油星子溅了满脸:"哪有啥秘诀?就像这饼,得慢慢煎,火急了就糊。人也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别老想着抄近道。"说着他捞起金黄的油饼,朝镜头比了个"吃"的手势,活像个老顽童。
去年冬天我陪姑父回了趟老家,他非拉着我去村头的老槐树下。当年他就是在这跪着给我妈磕头借钱,如今他蹲在树根旁,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十沓钱。"这是三万,你帮我给村里修条路,就叫'回头路'。"他拍着树干嘿嘿笑,"人这辈子,谁还没走错过路?关键是知道回头,知道哪条路能走到底。"
夕阳把姑父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突然想起他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当年那3000块,不是借我的钱,是借我的魂。人活一辈子,丢啥不能丢魂,丢了魂,就真成孤魂野鬼了。"如今看着他腰杆笔直的样子,活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是啊,他打赢了最难的仗,那就是和自己的心魔打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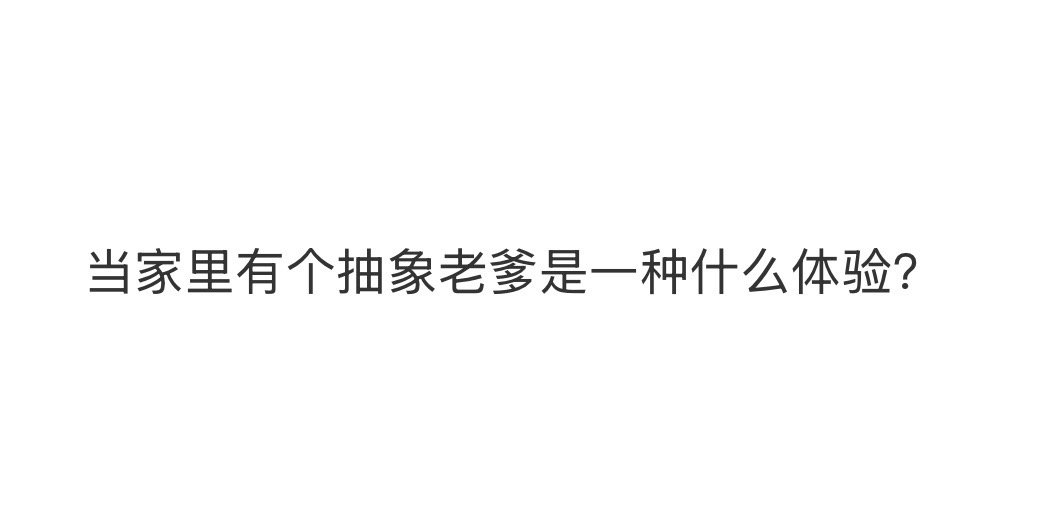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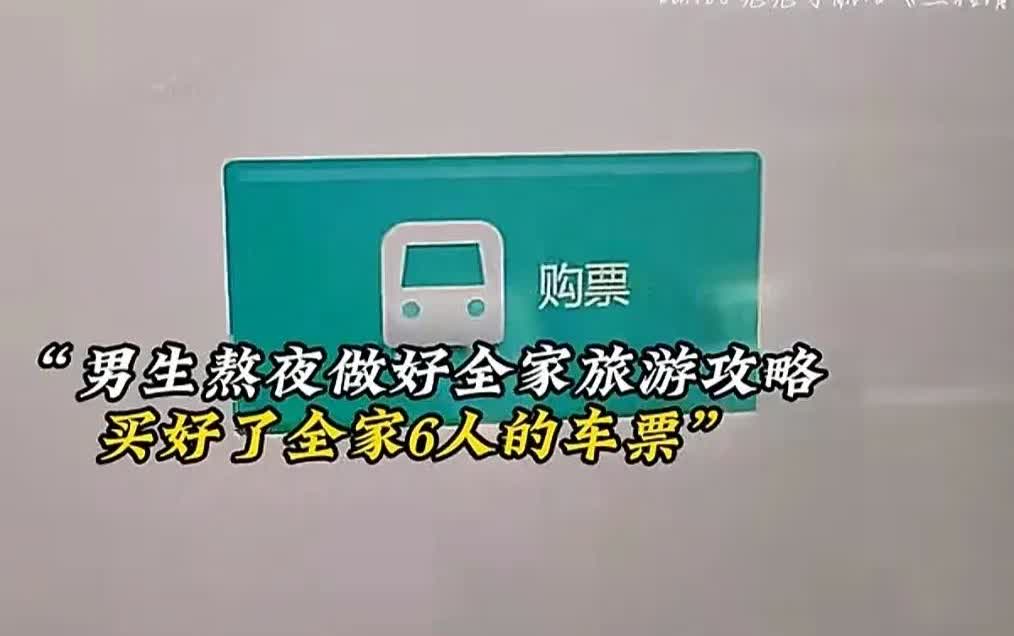

![原来鸡窝里只要有一只母鸡不规矩,整窝母鸡都得杀掉,又涨知识了[666]](http://image.uczzd.cn/2106924719343801245.jpg?id=0)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