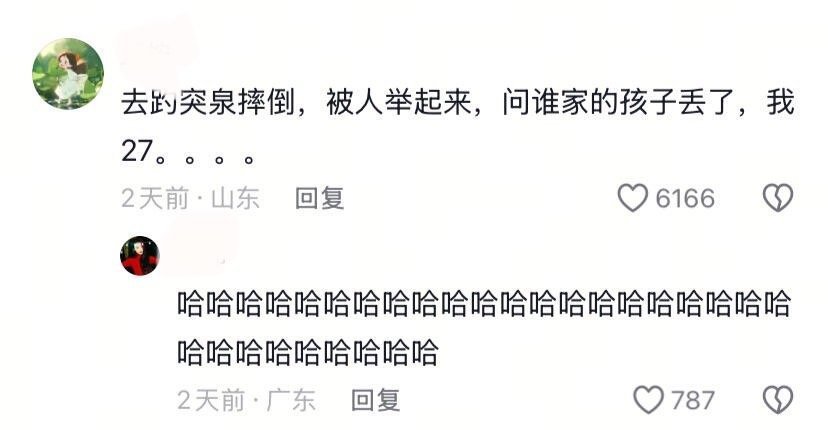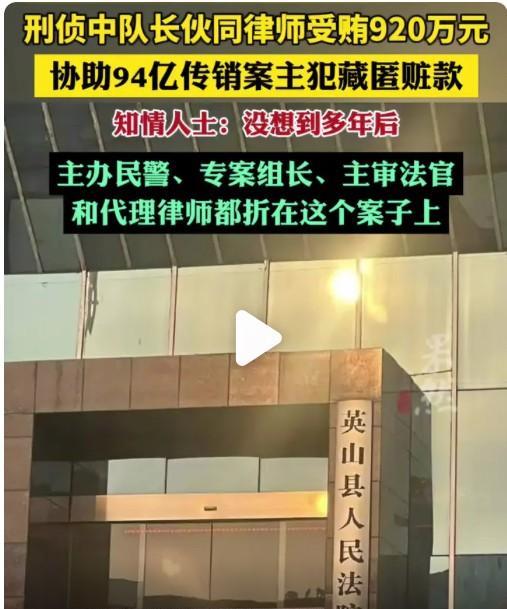【南都快评:#拐卖案应买卖同罪#,修法探讨无碍个案突破】#期待立法推进实现拐卖案买卖同罪#“山东入室抢婴案”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检察院认定,该案中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刘某强夫妇,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但因已过追诉时效,决定对二人不起诉。7月18日,被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们对此结果不服,已向检察院提交申诉。
极端恶劣的“入室抢婴案”,拐卖儿童的众犯得到法律严惩,而让被害人家属难以接受的是买家被认定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但因已过追诉时效而决定对其不起诉。“买卖同罪”一直是拐卖儿童案件中被害人家属的共同诉求,而在本案中更因为“入室抢婴”的恶劣情节,使得买家法律责任的追究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首先,拐卖案中的买家责任同样应当被追究,在法理层面并不存在争议,刑法第241条明确,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即便是“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也只是“可以从轻处罚”。但在具体实践中,因为买家所涉犯罪法定最高刑仅有3年,相应其追诉时效法定仅有5年。在众多寻亲个案中,往往因为持续时间较长导致买家法律责任无法被追究。基于此,不乏法律界人士屡屡呼吁提高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法定刑,以解决对其追诉时效较短的问题,这当然呼应了社会层面希望“买卖同罪”的呼声。
但事实上,从根本上修法的社会推动,与个案层面的司法努力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完全可以同步进行。毕竟,借由个案热点而引发的修法讨论,即便效率再高也已经无法溯及此时个案正义的实现。
特别是在本案中,被害人家属一方有证据指向买家还“部分参与拐卖行为”,而且刑法对追诉时效的延长也有明确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对照本案细节(甚至更多类似案件的情况)可以看到,买家在收买被拐卖儿童后,会采取一定的措施以洗白身份。儿童被拐卖的案件发生,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买家在此种情形下的搬家、伪造身份信息办理假户口等行为,难道不应当被视为逃避侦查?近年来,公共领域越来越多的身份造假、学历造假事件得到彻查,为之提供便利、进行权力寻租的陈年旧事被扒出、被追责。相应的,为收买妇女儿童洗白身份的罪恶,也没有道理被轻易放过。
更进一步的追问在于,长时间以来对于拐卖案的司法调查与追究,是否存在所谓“不追究买家,是为了更好解救”的路径依赖?到底有没有实证的案例数据可以证明,对买家犯罪行为的宽容,真的有助于拐卖案件的办理和被拐卖人员的解救?
作为相伴而生的一组犯罪行为,对买卖妇女儿童的法律追究与行贿受贿是否应当一起查具有相似性,行贿罪一度被放过,其部分行事逻辑就在于借此实现受贿案件的顺畅办理。从2018年开始,“行贿受贿一起查”逐渐成为共识,同样的,在拐卖案件中实现“买卖同罪”也不应当再被固有的办案路径依赖所限制。严格追究收买犯罪,对各种可能导致追诉时效延长的事由尽职予以核查,即便有法定从轻理由也只是从轻而非不追究,刑诉法一直都明确要求办案人员必须全面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实现拐卖案的“买卖同罪”,期待立法领域的点滴推进,同样需要个案层面基于证据事实的司法审慎与果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