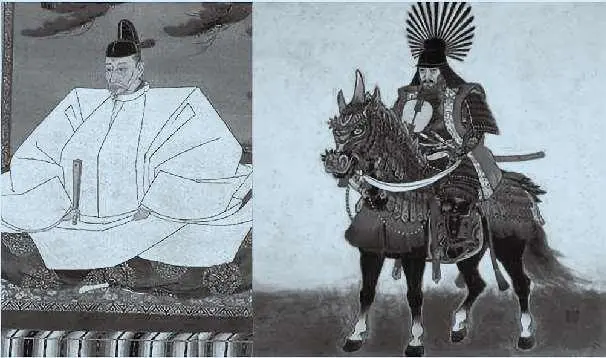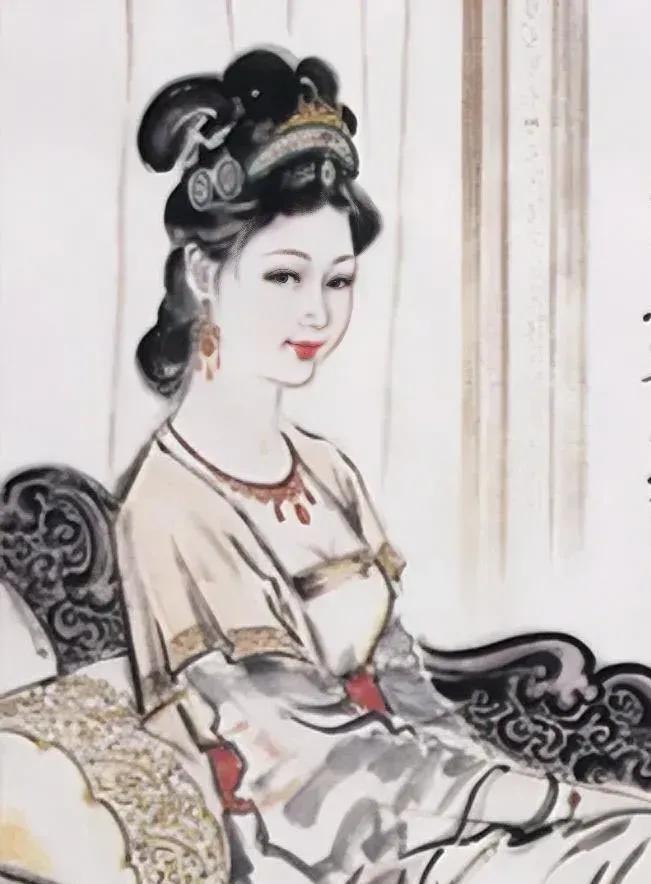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秋,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发生了一起震惊四邻的命案。村民王二牛被发现死在家中卧房,尸体蜷缩在地,口鼻流血,面色发青。他的妻子李氏跪在一旁痛哭,声称丈夫是“突发急病暴毙”。然而,村里人皆知王二牛身强体壮,平日里连风寒都极少沾染,突然暴毙难免惹人怀疑。
案件很快惊动了山阴县衙。知县张秉忠带着仵作赶到现场,一验尸便发现了蹊跷——王二牛的指甲发黑,喉间有灼烧痕迹,显然是中毒身亡。更令人费解的是,李氏的独子王顺在案发后始终闭门不出,面对衙役的询问,他眼神躲闪,双手不住发抖。这些细节让张知县嗅到了阴谋的气息。
李氏的“完美”说辞李氏被押至县衙后,声泪俱下地陈述:“民妇那日早起做饭,回房时夫君已没了气息!”她坚称自己无辜,甚至主动提出“愿以死明志”。然而,仵作的验尸结果却戳破了她的谎言——王二牛胃中残留的毒物,正是混在早饭的米粥里。李氏每日亲自下厨,除了她,谁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下毒?

面对铁证,李氏突然改口:“是顺儿!他怨恨他爹常年打骂,才在粥里动了手脚!”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王顺被传唤上堂时,脸色惨白如纸,却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张知县敏锐地发现,这对母子虽互相指认,但神情中竟无半分仇怨,反而透着一股诡异的默契。
地窖里的秘密案件陷入僵局之际,一个意外发现扭转了局面。衙役搜查王家时,在柴房角落发现了一块松动的地砖。掀开地砖,竟是一条通向地下密室的暗道!地窖中堆满金银首饰、绫罗绸缎,价值远超普通农户所能拥有。更骇人的是,角落里还藏着一包未用完的砒霜,与王二牛所中之毒完全一致。
张知县当即提审李氏:“这些财物从何而来?”李氏闻言瘫软在地,终于吐露实情——原来,她与城中富商赵德贵早有私情。赵德贵贪图李氏美色,许诺“若除去王二牛,便纳她为妾”。而地窖中的财物,正是赵德贵为掩人耳目,假借“接济孤儿寡母”之名送来的赃款。
四孝子弑母的惊天反转眼看母亲认罪,一直沉默的王顺突然暴起,冲着李氏嘶吼:“你既要跟那奸夫远走高飞,为何还要逼我毒杀亲爹!”公堂上顿时死寂。原来,李氏早在一个月前就胁迫儿子参与谋杀:“你若不听我的,我便将你私藏禁书之事告官!”明代律法严苛,私藏禁书轻则流放,重则斩首。王顺为求自保,只得将砒霜掺入父亲的粥中。

更令人唏嘘的是,案发当日,王顺因不忍下手,偷偷倒掉了毒粥。李氏见计划落空,竟亲自重新下毒,看着丈夫喝下致命米粥。她万万没想到,儿子为掩盖罪行,会在地窖中私藏证据,最终让这场“完美谋杀”露出破绽。
五、伦理与律法的碰撞案件真相大白后,山阴县衙面临巨大压力。按《大明律》:“谋杀亲夫”属十恶不赦之罪,当凌迟处死;而“子伤父母”更是大逆之罪,需千刀万剐。然而,王顺的遭遇却让张知县动了恻隐之心——他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更是母亲手中一枚棋子。
最终,刑部批复的判决震惊朝野:李氏凌迟,赵德贵斩立决,王顺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这份判决既维护了纲常伦理,又暗含对“被迫从恶”者的怜悯。有文人将此案写入话本,评曰:“毒妇毁家,稚子蒙尘,皆因贪欲二字。”
惨案背后的明代社会图景这起案件撕开了万历年间底层社会的生存困境。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催生道德滑坡,民间通奸、谋财害命案件激增。据《山阴县志》记载,仅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该县因奸情引发的命案就有11起。而王顺私藏禁书的细节,则折射出朝廷对思想控制的严酷——普通百姓为求自保,甚至不得不向至亲妥协。
更耐人寻味的是地窖中的财物。赵德贵作为商人,能轻易拿出巨额金银行贿,可见当时商贾阶层已悄然崛起。他们用金钱撬动道德枷锁,将触角伸向乡村社会,这与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形成强烈反差。

这桩“妻杀夫,子杀母”的惨案,在明代并非孤例。《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嘉靖年间扬州类似案件:寡妇与盐商私通,逼迫亲子弑祖。这些案件如同镜子,映照出传统伦理在利益冲击下的脆弱性。当“三纲五常”遭遇真金白银,人性之恶往往挣脱礼教束缚,酿成骇人悲剧。
如今重读此案,仍觉警醒——李氏为私欲毁家灭亲,王顺在威逼下丧失人伦,赵德贵仗财横行乡里。这些明代小人物的命运,何尝不是对“德不配财,必遭灾祸”的千年训诫?历史虽已远去,但贪婪与怯懦交织的人性困局,依然在时光长河中泛起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