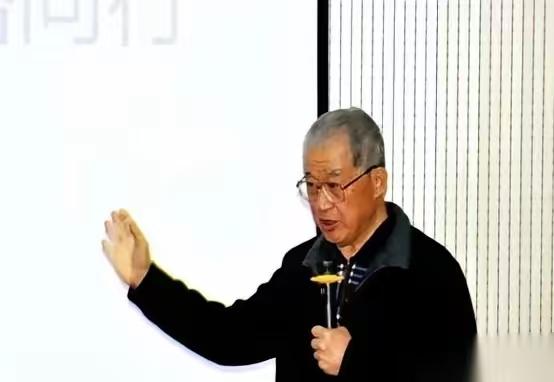他从副司令调部长,自认为老资格,后发现下属单位与他平级的不少 【1970年12月,北京玉泉路】“李司令,新官上任别把机床当火炮啊!”一句调侃,让刚换便装的李水清忍不住皱眉——那年,他从济南军区副司令岗位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一机部部长。 气氛并不轻松。一机部由原第一、原第八两个机器工业部合并而来,军工、农机、基础装备全揽。合并不过数月,文化大革命的余波仍在,各类“革委会”“筹备组”林立,指令时常相互抵触。李水清深知若不先厘清权责,生产秩序根本无从谈起。 过去领兵打仗看的是番号与番号之间的配合,如今面对全国一百多家直属企业,他只能从最朴素的做法开始——跑现场。不到四个月,他南至柳州、北到齐齐哈尔,中午听汇报,夜里在火车上对资料。有人算过,部长工作组跑出了一万多公里,相当于围绕长城走了一圈半。 路上困难不断。第一大难题是人。合并后管理层老化明显,许多工程技术专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关键岗位要么空着,要么由临时工顶替。李水清要求立即核实人员名册,恢复技术骨干原岗;可名册一拿来,足有七种版本,连厂长都搞不清谁算在编。没办法,他干脆把当年整训连队的经验搬来——现场点名、当面登记,忙到凌晨灯不熄。 第二重挑战是体制。1965年统一降薪定级后,军地干部薪级归一。李水清自认行政7级,算是“行伍里爬上来的老资格”。可刚坐进部长办公室就发现,一旁办公厅主任同样是7级,下属一家军工企业的党委书记也是7级,连外经局一位技术顾问竟挂着8级。职务与级别脱节,开会谁先发言成了难题,更别说指挥生产。 局面让他意识到:若仅靠领袖气质压阵,工业系统不会买账,必须在专业与管理之间搭桥。他挑选十几名35岁左右的技术骨干,成立“工艺协调小组”,直接对部长汇报,用今日话说就是扁平化管理。与此同时,他让几位资深老专家担任顾问,每周固定时间对年轻人做技术答疑,双方互补。 有意思的是,这套组合拳在几个月后初见成效。武汉某大型铸造厂一年半没出一台合格柴油机,经协调小组现场勘查、老专家远程指导,仅用六周便恢复批量生产。消息传到北京,国务院有关负责人批示:“机械工业有起色,可行。” 然而,制度积弊不是一朝能清。李水清很快发现,机关里的报批流程比军中请示繁琐数倍。文件盖章要跑四层楼,意见会签动辄拖十天。焦头烂额之际,他借鉴军队的“令行禁止”:凡是企业急需的零部件、材料采购,只要金额不超十万元,由厂长直接签字,事后报告。此举虽冒风险,却把很多企业从停线边缘拉了回来。 1972年至1974年,全国机械行业产值每年递增超过15%。一机部率先恢复对外配套出口,沈阳机床又远销东南亚。部里风气也悄然变化,年轻工程师深夜讨论方案,老专家重回图纸前。有人感慨:“三年折腾,如今机器声又像老黄钟,沉实了。” 事情并非全无波折。某些老干部对“让位”颇有情绪,甚至私下抱怨:“小伙子才三十多岁,凭什么指挥我?”李水清采取的办法很直接——把生产指标摊开到桌面,完成得好,指标就是话语权;完不成,再高薪级也得让位置。说来简单,执行时他得罪了不少人,可产量数字站在那儿,批评声音逐渐稀薄。 1975年初,中央着手军队整顿,南京军区急需熟悉装备保障的将领。此时一机部产能已恢复,主要厂所重新排出科研计划。李水清认为:专业干部已逐渐顶上,自己是半路出家的外行,留下反而耽误技术升级。于是郑重向组织递上报告,请求重返部队。 审批并未拖延。1975年5月,他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临行前,部里几位青年工程师到机场送行,一名小伙子握着他的手说:“李部长,您把我们当战士带,我们才知道该怎么跑。”李水清只是摆摆手:“别叫我部长,叫老李就行。机器运转好了,比我回不回部队更重要。” 此后数年,南京军区在装备检修方面屡获表扬,而一机部也顺利完成结构再调整。经历双向磨炼的李水清,用自己“副司令—部长—副司令”的特殊履历证明,军队的管理铁律与工业的精细流程并非水火,找到契合点,二者可以共同催生效率与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