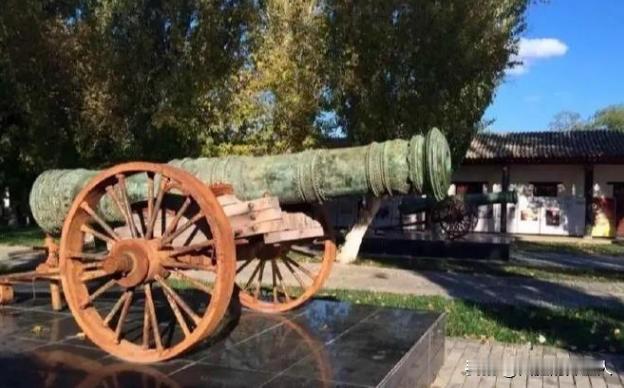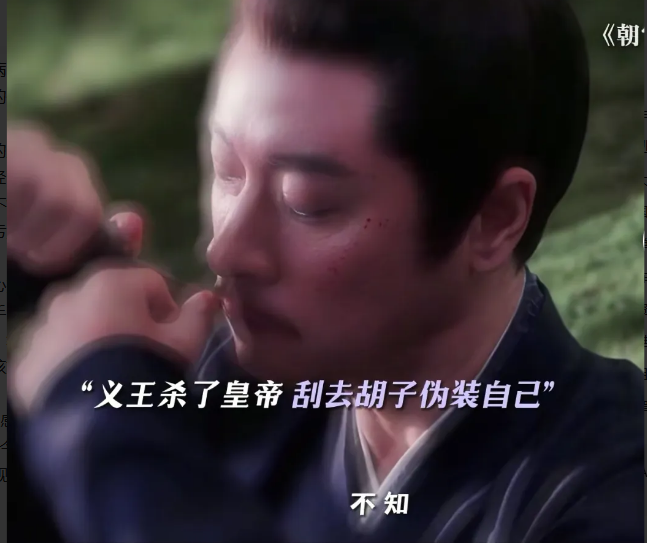1662年,20岁的郑经与35岁乳母生下一子,郑成功气得口吐鲜血,下令处死妻子董氏、儿子郑经及刚生下来的孙子。派去的将领拒绝执行命令,郑成功被活活气死。
1661年,当37岁的郑成功意气风发地率领两万将士,乘着数百艘战船,浩浩荡荡地横渡台湾海峡时,远在厦门的他的20岁的长子郑经,却似乎并没有体会到父亲肩上的重担。史料记载,那时的郑经,正与一些狐朋狗友厮混在一起,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或许,对于这位从小锦衣玉食的世子来说,父亲的丰功伟绩如同遥远的故事,远不如眼前的灯红酒绿来得实在。 郑成功并非没有察觉到长子的不成熟。早在出征台湾之前,他就将厦门这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划分为五镇,由不同的将领分兵把守。这表面上是为了加强防御,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也是他对儿子的一种制约,担心他趁自己不在兴风作浪。毕竟,十多年前,他的父亲郑芝龙降清,随后被押往北京,家族的兴衰荣辱,早已在郑成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深知,维系这份庞大基业的艰难。 然而,让郑成功始料未及的是,家族内部的风暴竟然以一种如此不堪的方式爆发。就在他收复台湾仅仅半年后,一桩丑闻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轩然大波。按照当时的伦理纲常,尤其是深受朱熹理学影响的社会,嫡庶有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元配夫人所生的儿子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而乳母的身份地位卑微,与主人发生私情并生育子女,简直是“大逆不道”。 偏偏,郑经就犯下了这样的错误。他与他四弟的乳母陈昭娘私通,并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郑克臧。消息传到台湾,如同火上浇油,让郑成功怒不可遏。
1662年五月初,一道措辞严厉的手令,由信使快马加鞭送到了金门。这道命令来自于台湾湾里溪畔,病榻之上的郑成功。接令者是郑经,作为郑氏集团名义上的继承人,他继承了父亲在海上建立的庞大商业和军事帝国,但他似乎更愿意以一个“读书人”自居,附庸风雅。这种身份的错位,或许也为他后来的行为埋下了伏笔。而这次,他的“读书人”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庇护,父亲的命令直指核心——“治家不严”,竟然成了死罪。 与此同时,在厦门芝山岩的郑府里,被关押的陈昭娘紧紧地抱着怀中的婴儿郑克臧。她或许并不知道,这个因为郑经的一时贪恋美色而降生的孩子,日后竟然会短暂地摄政台湾二十年,成为郑氏集团最后的希望之一。 金厦都护使郑泰是郑成功的老部下,他深知这位主子的脾气。 当他得知郑成功下令逮捕黄毓(据一些野史记载,黄毓可能与郑经的丑闻有关)的消息后,他更加忧心忡忡。远在台湾热兰遮城废墟上的郑成功,或许也会想起当年洪承畴劝降他父亲郑芝龙时的场景:大明遗民与江南豪族的联姻,看似强大,却也承受不起内部人伦崩坏带来的合法性损耗。
千里之外的金门庙湾码头,夜色如墨,郑泰与另一位重要的将领洪旭正在秘密商议。 不识字的洪旭将军在纸上画出了金厦的地形图,他对郑泰说:“当年世子年幼,主公尚且将其监禁在何廷斌府中,如今怎能因为这点事就下令处死呢?这岂不是首尾倒置吗?”这个提议,最终导致了郑氏集团内部文官武将的分裂,为后来的权力斗争埋下了伏笔。 郑成功去世仅仅七天后,黄昭、萧拱宸等文官就打着“法不可废”的旗帜,拥立郑成功的弟弟郑袭为新的领导者。 郑经采纳了冯锡范“先定内乱再御外侮”的建议,率领舰队秘密横渡海峡。随着郑经的部将陈永华偷偷潜入台湾北线尾,散布所谓的“詹事府密令”,揭露黄昭等人篡位的阴谋,台湾的军事态势急转直下。仅仅五个月后,黄昭被杀,萧拱宸被斩首,郑袭被软禁,这场发生在东南海上的“七王之乱”暂时平息。 远在福州的清朝水师总兵陈霸,在内院摊开地图,看着郑氏集团的内斗,不禁感叹道:“郑家竟然敢效仿汉高祖刘邦诛灭异姓诸侯,如此内耗,恐怕离祸患不远了。” 1663年秋,当清朝与荷兰的联合舰队压境之时,郑成功生前呕心沥血打造的承天府铁税制度出现了严重的漏洞。当年收复台湾时,得力干将马信曾建议实行“盐铁专营以富军需”,但由于内斗期间马信的突然暴卒,这个计划也随之夭折。失去了这位理财能手的郑氏集团,再也难以恢复征台前的备战状态。厦门失守时的混乱撤退,导致三十多艘战船搁浅焚毁。 多年以后,郑经令人编纂的史料中,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只是笼统地记载道:“夫太妃恭谨有训,世子克终丕绪。”而后来投降清朝的冯锡范的家谱中,则披露了更多复杂的细节:郑经曾经秘密召见范文程之子,并对他说:“家严当年如果能理解程朱理学中的迂腐之处,又何至于导致闽粤地区的萧条凋敝呢?” 从郑家内斗的情况来看,家族矛盾已经严重动摇了军心。1664年清明时节,当郑经率领最后较为完整的军马撤离铜山时,跟随他撤退的监军陈永华,在戈船上发出了深深的叹息:“叔宝临朝而晋室亡,此江左覆辙也。”后来的历史不幸印证了他的担忧:失去凝聚力的郑氏军队,在澎湖海战中屡次出现部下投降清军的情况,最终导致施琅的大军几乎兵不血刃地收复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