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走茶凉?”2021年上海,老人去世后,家中保姆协助老人儿子办理了身后事,两个月后,老人儿子要求保姆从房子里搬走,可保姆却认为自己照顾了老人一辈子,对老人有恩,不愿意搬离。老人儿子将保姆告上法庭,要求保姆搬离房屋,并支付房屋使用费,法院判了。网友:真把这里当自己家了!
在繁华的上海,一处看似普通的住宅里,保姆珍姨的一句话,揭开了一场持续二十多年的情与法的纠葛:“这是我照顾了老王二十多年的家,凭什么要我搬走?”
故事得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那会儿,珍姨刚到王家,王晓还是个十岁的男孩。她负责照顾孩子、打理家务,把一个三口之家料理得井井有条。
好景不长,王晓的父母离了婚,母亲周霞带着他远走国外。即使雇主家庭分崩离析,珍姨也没走,而是选择留下来,照顾独自生活的老王。
这一照顾,就是二十多年。珍姨成了老王晚年生活里离不开的支柱,从一日三餐到生病陪护,她早已超越了保姆的职责,更像一位亲人。
王晓虽远在国外,也时常和父亲通电话,对珍姨在父亲身边的角色,他心知肚明。这份超越雇佣的情感,似乎成了这个特殊家庭里心照不宣的共识。
2021年夏天,老王突然离世。因为疫情,远在国外的王晓无法回国。最后是珍姨和亲戚们一起,为老王操办了身后事,送了他最后一程,这份情谊,却在老王去世后,撞上了冰冷的房产证。
原来这套房子背后另有隐情。早在2000年初,老王买下这套房,可付了首付就还不起月供了。他和前妻周霞商量后,把购房人改成了周霞和儿子王晓,后续的房贷也由周霞一人还清。所以,房子的产权证上,从来就没有老王的名字。
尽管如此,周霞和王晓也曾同意为珍姨母女办理居住证,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默许了她的长期居住。珍姨也说,老王生前不止一次对王晓提过,要给她一笔安置费或解决养老住房,可这些口头承诺,终究没能落在纸上。
老王走后两个月,王晓通过微信联系珍姨,请她搬走。他的逻辑清晰,甚至有些冰冷:父亲在世时,珍姨每月都领工资,这是标准的雇佣关系。他感谢珍姨多年的照顾,但这并不代表她可以获得合同之外的房产权益。感谢归感谢,房子归房子。
珍姨当然不答应。她坚信自己二十多年的付出,早已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她觉得自己是这个家的成员,尤其在老王生命的最后阶段,她扮演的角色无可替代,更何况老王还有过承诺。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亲情协商的路走不通,最后只能对簿公堂。
法庭上,争论的焦点很明确。王晓一方手握房产证,这是最硬的道理。他认为,雇佣关系已经随着父亲的去世而终结,珍姨继续居住于法无据。而珍姨这边,能拿出的只有二十多年的感情和一段无法证实的口头承诺。她用二十年的情感,去对抗一张写着别人名字的房产证。
从法律角度看,这案子其实并不复杂。根据《民法典》,居住权的设立需要书面合同或遗嘱。珍姨一样都没有。
至于老王的口头承诺,先不论真假,关键在于,老王自己都不是房主,他又如何能承诺一套不属于自己的房子呢?他的承诺,在法律上自然也约束不了真正的产权人王晓。
最终,法院的判决并不意外。法院认定,珍姨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所谓的安置费承诺,即便有过这个意愿,也不能强加给王晓。作为保姆,她照顾老王是职责所在,并且已获得了劳动报酬。
老王去世后,她继续居住确实缺乏法律依据。不过,法官也并非不近人情,考虑到珍姨多年照料的功劳和长期居住的现实,给了她一段合理的搬离宽限期。
一场官司,在法律上尘埃落定,在人情上却掀起了巨大波澜。有人说王晓“人走茶凉”,太过无情;也有人觉得,亲兄弟尚要明算账,更何况是雇主和保姆,“真把这里当自己家了?”这句评论,也道出了很多人对边界感的看重。
说到底,这起纠纷拷问的,是在金钱与契约之外,情感付出的价值到底有多重。它也像一记警钟,提醒着无数依赖家政服务的家庭:情感再深厚,也不如一纸清晰的协议来得可靠。法律的判决可以分割房产,但又如何能厘清那二十多年相伴的恩与怨呢。
信源:九派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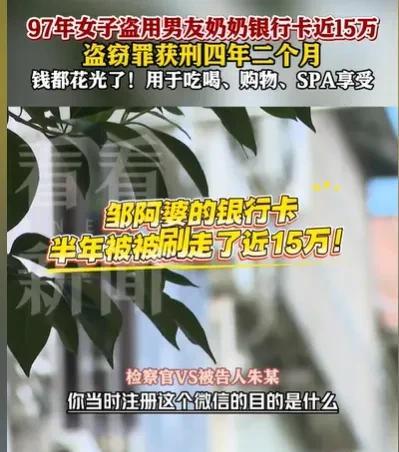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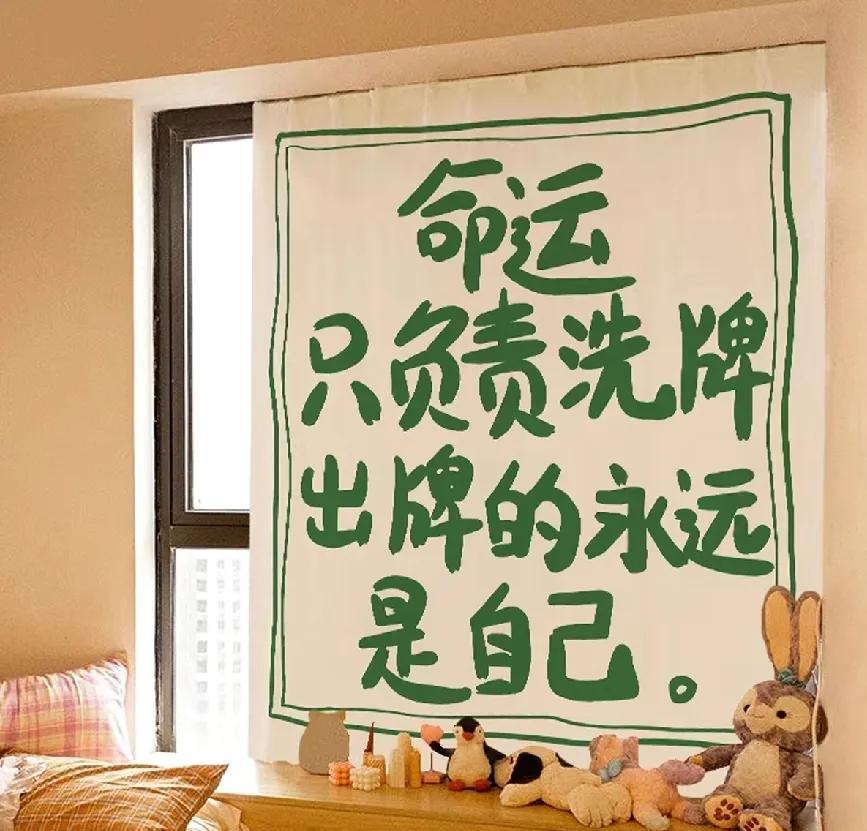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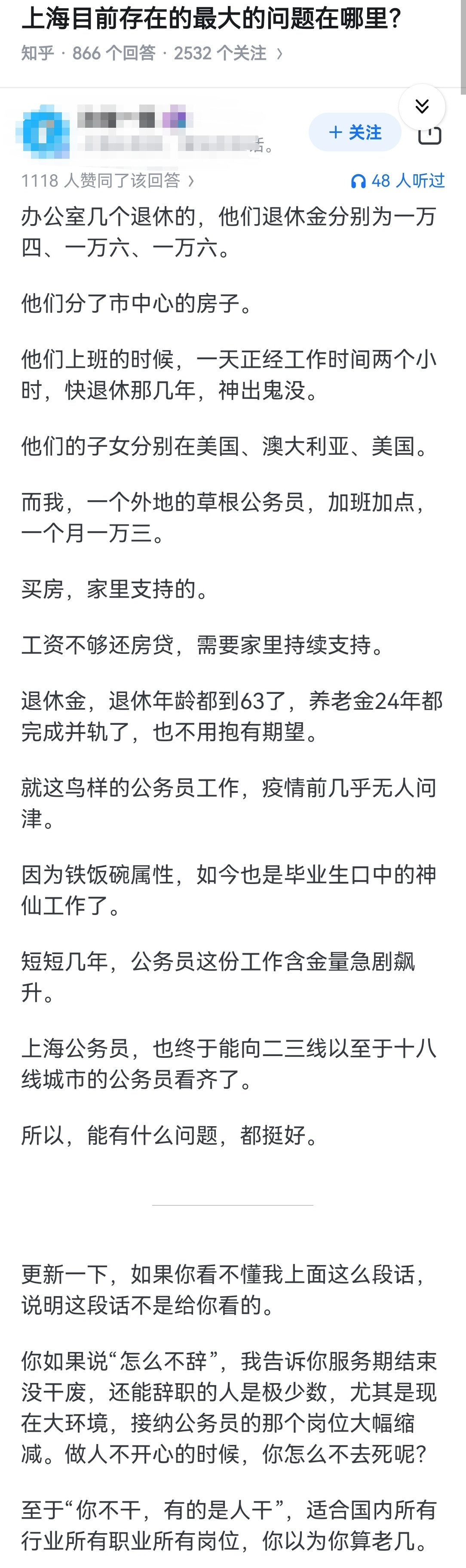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