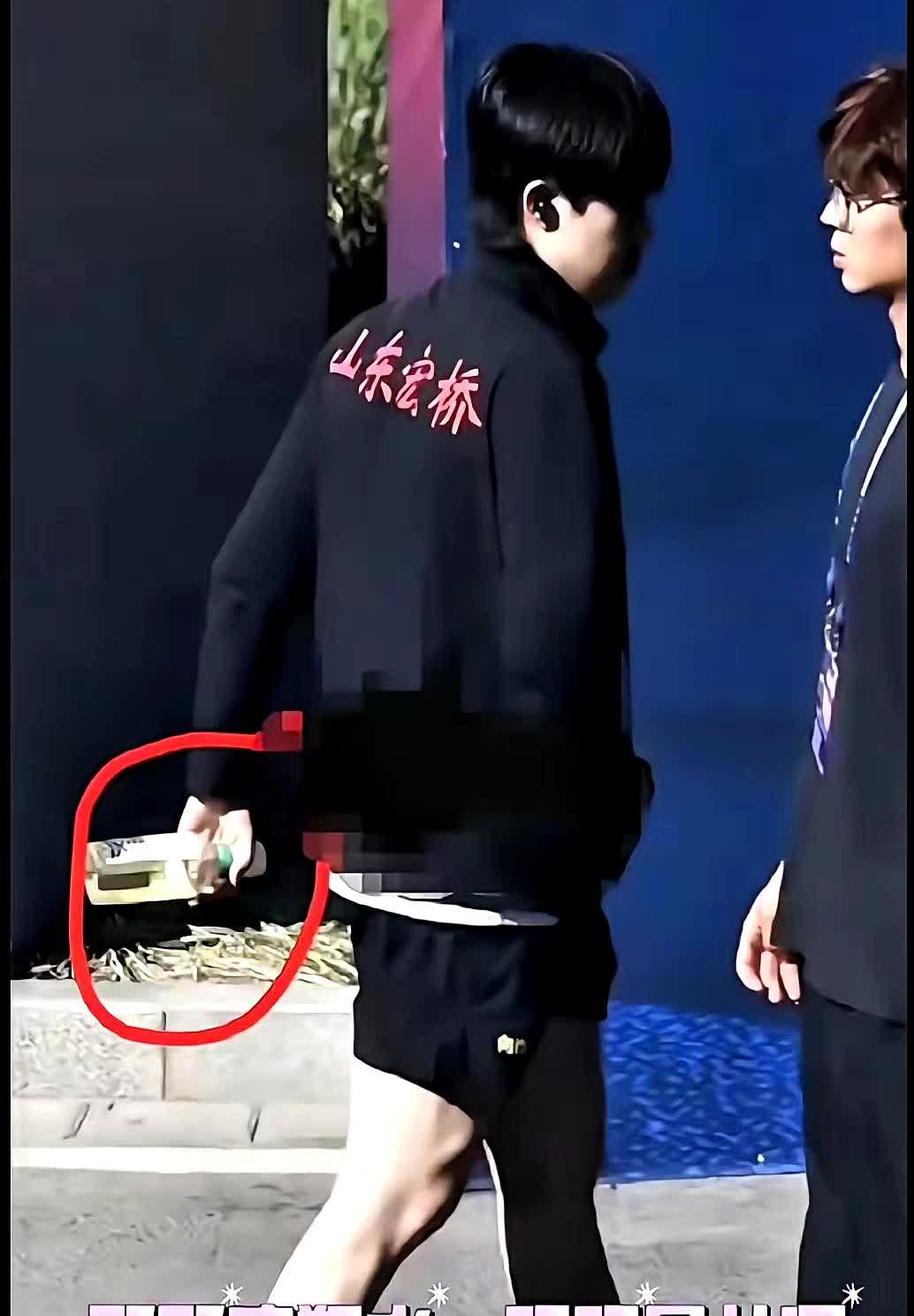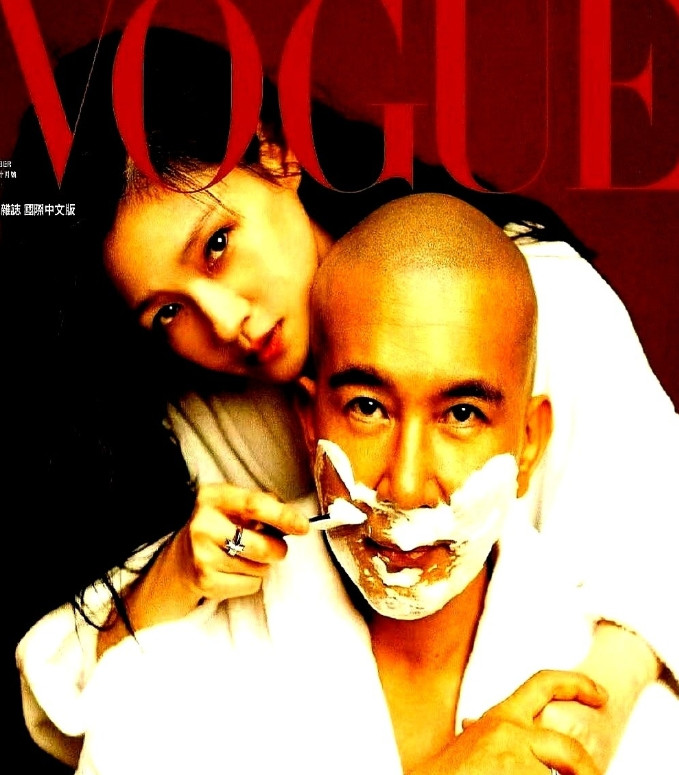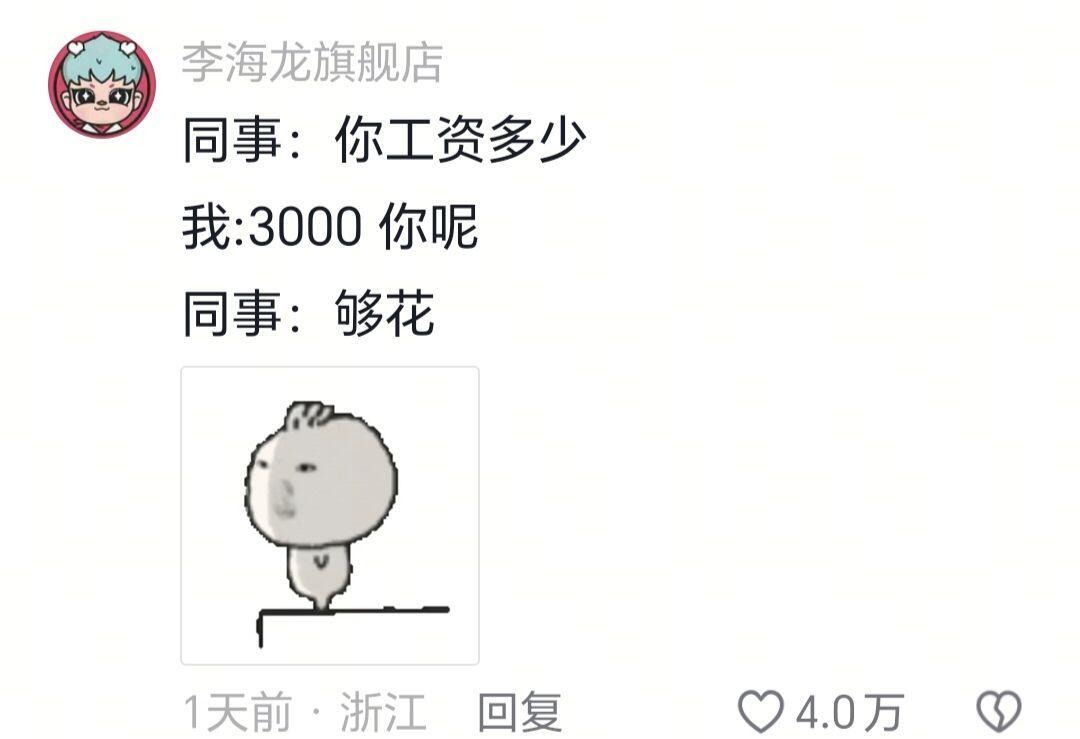1988年纪登奎去世前,说了一句话:“我不行了,我要死了。”那天他刚吃过晚饭,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本来是散步消食,谁都没想到,一场彻底的告别就在几分钟后发生...... 1988年那个夏天,北京的天气一向闷热。 晚饭后,纪登奎像往常一样在内务府街的四合院里踱步,手里没拿书,也没讲话。天还是亮的,空气里泛着潮气,他一边走,一边消食。 院子里那株石榴树正结着小果,红不红绿不绿地挂着,风不大,虫子倒挺响。 谁都没想到,就在那几分钟里,他突然停住了脚,身子一歪,摔在砖地上,只留下一句话:“我不行了,我要死了。”声音不大,但够真切。他的老伴王纯吓得不轻,冲出来的时候,还以为是闹着玩。可纪登奎脸都白了,手指蜷着,身上也没了动静。 这人啊,说没就没了。 那时候他才65岁,正部级待遇,住在市中心一座老四合院里。 院子不大,收拾得挺干净。 墙角种了点花草,后面一排矮竹子,静的时候能听见鸟儿叫。他早就不在高位上了,生活过得简朴,除了几个老同事偶尔来串门,基本就是他和王纯在一块过日子。 两人认识得早,早到还能追溯到抗战时那个闹哄哄的年代。 王纯比他大一岁,是女八路出身,后来跟着部队辗转在河南一带搞地下工作。 两人同在许昌,相识那年都还是年轻人,一路走来,生了五个孩子,也经历过起伏不少的年头。 说起纪登奎,有的人会想到他是毛主席口中的“老朋友”。 这话是毛在1951年南下许昌时说的。当时毛要听地方干部汇报,纪登奎才28岁,是最年轻的地委副书记。他讲话语速不快,汇报得清清楚楚,毛听完后点头说:“你多大?”他说23年生的。毛乐了:“小我三十岁,老朋友啊。”一句调侃,却记了下来。 此后毛对他格外留心。 几年后在郑州,毛再次提起这位“老朋友”,还让人找来一块大理石做纪念,说这人“靠得住”。 纪登奎仕途的起步,其实就是从那场汇报开始的。 从地委副书记一路上调,他干过洛阳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还进了国务院。 1975年被任命为副总理,成了副国级干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这种上升速度说快也不快,说慢也不慢。很多人说他是“毛看重的人”,这话没错。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懂得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他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干部,也不爱抢功。 他说话慢,做事也稳,不太讲场面话,倒是挺能忍。分管宣传那会儿,很多文化单位都归他管,但他从来不把调子拉得太高,说自己就是“过日子的人”。 等到1980年,他突然递交辞呈,提出辞去副总理职务。 外头人还没缓过劲儿来,他已经把东西收拾好,调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不带头衔,没实权,但待遇不变。那会儿中央不少干部都在往“实职”上靠,他却往后退了一步。 有人说他是识时务,也有人说他是“退得漂亮”。那时候“老中青”交替成为潮流,退下来的干部要么“带病留任”,要么“下放虚职”,像纪登奎这样主动辞去副国级职位的,确实不多。 他也没吵没闹,甚至连告别会都没办,低调得很。 辞职以后,他和王纯搬进了内务府街的那套四合院,住得算舒服。 原先的干部宿舍早已住满,老两口喜欢安静,也不愿再凑热闹。四合院一进门是影壁墙,右边是厨房,正屋三间,书房和卧室都挨着。 纪登奎每天早上起得早,读资料、写字、看报纸,有时候会跟王纯聊起旧事。 他确实有写回忆录的打算,不是一时兴起,是真的认真筹备。 他说要写两本,一本是人生经历,另一本文专讲“特殊十年”。秘书回忆说他动笔了,前面写得挺顺,就是没来得及写完。案头常年堆着文革时的文件副本,还有自己当年签批的材料,旁人看了都头大,他倒是常说:“这些事不说清楚,不算个完。” 那几年,除了写作,他偶尔也会接待些老朋友来串门。 说不上热络,但不拒人。有一次,有人说起中央的政策调整,他摆摆手说:“别问我了,我早就退下来了,现在就是个写字的。”话说得平淡,其实也有几分无奈。 他没病,或者说没有大病,平时身体也硬朗。 王纯一直陪在他身边,吃穿用度都照料得细致。俩人年纪相仿,一块生活了几十年,有说有笑,有时也斗嘴。 那天晚饭后就是这样,起因说起来有点可笑——两人聊到谁的革命资历更老。 王纯不服气,说自己1938年就跟着部队跑了。 他说自己虽然也是38年参加工作,但入党比她早几个月。王纯一听就不乐意,说:“你净爱抢功。”他说:“我说的是事实嘛。”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虽然没吵大架,但多少带点情绪。 饭后他照常散步,王纯还在厨房擦碗。 谁也没想到,那会儿就是永别。事后王纯一直念叨:“那天不该跟他争那几句。”她哭着说,如果不争,他就不会激动,也许还能多活几年。 但医生说得明白,这是心脏病突发,不是情绪惹的祸。 纪登奎本身就有心血管病史,只是从来没发作过,谁也想不到,那天的发作来得那么急。 葬礼办得不大,家属坚持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