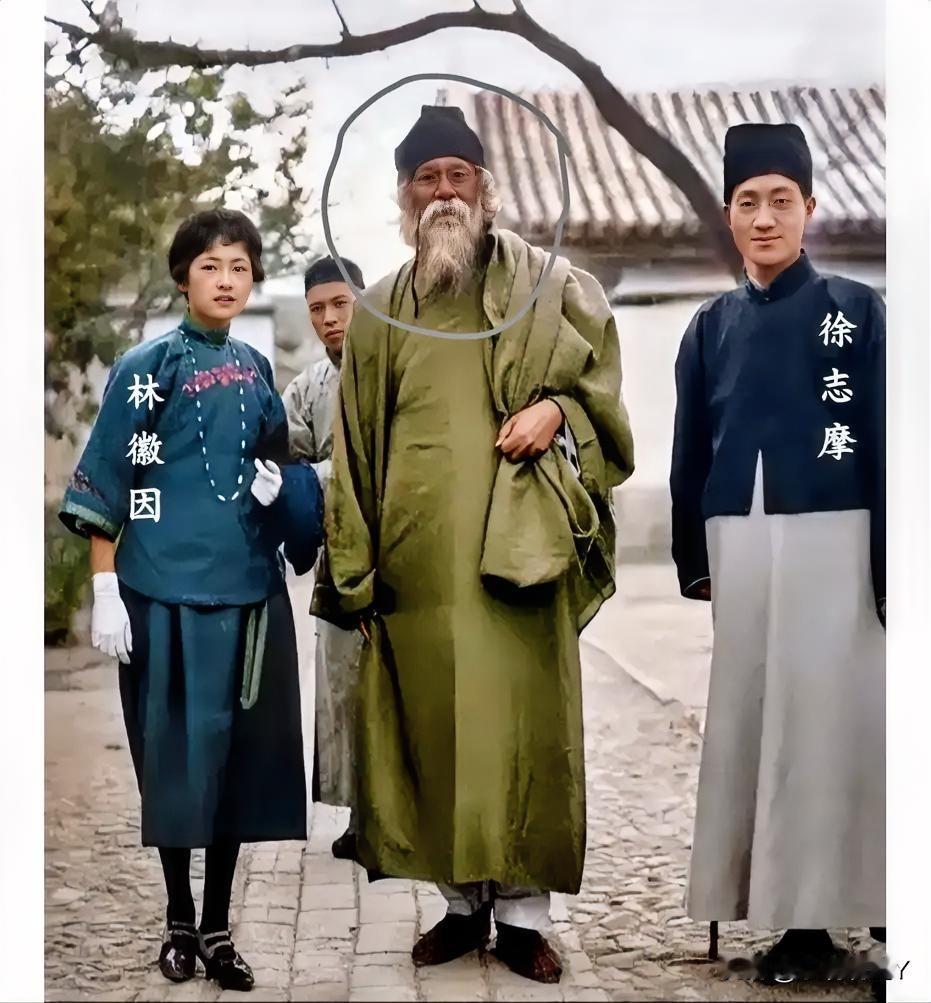1925年11月林徽因父亲兵败身亡时,她四个弟弟中最大的才11岁。四个异母弟弟后来都靠林徽因照顾抚育,她和弟弟们感情非常好,为此没少挨亲生母亲的责骂。
林徽因的名字,这些年总是被人拿来说事。 她父亲林长民,是民国初年政坛的“清流”,字写得好,话说得利落,人也有担当。 可惜命不长,1925年,那会儿国共合作刚刚起步,北方战乱没停,林长民因卷入郭松龄倒戈张作霖的事件,被乱军流弹击中身亡。 那年林徽因才21岁,人在美国留学,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林家一下子散了。 老先生留下的四个小儿子,全是异母,最大的十一岁,最小还在吃奶。 对旁人来说,这种局面可能就是家族的残局,兄弟姐妹一哄而散,各自靠命。 可林徽因不是这么想的。 她不光自己忍住哀伤,还开始张罗弟弟们的事。 这些弟弟,说白了跟她并不算“血脉至亲”,母亲不是一个,但父亲的血脉相连,她认得清这一点。 后来她从美国回国,先是把母亲接来住,再一一把弟弟们接进自己家。 住得下吗? 不宽裕。 处得好吗? 也不好。 尤其她母亲,对这些异母的孩子一直看不顺眼,逮着机会就骂。 林徽因夹在中间,明里暗里受了多少气,没人知道。 有段时间她整夜睡不着觉,写信给朋友时说,自己被母亲“拖入了人间地狱”。 那信后来传出来,很多人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民国才女”,过的是什么日子。 她的坚持,其实也没什么高调理由,不是道德崇高,不是家族荣耀,就是骨子里那口气。 她说:“父亲不在了,我不能让这个家也没了。” 这句话她没大声说过,只是一直这么做。 哪怕她弟弟考上清华,她都一声不响把人接来家里住。 外人听着可能觉得“这不就长姐如母么”,可在那个年头,女子连继承权都没有,一个未婚女子主动养异母弟弟,这不是善良,是倔强。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梁思成慢慢走进了她的生活。 两人早年在美国就认识,按说是“自由恋爱”,但真往细里看,其实他们的结合,也有一层现实考量。 林徽因父亲身故,家中顿时无主,梁启超出面张罗丧事,还自掏腰包资助林家度日,这在那时是极讲义气的举动。 林徽因对这份情,看得分明。 婚姻之中当然有情爱,但感恩与责任也在。 她有一句话传下来,说给梁思成听的:“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会用一生来偿还。” 这话不像小情小爱,更像是盟约。 婚后两人去了宾大继续求学。 那个年代,美国的建筑系不收女生。 林徽因干脆转进美术系,再通过旁听、做助教,一点点摸进建筑学的大门。 梁思成本来对建筑没多大兴趣,爱画画,后来被林徽因一句话打动了:“建筑,是艺术和工程的结合。” 从那以后,这对夫妻就成了中国建筑界的“工友”。 别人蜜月去巴黎喝红酒,他们是背着画板奔走在各国街头,看教堂、看拱顶、量柱距,记录每一个砖石细节。 这对夫妻从来不谈浪漫。 他们从美国回国后,直接在东北大学创建建筑系,教学、画图、写教材,林徽因一干就是十几个年头。 她对学生要求特别高,图纸稍有瑕疵,就直接批评,有次一个学生画歪了,她当众说“这不是人画的”,语气那叫一个直。 有人说她不够温柔,她不争。 她说:“建筑不是柔情,是尺度。” 这一句话,就能看出她内心的利落。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北平很快沦陷。 林徽因一家人没犹豫,立刻南下。 昆明、贵阳、再到李庄,一路颠沛流离,她带着孩子、带着母亲,还拖着一本本厚重的建筑资料。 别人劝她出去治病,她说:“这个时候,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不该离开。” 她那会儿肺病加重,骨瘦如柴,每天咳到脸色发白,但只要还有口气,就不放下手上的校稿与翻译。 在昆明时,他们被请去参与西南联大的校舍设计。 经费不足,图纸一改再改,最后只能搭茅屋充教室。 林徽因看着定稿的那一晚,流了整夜的泪。 她没说“这设计不好”,只说:“中国的孩子,要在茅草屋里上学了。” 这不是伤感,是痛心。 那种感觉,像她一直想要留住点什么,却眼睁睁看着它一片片剥落。 后来抗战结束,她回到北京,身体已是一身病。 那时城里开始拆古城墙、修大马路,她气得直发抖。 她拄着拐杖站在城墙边,朝着工人喊:“你们真拆了,将来会后悔!重建的再像,也是假的!” 没人听。 她声音嘶哑,脸色苍白,但还是站了一整天。 拆与不拆已经不是她能左右的事了,可她非得喊出这一句,哪怕没人信。 1955年春天,她在北京病逝,年仅51岁。 死的时候瘦得像纸,很多朋友都说,这样一个人,若是生在别的年代,也许能活得轻松点。 但她就是生在这个年代,她也从没打算轻松。 她做的那些事,不是为了成为“传奇女性”,只是她看见了责任,看见了遗产,看见了这个国家千疮百孔的身体,她没法不去缝。 别人问她图什么,她从不解释。 她一生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事该有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