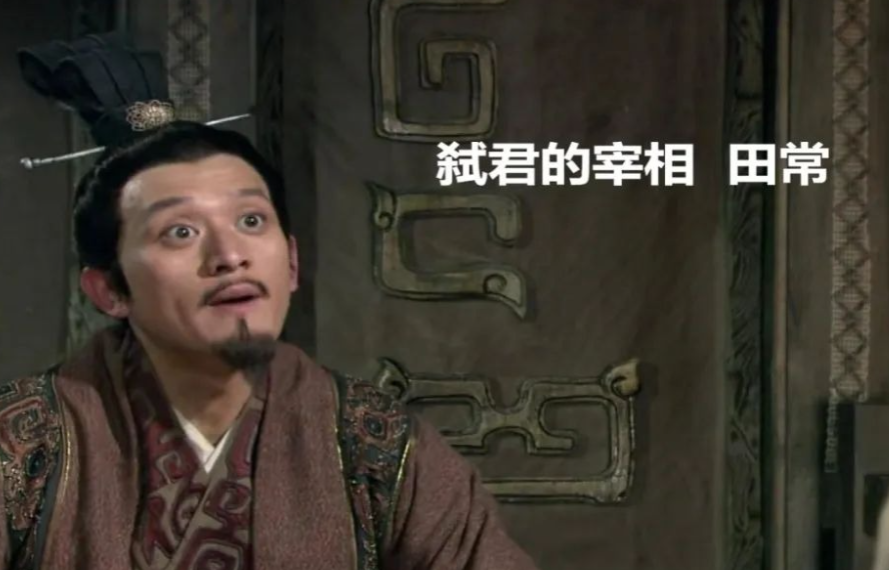347年,东晋驸马桓温率军灭了成汉,却看上了绝色的成汉公主,还强行将其纳为小妾,很快,他的公主老婆就发现这一秘密,她提着刀就要去砍了小妾。 谁料,见到小妾后,她却不忍心了,还脱口而出:“怪不得那个老家伙动了心,就连我这个女人看了也心动!” 东晋永和三年,一场看似寻常的纳妾风波,却因一句“我见犹怜”流传千古,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权臣桓温、皇室公主南康,以及成汉亡国公主李氏。 桓温出身颍川桓氏,父亲桓彝在苏峻之乱中殉国,十五岁的桓温立誓复仇,四年后在江播的丧礼上手刃仇家三子,一时声震建康,晋明帝司马绍看中他的胆识和才干,将嫡长女南康长公主许配给他。 南康公主的刀是西域进贡的弯刀,银鞘上镶着红宝石,此刻却被她攥得发白。 侍女跟在后面小跑,裙裾扫过回廊的青石板,发出细碎的响。“公主,要不……先回吧?”有人怯生生地劝,“将军(桓温)知道了,怕是要动气。” 南康猛地停脚,回头时,鬓边的金步摇打得脸颊生疼。“动气?他纳小妾时,怎么没想过我会动气?”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更多的却是怒,“我是大晋的公主,他敢把亡国奴塞进门?” 穿过月亮门,就到了桓温新辟的别院。 窗纸上映着个纤细的影子,正坐在案前,手里好像在绣着什么。南康深吸一口气,一脚踹开房门,弯刀“噌”地出鞘,寒光劈向那影子。 李氏吓得猛地站起,手里的绣绷掉在地上,丝线缠成一团。 她没躲,也没哭,只是抬起头。 晨光从窗棂漏进来,落在她脸上,皮肤白得像上好的羊脂玉,睫毛长而密,垂落时像两把小扇子。最要紧的是那双眼睛,没有惊慌,只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像雨后的湖面,漾着水汽。 她还穿着成汉的旧衣,素色的襦裙洗得有些发白,却衬得身姿更显单薄,像株被风雨打蔫的玉兰。 南康的刀停在半空。 她原以为,这亡国公主定是妖妖娆娆,靠着狐媚手段勾引人。 可眼前这模样,干净得让人心头发紧。 “你……”南康的声音哽住了,刀差点从手里滑下去。 李氏慢慢屈膝,福了一礼,声音轻得像羽毛:“罪女李氏,见过公主。” 她的发髻歪了,一支素银簪子摇摇欲坠,是成汉宫里最普通的样式。南康忽然想起,自己十岁生辰时,父皇送的金簪上镶着鸽蛋大的珍珠。 “你可知罪?”南康强撑着威严,刀尖却不自觉地偏了偏。 李氏低头,指尖绞着衣角:“国破家亡,身不由己,罪女不敢辩。” 这话像针,扎在南康心上。 她是大晋公主,生来尊贵,可她也见过永嘉之乱后,流民扶老携幼逃难的模样。那些亡国的宗室女,下场比死还难堪。 眼前这女子,明明是阶下囚,却没半点卑贱相,反而有种说不出的体面。 桓温这时闯了进来,看见这架势,脸都白了:“阿南!你这是做什么?” 他想上前夺刀,南康却猛地转身,瞪着他:“老家伙,你倒是好眼光!” 她把刀扔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指着李氏对侍女说:“给她换身新衣裳,搬到我隔壁院住。”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桓温愣在原地,李氏也愣了,只有地上的绣绷还在轻轻晃动,上面绣了半朵蜀葵,是成汉的国花。 后来,南康常找李氏说话。 听她说成汉的趣事,说蜀地的荔枝有多甜,说她父亲(成汉皇帝)其实并不凶,只是老了糊涂。 李氏也听南康说建康的繁华,说晋明帝如何疼她,说桓温年轻时有多愣,为了给父亲报仇,在丧礼上杀人时,手都在抖。 有回喝了点酒,南康红着脸问:“你真不恨他?” 李氏拨着酒盏里的青梅,轻声说:“恨也没用。公主,你不也常说,好多事由不得自己吗?” 南康没再说话,只是给她满上了酒。 她忽然懂了,那天自己为何下不了手。 不是因为李氏太美,是因为在她眼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都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只不过一个生在皇室,一个成了亡国奴。 桓温后来问过南康:“你怎么突然转性了?” 南康白了他一眼:“我见犹怜,何况老奴?” 这话传出去,成了建康城里的笑谈,却也没人再敢轻视李氏。 再后来,李氏为桓温生了个儿子,南康亲自给孩子取了名,叫桓玄。 没人知道,南康偶尔会看着李氏绣蜀葵,想起那天清晨,晨光里那个单薄的身影。 这场纳妾风波,哪是什么争风吃醋。 是两个女人,在男权的棋盘上,突然看懂了彼此的身不由己。 南康的刀没劈下去,劈碎的却是“公主”与“亡国奴”的对立。 李氏的沉默没换来屈辱,反而赢来了一份微妙的尊重。 而那句“我见犹怜”,说到底,是女人对女人的共情——再高的身份,再美的容貌,在乱世里,都不过是风中的花,能相互怜惜,已是难得。 (信息来源:《世说新语·贤媛》《晋书·桓温传》,历史文化网《“我见犹怜”背后:东晋公主与亡国公主的和解》,趣历史《桓温纳妾:一场改写女性关系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