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有个画家,叫黄公望。他79岁高龄时,一天独自在江边作画,突然被觊觎他的仇家从背后推了一把,瞬间跌入滚滚江水中
1343年深秋,79岁的黄公望在富春江边跌落激流,江水裹着枯草灌入喉咙,后背的剧痛让他浑身发麻。
落水前,那双布满褶皱的手死死护住背上的画筒,《富春山居图》的草稿在里面,他大半年的心血都在里面。
岸边仇家的脚步声渐行渐远,那些人是是当年乡绅派来的报复者。
几个月前,那乡绅捧着金子求他作画祝寿,被这位性子耿直的老画家冷眼拒绝。
黄公望前半生仿佛被命运拖行,早年父母双亡,被温州人黄乐收为义子,之后改姓黄。
青年时期两次入仕为书吏,因主官更替和政治斗争先后失去职位。
然而官帽没戴热,上司张闾的九条命案将他拖入大狱,出狱时人至中年,两鬓尽白。
出狱后的清晨,当故人敲开他的破门,邀他重入府衙当差,黄公望提笔落下一幅墨竹,此后掩门而去再不回头。
然而五十岁学艺谈何容易?年过半百的黄公望站在画家王蒙门前,对方连连摇头。
王蒙的拒绝声散进风中,只见这位须发皆白的老者默然坐在山岩上,从破晓到黄昏,凝视云雾聚散,聆听渔舟归唱。
就在数月之后,当那幅惊心动魄的山水在王蒙眼前展开,时光仿佛倒流三十年,黄公望枯坐山石非为痴傻,是在与天地默默对话。
待他隐居富春江畔时已近耄耋。
他的师弟无用和尚见他整日在礁石上铺纸作画,苦劝他远离江涛之险。
而黄公望静坐如老松盘根根本就是不听,而无用看他这样只得叹息着转身离去。
没想到那天他和往常一样,坐在江边画画,没成想仇家派人给他推下江中。
刺入骨髓的江水裹着秋寒,他的指甲抠进岸边的苇根,没成想粗木画筒竟成了救命浮木。
待到渔民老王撑船而至,将他连人带画拖上腥味弥漫的船舱。
一碗滚烫鱼汤下肚,他看着画筒内浸湿的草稿,突然笑了。
画具早已卷入江涛,老王捡来烧黑的木炭和糙纸。
黄公望蘸着墨汁勾画心中富春江,晨雾如何漫过山腰,夕照如何熔金化水。
老王盯着木炭勾勒的江面,喃喃说道这画里的江比他日日捕捞的更真切。
老人眉间霜雪微融,经此一劫,他突然懂得画魂不在形似,而在那寒江淬炼过的坚韧精神,江水起伏是人生跌宕,芦苇细弱却能守住根本。
之后步履蹒跚辞别渔家,黄公望逆江而上,住进庙山坞的废祠。
此后四年,村人常见他拄着拐杖沿江跋涉,晨雾中一坐便是一日。
村里人见他攥着浸透江水的草稿,却画得更忘我。
松烟作墨,山鸡毛做笔,他画的不是山水气象,而是生命的体悟,晨雾朦胧如婴儿初醒,夕阳披拂似老者慈容。
富春江的浪头多了推舟向前的韧劲,岸边古树枝桠扭曲却誓死不折。
樵夫问他古稀之年为何受这风雨之苦,他指向烟波浩渺的江面,江水不问岁月只管奔涌,此画当随江流存千古。
1347年,庙山坞的落叶堆满窗前时,《富春山居图》完成。
三丈长卷展开富春江四时轮回,十座峰峦绵延出天地正气。
师弟无用和尚捧着画卷双手微颤—,里藏着落水时的寒雾,苇丛里的喘息,渔人那碗滚烫的关怀。
黄公望鬓发已染浓霜,看着画卷只觉此生足矣,此作当随江水千古流芳。
随后,老人将这幅历经生死劫数的长卷托付给了师弟。
八年后雪锁山坞时,八十六岁的黄公望在茅屋含笑而逝。
此卷辗转数百年,在1650年惨遭火焚,被吴静庵从火盆中抢出时已成两截。
前段《剩山图》烟痕斑驳,如泣血之唇,后段《无用师卷》焦痕蜷曲,似撕裂之躯。
《剩山图》最终停驻杭州西湖之滨,《无用师卷》则随渡海人流落向孤岛,如同两片残破的浮萍隔海相望。
直到2011年6月,台北故宫展柜灯光柔亮,《富春山居图》断裂的身躯隔着三百六十年光阴首次依偎。
人们说这是山水合璧,却不知这是富春江的魂魄穿过烈火与海潮的隔世拥抱。
黄公望以枯槁的手指丈量过富春江的每一寸肌理,临终前也未料到,他饱含生命的画作历经火烧水浸,却成就了艺术史上最荡气回肠的逆流而上。
浩荡江水千年如故,黄公望画中的舟楫仿佛仍在云水间沉浮,生命的长度本由天定,可总有人用血墨和风骨,在历史长河里劈开属于自己的航道。
他真正的洒脱,是看透世间浮名不过云烟,唯有心中山水永存。
昨天是段历史,明天是个谜团,而今天是天赐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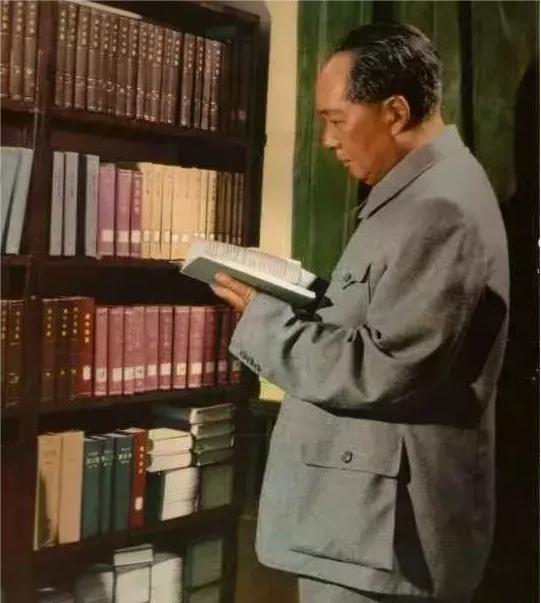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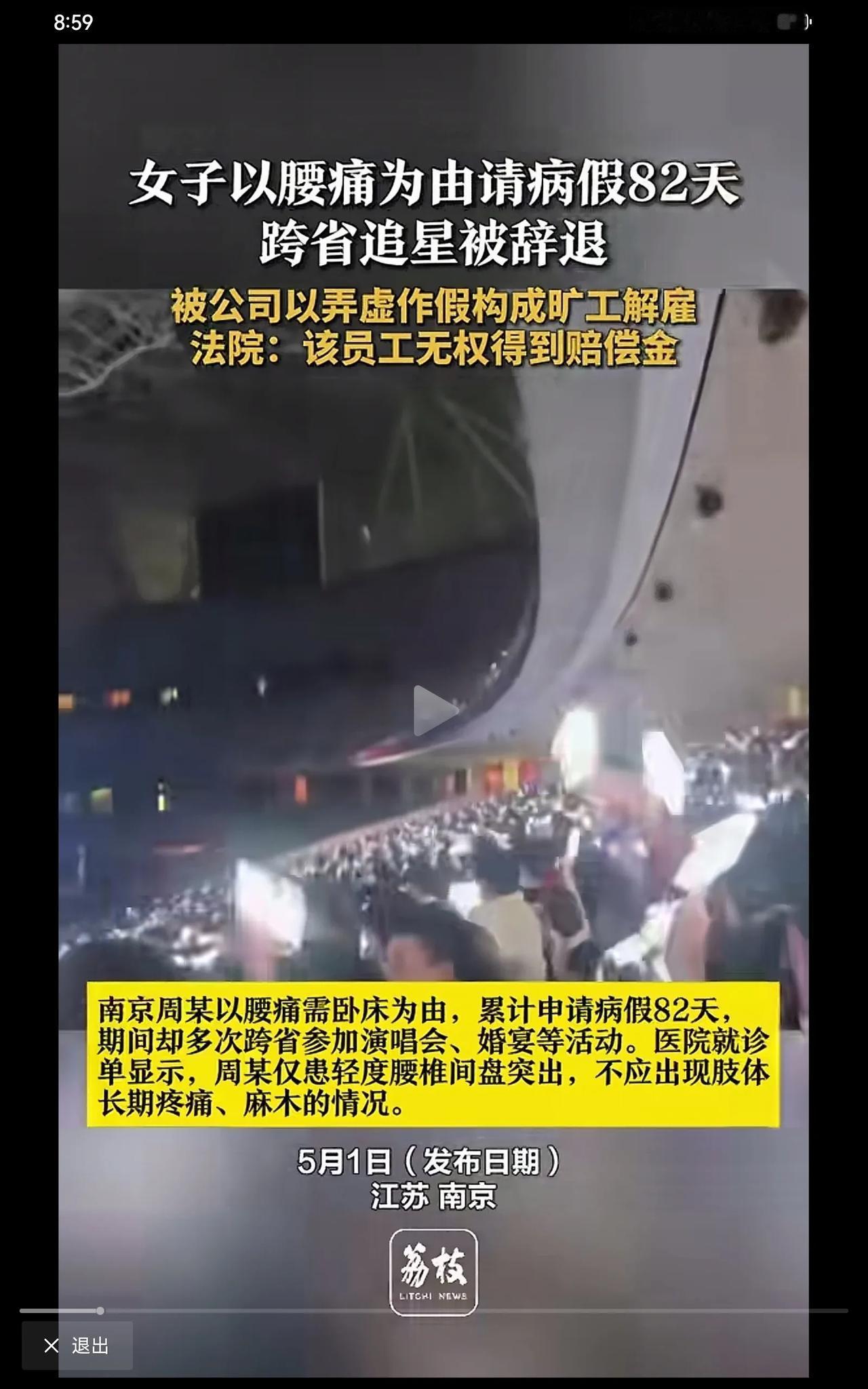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