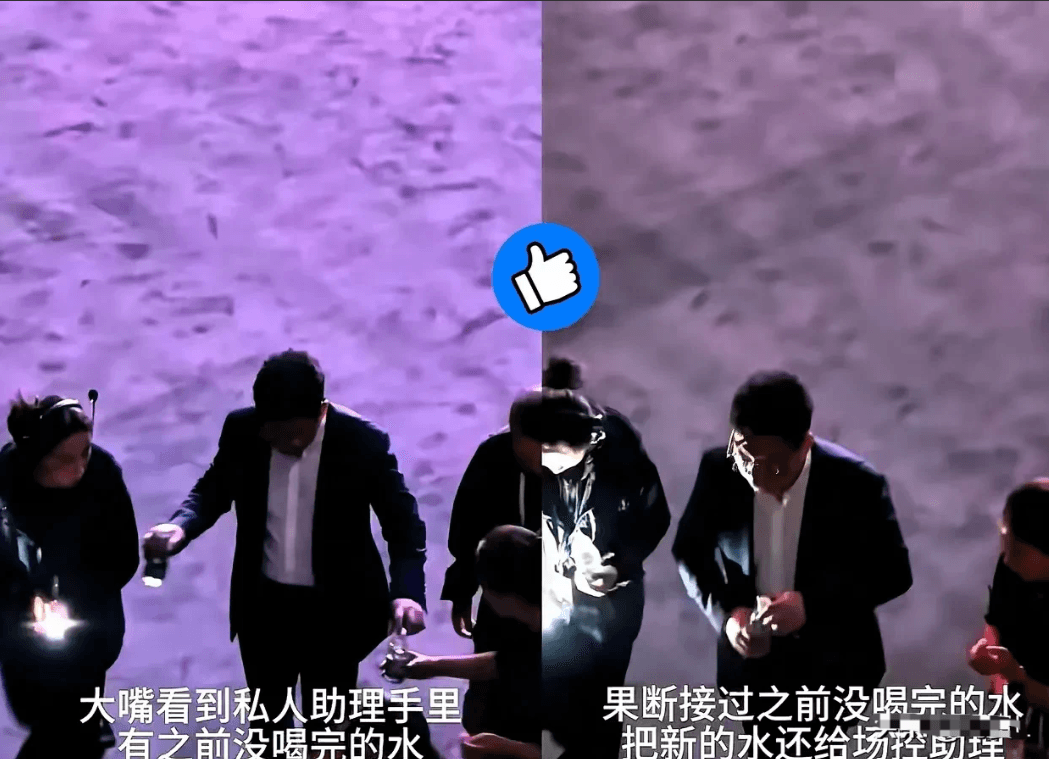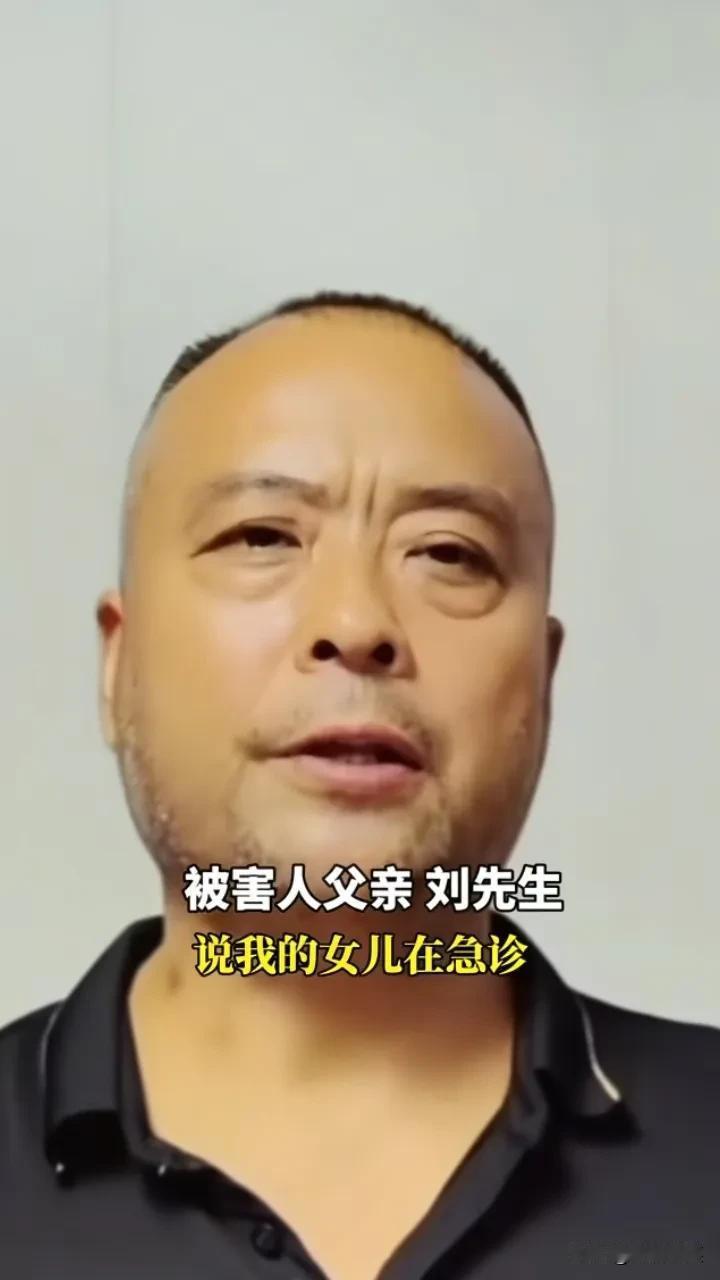1955年,武汉1女大学生放弃城市工作,连夜出逃奔赴新疆,母亲气得生了大病,父亲发誓再也不与她往来,谁料,几年后,女孩回家站在母亲面前,母亲:“你是谁?”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代的中国,城市青年有铁饭碗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吴明珠是那个年代极少数的女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农业科学院工作,端的是人人称羡的“金饭碗”,可就在所有人以为她会稳稳过一辈子的时候,她却做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决定——去了新疆,在那个年代,新疆是偏远、艰苦、条件极差的代名词,很多人一听就退避三舍,但吴明珠主动申请奔赴西部。 她没有告诉家里人,连丈夫也是事后才知道,没有告别,没有铺垫,她就这样带着简单的行李,坐上了开往西北的列车,从北京到吐鲁番,路上花了几天几夜,火车穿过平原、山地、戈壁,最后到了那片被称为“火洲”的地方,那里夏天的温度能轻松超过40度,一脚踩在沙地上,鞋底能被烫化,鸡蛋放在石头上,不用火也能熟。 初到吐鲁番,她住在一间简陋的木板房里,屋子四面透风,晚上风沙灌进来,床单上、桌子上全是灰,水源紧张,洗一次头要提前储好水,吃的也难以适应,当地人以牛羊肉为主,吴明珠从小吃惯了米饭、蔬菜,刚到时常常吃到一半就觉得反胃,有时候忍不住呕吐,她就扶着门框喘口气,再回去继续吃,没有选择,吃不下也得吃,只有适应才能留下。 生活艰苦,但她从没想过回头,她来这里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做一件她觉得重要的事——育种,那时候中国的许多瓜果种子依赖进口,品种不稳定,产量也不高,吴明珠学的是果蔬专业,她知道,如果能培育出适合中国气候、土地的优良品种,不仅能提高产量,还能让农民增加收入。 她开始深入田间地头,走访一个又一个村庄,天气热得让人站着不动都能出一身汗,她却背着包、带着干馕和水壶,走遍了吐鲁番大大小小的生产队,每当发现一个外形特别或者味道出众的西瓜品种,她就采集样本,详细记录特征,有时候为了一个瓜,她要走三十多公里,翻山越岭,甚至在野外露宿。 研究瓜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反复实验、嫁接、筛选,一个新品种从选种到稳定,少则五六年,多的要十几年,吴明珠没有实验室的舒适条件,很多试验工作都是在地里完成的,她戴着草帽,蹲在瓜棚旁记录瓜秧的生长情况,有时候一待就是一整天,她不怕晒,不怕热,只怕错过最佳观察时间。 她怀孕的时候,也没停下工作,挺着肚子在瓜地里走动,汗水湿透了背心,记录本上常常被汗水滴得模糊不清,有人劝她休息,她却坚持继续,孩子出生后,身体虚弱得几乎没有奶水,她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由亲人代为照顾,这是她作为母亲最无奈的决定,但她知道,科研不能停,她的工作有太多等待。 她的丈夫杨其祐原本在北京高校任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看到妻子如此执着,他也选择辞职,来到新疆支援,两人一个搞科研,一个管理后勤和资料,生活虽然清贫,但配合默契,在那片干燥炎热的土地上,他们扎根下来,把一个实验站变成了全国著名的瓜果育种基地。 最初的几年,他们几乎看不到成果,瓜苗失败了无数次,有的品种抗病性差,有的口感不佳,有的产量低,但吴明珠不气馁,每失败一次,她就记录原因,再调整配方,她常说,一颗好种子,是一代又一代人试出来的,终于,在无数次试验之后,她和团队育成了多个优质西甜瓜新品种,像“8424”西瓜、“绿宝石”、“麒麟瓜”这些如今家喻户晓的品种,都是她参与选育的成果。 为了加快育种速度,她还想出了一个创新方法——冬季把瓜苗送到海南岛培育,利用那里的气候优势增加一季生长周期,这个“南繁北育”的模式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科研中,大大提高了效率,她的这种实干精神,在当时的科研圈里极为少见,也为中国瓜果育种打下了坚实基础。 丈夫因长期劳累,年纪尚轻就病倒了,他住院期间还坚持翻译国外最新的农业资料,堆在病床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放下工作,吴明珠赶到医院时,他已无法说话,只是用眼神看着她,仿佛在说,工作继续,她把眼泪咽下,转身又回到了实验田。 国家后来给她颁发奖金,她拿到手里不到一天就捐出了大半,用于支持课题组的研究经费,她说,钱用在地里,才能长出真正的成果。 吴明珠晚年依旧坚持下田,哪怕腿脚不便,也要亲自查看瓜苗长势,有一次在田里摔倒了,她第一反应不是看自己的伤,而是赶紧看怀里抱着的瓜苗有没有摔坏,同行的学生被吓坏了,她却笑着说,瓜苗比她这把老骨头更重要。 她不图名利,也不为奖章,在她看来,那些甜到心头的西瓜,就是对她一生最好的肯定,她把青春、家庭、健康都埋进了这片土地,换来了千家万户的甜蜜滋味。 信息来源:中国妇女报——戈壁“明珠”终无悔 只为甘甜润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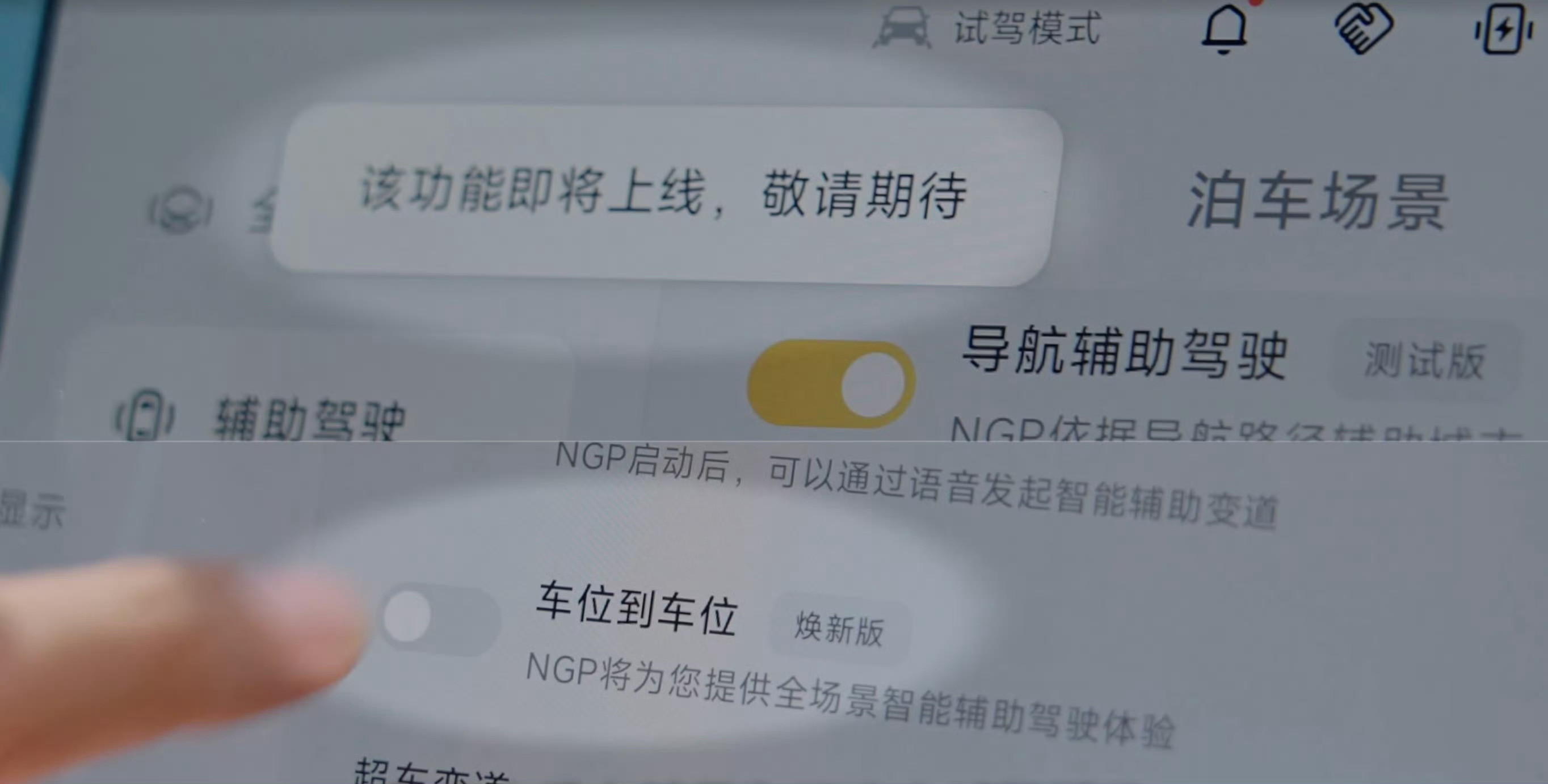
![乐道的交付是快啊,小区里已经有乐道L90了,还是临牌的状态[666]](http://image.uczzd.cn/5554258290714073961.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