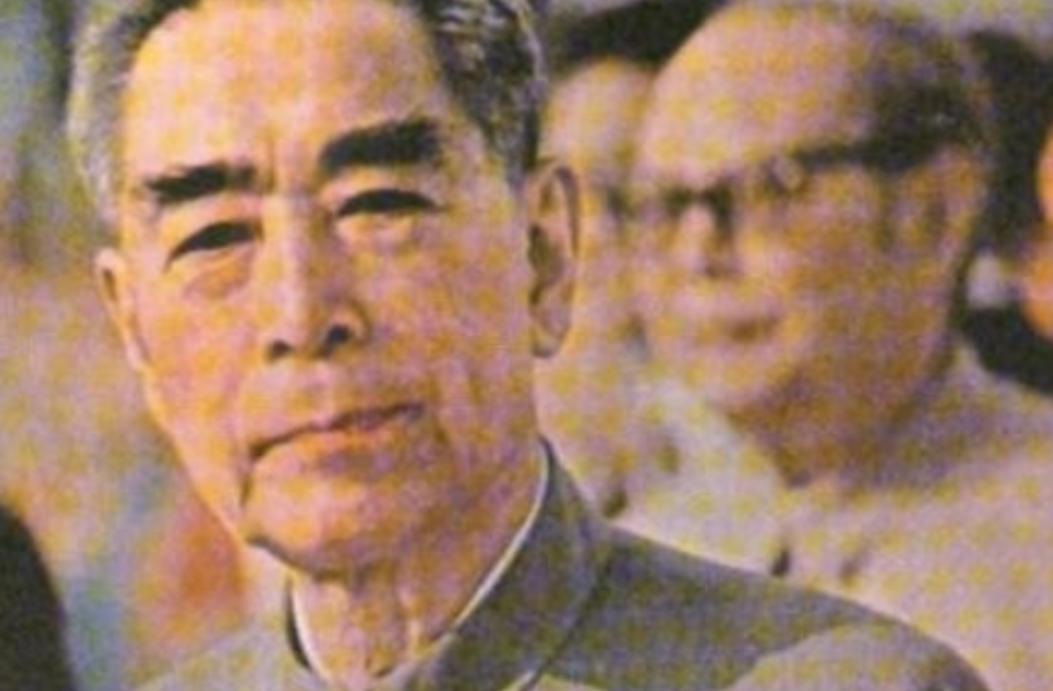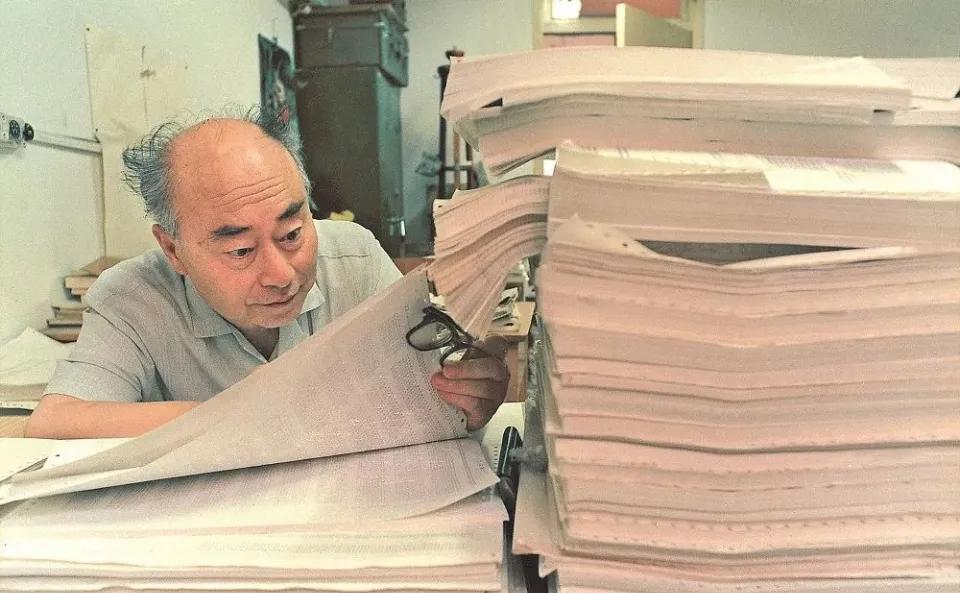一次,六岁小男孩指着电视问妈妈:电视里说的于敏是谁呀?他好厉害呀?孙玉芹伤感地摸着小男孩的头说道:他就是你爸爸呀。这个小男孩就是“氢弹之父”于敏的儿子于辛。对于年幼的于辛来说,“父亲”这个词,起初更像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着天津家里那扇常年灯火通明的房门,门缝里偶尔会飘出清脆的算盘声,还有母亲孙玉芹那句“爸爸在忙国家的大事,别去打扰”的嘱咐。记忆里,总是母亲坚韧的身影,一手牵着他,肩上挂满生活的零零碎碎。于敏先生的家中,时常能见到这样一幅画面:他静坐一隅,思绪早已飘向远方的科研世界,桌上温热的饭菜凉了又热,他却浑然不觉。那种专注和凝重,让小小的于辛不敢靠近。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人,他甚至要被请出去玩,在寒风里站到脸颊生疼,只因父亲的工作需要绝对保密。但父亲并非总是严肃的。难得的假日,他会带着全家去颐和园。在长廊上,他把“岳母刺字”的故事讲得生动又深刻,一颗爱国的种子,就在不经意间埋进了于辛和姐姐的心里。他还曾带回一只烤鸭,自己却没吃几口,只是满足地看着妻儿大快朵颐。这个家,物质上极其简朴。一家人睡铁架床,看的是老旧电视,饭桌上是粗茶淡饭,出门基本靠走。可是在于辛心里,这个家却无比安心。父亲书房里那幅“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墨宝,随着年龄增长,他渐渐读懂了其中的分量。时光回溯至1981年,于辛的人生轨迹悄然来到一处关键分岔口,面前横亘的,正是决定未来走向的高考。面对计算机这一蓬勃兴起的专业领域,他心中始终满怀着热烈的憧憬与向往。然而,父亲于敏却与他进行了一次深谈。父亲没有强迫,而是细致地剖析了当时中国的现状:轻工业落后,大家买布还要凭票,产品单一,毫无竞争力。于敏曾对儿子这般说道:纺织产业的发展,不仅能让老百姓的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更是国家积累建设资金、拓宽外贸出口渠道、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这个领域,太缺人才了。他希望儿子能投身进去,为国家出份力。这番话深深触动了于辛,经过反复思考,他最终在志愿表上填下了纺织专业。大学四年,图书馆成了他的第二个家。1985年毕业后,他被分到轻纺科研单位,从最基层的岗位干起。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凭借着那股钻研劲,主导建立了一套先进的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把生产、销售、财务等环节全部打通。该系统甫一启用便展现出显著效能:销售端的动态数据能即时同步至生产环节,助力生产团队精准校准排产方案。这一联动机制不仅彻底化解了库存冗余与货品断供的双重难题,更推动整体运营成本实现大幅优化。他还非常重视信息安全,带着团队成功挡住了好几次网络攻击,并且建立了一套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让企业走得更稳。岁月流转,母亲孙玉芹先一步离开了。于敏时常睹物思人,心中满是愧疚。纵使工作的节奏再快,事务再繁杂,于辛也从未疏忽对父亲的陪伴。他总会特意留出些时光,与父亲静坐闲谈——或是聊起儿时一同品尝烤鸭的温馨往事,那些藏在香气里的记忆鲜活如初;或是打趣地说起自己年少时的懵懂模样,曾天真地向母亲追问“于敏是谁”。每每当这些趣事从于辛口中道出,父亲总会被逗得眉眼舒展,笑声里满是欣慰与暖意。2019年,这位“愿将一生献宏谋”的功勋科学家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巨大的悲痛中,于辛和家人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父亲生前用过的计算机、印章、钢笔等所有遗物,无偿捐献给国家博物馆。在于辛看来,父亲的一切本就属于国家,他自己继承的,不是物质遗产,而是那份宝贵的“精神火种”。他希望这份火种能被更多人看到,成为整个民族的财富。当下,于辛的身份列表里多了一个崭新的注脚——中国科学精神报告团的一员。他肩负起传承“两弹一星”精神的使命,频繁走进天津工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高校,为年轻的学子们讲述父亲的故事。他的报告生动而深刻,台下的学生们常常听得聚精会神,甚至眼含热泪。他鼓励这些年轻人,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计,共同托举起伟大的“中国梦”。巨人的时代或许已经落幕,但他的精神从未远去,它化作了夜空中永不陨落的星辰,成为后辈们迈向未来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