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书“佛”字,问道吾:“是甚么字?”吾曰:“佛字。”师曰:“多口阿师!”
——《五灯会元》第五卷 药山惟俨禅师
白话直译:一天,药山惟俨写了一个“佛”字,就问一旁的道吾宗智:“这是什么字?”
道吾宗智老老实实的回答:“是个佛字。”
药山惟俨说:“多嘴的家伙!”
 鉴赏评说:
鉴赏评说:是不是觉得当禅师的徒弟好难啊?不回答要被敲打,回答了又被嫌多嘴。
这个字难道不是“佛”字吗?是佛字,不要有丝毫怀疑!药山惟俨并没有说道吾宗智的回答是错的,只是说他“多嘴”。
这句“多嘴”,也不是骂他,也不是教导他佛不可言说,佛不可思量,仅仅是提醒一下:不要只知道意识知解、嘴上回答哦,要体悟真 佛的所在。
禅宗师父不会给徒弟讲道理的,他的一切言行只是提醒、指一指,至于弟子见未见到他所指的那个,他也顾不上那么多,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再说。

因为那个地方,只有自己才能体验,任何人皆无法揣度。
真 佛在哪里呢?就在这个佛字的对面,看见佛字的那个。药山惟俨可没这么说,只是我多嘴。
道吾未觉察到那个“我”,依从大脑着境住相,当然回答“是个佛字”。如果能觉察生起万 法的“我”,还是可以回答“是个佛字”,他难道要回答那是个“我”字不成?
有我无我,都不影响外在的回答,只是区别于内在的自我体验而已。
当然,如果他觉察是师父在勘验自己,也能时时觉察“我”的妙用,当然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来应对。

药山问:“这个是什么字?”
道吾可以不言语,也在桌子上写一个“佛”字,指给师父看。你看见的那个,就是我看见的这个;让你看见的那个,就是让我看见的这个。
道吾也可以把桌上的那个字擦去。擦去字的这个,和看见字的那个是同是别呢?师父你自己看看吧!
当然, 道吾还是可以老老实实的回答:“是个佛字。”
当药山惟俨说出那句“多嘴的家伙”之时,道吾也还他一句:“多嘴的家伙!”
其实,药山的那句“多嘴阿师”本来就可以是自嘲,他不就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吗?佛字,哪个僧人不识呢?既然认识,那你还来问,不是多嘴是什么!

即使道吾打药山一拳,药山也只能一笑了之,因为他也无法反驳啊!挥拳的这个难道不是真 佛吗?如果说不是,那你说说挥拳的这个是什么?如果说是,当然只能欣然领受了。
当然,前提是道吾有那个担当才行。
没有承担当下之人,一定还在纳闷:师父是何用意呢?拿个这么简单的的字来问我?
当药山说他“多嘴”的时候,他唯唯诺诺,又在揣测:师父是何用意呢?是要我放下知见吗?是在给我说佛不可言说吗?
不要打妄想了,它就分分明明的摆在那里,一眼透过啊!正所谓:
“道吾忽尔见先师,问字开拳显妙机。对佛是真 真是佛,药山为破肚中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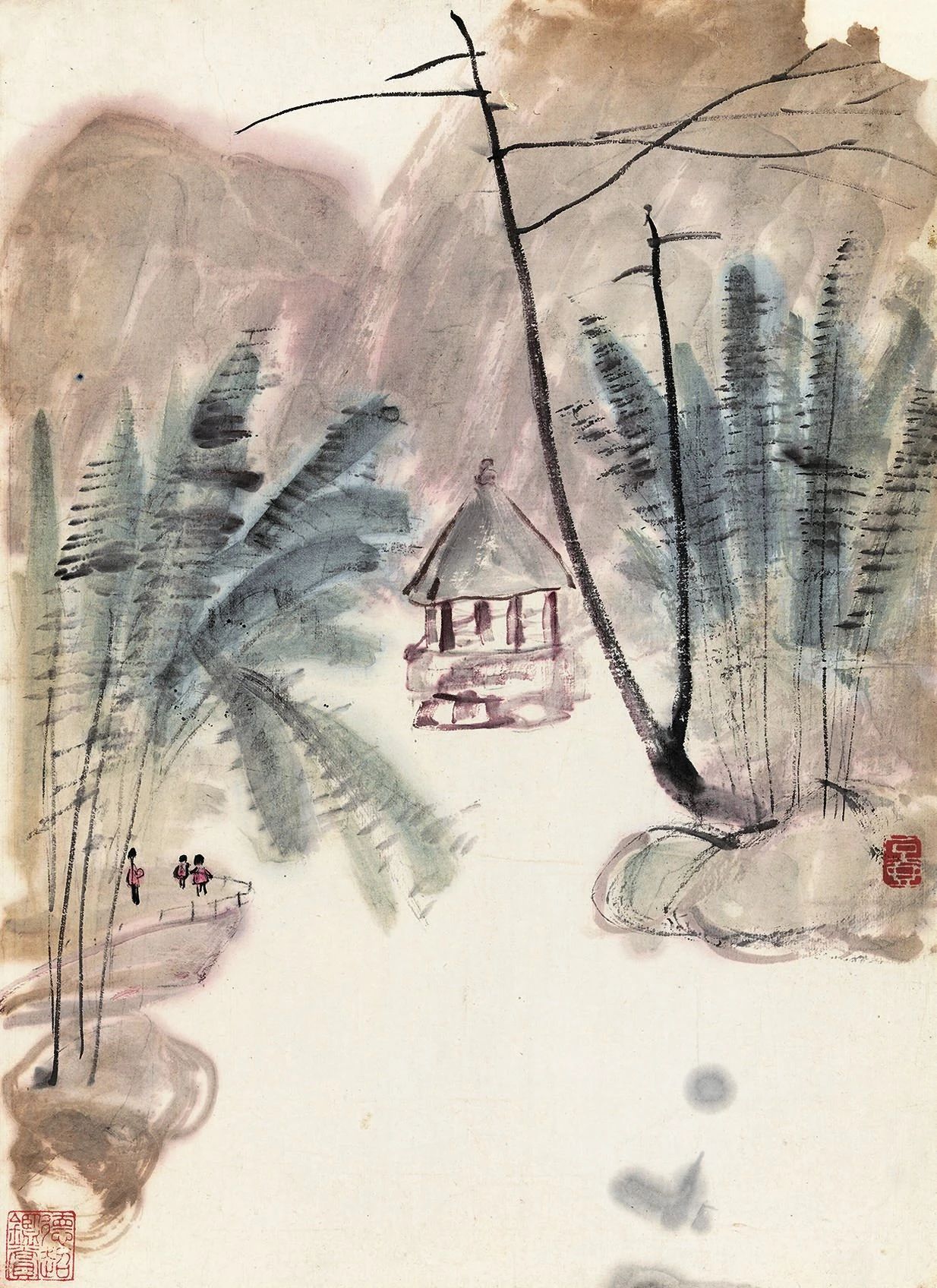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