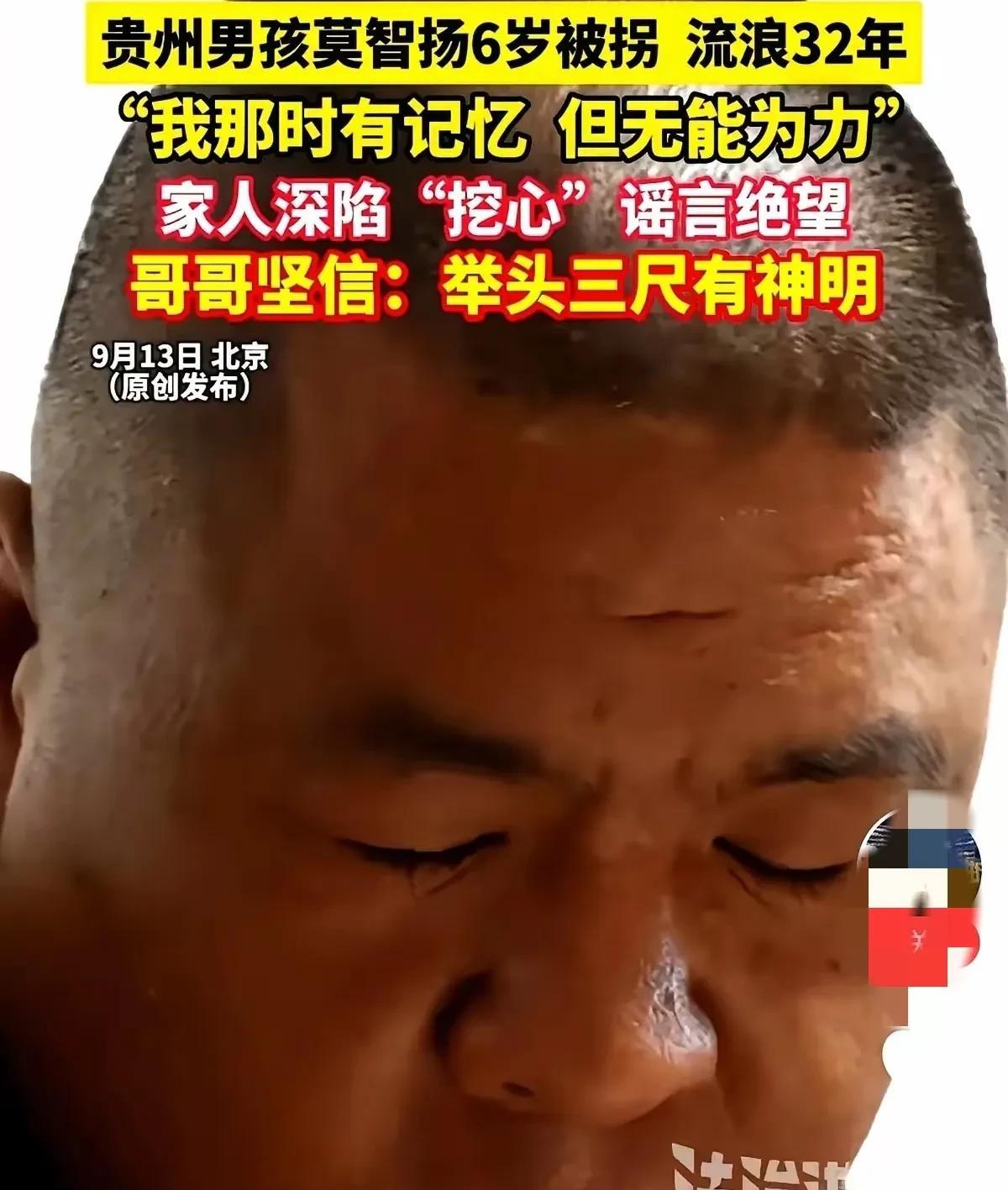1995 年的香港,某栋居民楼 13 楼窗台,28 岁的乐韵张开双臂,带着一声 “死了吧!死了吧!” 的嘶吼纵身跳下。 楼下,她的母亲一边哭一边骂:“白瞎这么好的脸,连个大款都没傍上,活着有啥用!” 直到看见女儿倒在血泊里,母亲的哭声才变了调,可那双曾无数次催着她 “找好出路” 的手,再也拉不回这个年轻的生命。 乐韵打小就长得扎眼,街坊邻居路过她家院儿,总忍不住探头看,小姑娘梳着羊角辫,一双丹凤眼亮得像浸了水,跑起来裙摆一飘,连卖冰棍的大爷都愿意多给她一块糖。 可母亲不稀罕这些 “虚的”,从乐韵十岁起就天天念叨:“长得好不算本事,要嫁得好、走得远,去香港、去国外,那才叫有出息。” 她还特意给乐韵报了礼仪班,不是教跳舞唱歌,而是教 “怎么跟有钱人说话” “怎么用刀叉才不丢面子”,乐韵不喜欢,母亲就拧着她的耳朵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妈是为你好。” 1983 年,16 岁的乐韵在报纸上看到《红楼梦》剧组选角的消息,瞒着母亲报了名。 试镜那天,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一进考场,原本吵吵嚷嚷的屋子突然静了。 导演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半天,让助理拿王熙凤的戏服给她试穿。 穿上凤冠霞帔的乐韵,往镜头前一站,抬手拢头发的动作都带着股泼辣劲儿,导演当场拍桌:“这就是我要的王熙凤!” 连当时也在争这个角色的邓婕,都笑着说:“我跟她比,少了点那股子劲儿。” 剧组把剧本送到乐韵家时,母亲回来了。翻了两页剧本,她把本子往桌上一摔:“演个戏有什么用?天天在剧组熬着,能熬出大富大贵吗?” 正好那阵子,香港影星罗烈来内地拍戏,通过朋友认识了乐韵。 罗烈比乐韵大二十多岁,却很会说情话,天天捧着玫瑰来剧组,说:“你这么好的条件,在大陆可惜了,跟我去香港,我让你当女主角,保准你比张曼玉还红。” 他还拉着乐韵的手承诺:“我回去就跟我老婆离婚,以后我只对你一个人好。” 乐韵被说得动了心,尤其想到母亲天天念叨的 “香港梦”,更是觉得这是个机会。 导演组舍不得她,劝了又劝:“就算不演王熙凤,演尤三姐也行,戏份不多但出彩,以后肯定有机会。” 可乐韵摇了头,背着母亲收拾了两件衣服,就跟着罗烈去了香港。 一到香港,罗烈就变了样。他没带乐韵去影视公司,反而把她安置在郊区的一栋小别墅里,说:“你先适应适应粤语,等我把家里的事处理好,就带你见导演。” 乐韵信了,每天在家对着电视学粤语,笔记本上写满了拼音标注,比如 “你好” 写成 “雷猴”,“谢谢” 写成 “唔该”。 可等了一个月,罗烈还是没提拍戏的事,每次问起,他就找借口:“再等等,我在跟嘉禾的老板谈,要给你找最好的剧本。” 乐韵偷偷溜出别墅想找影视公司,可到了地铁站就慌了,听不懂广播,看不懂路牌,只能灰溜溜回去。 直到有天,一个陌生女人带着佣人找上门,手里攥着她和罗烈的照片,指着她骂:“狐狸精,抢别人老公还敢住这!” 乐韵这才知道,罗烈根本没打算离婚,只是把她当 “金丝雀” 藏着。 罗烈得知后,连夜搬空别墅里的东西,还逼乐韵还之前给的钱。她身无分文,只能在旧楼租间十几平米的房,楼梯又陡又窄,下雨天还漏雨。 托人找了家小影视公司,可粤语不流利,只能演 “路人甲”“女配角的闺蜜”,最多一次,一整部戏就三句台词。 1988 年,母亲从内地来香港找她。看见女儿住的地方,母亲脸当场拉下来,做饭时天天唠叨:“隔壁安徽丫头,来两年就嫁老板住复式楼,你呢?演小角色,连件像样衣服都没有!” 有次酒楼请乐韵剪彩,给两千块,母亲催着去,乐韵不愿意:“我是演员,不是剪彩的花瓶。” 母亲气得摔碗:“花瓶怎么了?能换钱!你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还端架子!” 之后几年,乐韵的日子越来越难。香港影视圈遇冷,她几个月接不到戏,只能打零工糊口。 母亲的抱怨也越来越多,有时指着她鼻子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不争气的,空有张脸,一点用没有。” 乐韵想反驳,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 她也问自己,要是当初没跟罗烈来香港,是不是早成了家喻户晓的演员? 1995 年那天下午,乐韵好不容易接到个小角色试镜通知,却发现母亲把她唯一一双干净高跟鞋扔了 —— 母亲说 “试镜有啥用,白费功夫”。 看着地上的鞋,听着厨房的骂声,乐韵突然觉得累了。她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车流霓虹,想起 16 岁试镜时导演的笑容,最后喊出那句 “死了吧”,纵身跳了下去。 直到现在,还有人记得乐韵 —— 那个本该演王熙凤的姑娘。 信源:她是被钦点的王熙凤 一心为爱赴港|她是|钦点——川北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