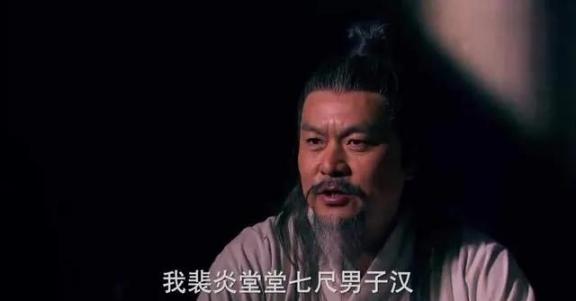公元757年,年过古稀的太上皇李隆基在六百名侍卫的护送下回到了长安,新帝李亨带了三千精锐前来迎接。见李亨这阵势,李隆基赶忙让侍卫们丢开刀剑投降,他勉强笑着说:“我只是想回宫安度晚年。”这话说完,二人便打算迈步进宫,可谁走在前面呢?父子二人又僵持住了,只能尴尬地问群臣,可大臣们也支支吾吾,没人敢回答。 李隆基是什么人?咱们熟悉的唐玄宗啊,前半辈子那是妥妥的“天选之子”。年轻的时候,以“阿瞒”自居,把曹操当偶像,政治手腕那叫一个漂亮。平定了韦后和太平公主的乱子,一手开创了万国来朝的“开元盛世”。那会儿的大唐,就是全世界最亮的星,而他,就是站在星光最中央的那个人。 可人呐,最怕的就是在功劳簿上躺平了。到了晚年,李隆基明显有点飘了,朝政懒得管,身边围绕着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人,最终亲手点燃了安史之乱这把大火。公元755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叛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长安。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皇帝,一夜之间变成了仓皇出逃的难民。 逃亡路上,在马嵬驿那个地方,发生了改变他一生的事。愤怒的士兵们杀了杨国忠,又逼着他赐死了心爱的杨贵妃。这事儿对李隆基的打击是致命的,不仅是失去了爱人,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连身边人的性命都保不住了,皇帝的权威碎了一地。也就是从那一刻起,父子俩的命运走向了不同的岔路口。李隆基继续南下成都,而太子李亨,则选择了北上灵武。 李亨这个太子当得非常憋屈。在爹的光环下活了快二十年,战战兢兢,生怕哪天就被废了。安史之乱对他来说,既是危机,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灵武,他没等远在成都的李隆基发话,直接就自己登基当了皇帝,遥尊李隆基为太上皇。这招“先斩后奏”玩得相当高明,说白了,就是把生米煮成了熟饭,你李隆基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 李隆基在成都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史书上说他“初闻之,大惊”,然后才慢慢接受现实。能不惊吗?自己还是名义上的皇帝,儿子却另立了中央,这在古代可是妥妥的谋逆。但他手里没人没兵,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这个“太上皇”的头衔。 两年后,公元757年,在郭子仪、李光弼这些名将的浴血奋战下,长安终于收复了。李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成都,把老爹接回来。这事儿必须办,而且要办得风风光光。为啥?这是政治需要,关乎他的皇位正统性。 把太上皇接回首都供养起来,才能向天下人证明,他李亨不是篡位,是临危受命,父慈子孝的戏码必须演足。 李隆基回到咸阳,看到儿子那三千精兵的阵仗,心里哪能不明白?他立刻让自己的六百侍卫放下武器,这一个动作,就是最明确的政治表态:我不跟你争,我认输了。 他那句“我只是想回宫安度晚年”,听着心酸,其实也是说给李亨和天下人听的,我老了,玩不动了,只想找个地方养老。 父子俩泪眼婆娑,上演了一出久别重逢的感人戏码。李隆基甚至亲自给李亨披上龙袍,彻底完成了权力的交接仪式。可真到了要进宫门的那一刻,新的尴尬又来了:谁走在前面? 这个问题,大臣们谁敢回答?说让太上皇走前面,那是遵循孝道和旧制,可新皇帝李亨能乐意吗?这不是打他的脸,说他名不正言不顺吗?可要是说让新皇帝走前面,那又置太上皇于何地?这是公然把“孝道”踩在脚下。这道题,怎么答都是错的。 最后还是老太监高力士有眼力见,出了个主意,说请太上皇从夹城西门进兴庆宫,请皇帝从正门丹凤门入大明宫。这一下,既分开了路线,又各自给了台阶,算是暂时化解了危机。 但回到长安后的李隆基,真的能“安度晚年”吗?显然不能。起初,李亨对他还算不错,让他住进了他熟悉的兴庆宫,朝中老臣、旧日亲信也时常去看望他。李隆基毕竟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盘根错节的势力还在。他时不时跟人聊聊天,喝喝酒,甚至还会对朝政指点一二。 这种日子没过多久,就碍着别人的眼了。这个人就是李亨身边的大红人,宦官李辅国。李辅国是靠着拥立李亨上位的,他最怕的就是李隆基东山再起,那他这个“从龙之功”可就打了水漂。于是,他开始在李亨耳边吹风,说太上皇跟外臣来往过密,恐怕对陛下不利。 被李辅国这么一挑唆,疑心病就犯了。公元760年,李辅国假传圣旨,强行把李隆基从兴庆宫迁到了更偏僻、更冷清的太极宫甘露殿,基本上就是软禁了起来。更狠的是,他还把跟随李隆基一辈子的老仆人高力士流放了。 这下,李隆基彻底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他被囚禁在深宫里,身边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昔日的辉煌、曾经的雄心壮志,都成了过眼云烟。他常常一个人登上宫楼,呆呆地望着远方,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许是在后悔自己晚年的昏聩,或许是在思念马嵬驿那个香消玉殒的丽人,又或许,是在感叹这世态炎凉、父子无情。 两年后,公元762年的春天,这位曾经创造了一个时代的伟大帝王,在无尽的孤独和抑郁中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