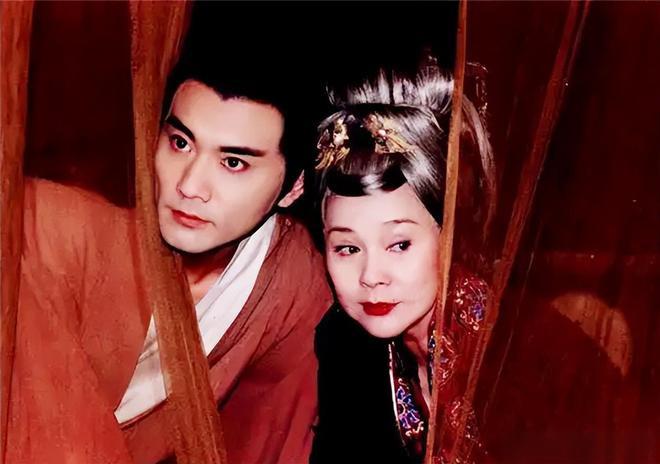643年,太子李承乾谋反,按律当诛杀,李世民心如刀绞,质问:“皇位本会传给太子,你为何如此逼宫,是等不及了吗?”李承乾却意味深长:“我不想落得和前太子李建成一样的下场!”李世民神色大变。 殿内的烛火“噼啪”一声炸开,火星溅在金砖上,转瞬就灭了。李世民盯着阶下被铁链缚住的儿子,那件曾绣着五爪蟒纹的太子袍,此刻沾满了尘土与血污,像极了二十多年前玄武门那场乱战里,溅满泥浆的铠甲。他忽然觉得喉咙发紧,原本到了嘴边的斥责,全堵在胸口,变成了一阵发颤的呼吸。 李承乾抬起头,脸上没有阶下囚的惶恐,反而带着一种破罐破摔的坦然。他的左眼因为前些天的打斗肿得老高,视线只能偏着看父亲,可那目光里的东西,让李世民不敢细想——是警惕,是恐惧,还有一丝藏不住的“预判”。就好像从他被立为太子的那天起,就知道自己迟早会走到这一步。 “父皇总说,儿臣是嫡长子,这江山迟早是我的。”李承乾的声音沙哑,带着铁链拖动的哗啦声,“可父皇忘了,当年大伯也是嫡长子,也是先帝钦定的太子。” “住口!”李世民猛地拍了龙案,案上的玉圭震得跳起来,滚落在地。他很少在人前失态,可“大伯”这两个字,像一把生锈的刀,精准地捅进了他最不愿触碰的伤口。二十三年前的那个清晨,玄武门的箭雨,李建成倒在马下的模样,李元吉临死前的嘶吼,还有父亲李渊在太极宫垂泪的脸,一瞬间全涌了上来。 他当年踩着兄弟的血登上皇位,后来又用了无数的功绩去掩盖这段过往——修《贞观政要》,纳谏如流,平突厥,治天下,可到头来,自己的儿子,竟然在怕重蹈李建成的覆辙。 李承乾却没停,反而笑得更苦:“父皇不用恼,儿臣知道这话逆耳。可这些年,父皇看李泰的眼神,儿臣不是没看见。他府里的门客越来越多,赏赐越来越厚,甚至有人在朝上说,‘泰贤,当立’——这不就是当年有人说‘世民贤,当立’的翻版吗?” 李世民的手指攥得发白,指节抵着龙案的木纹,几乎要嵌进去。他确实偏爱李泰,这个儿子聪明,会讨他欢心,不像李承乾,自小就有足疾,性格又刚愎,总让他觉得“不够完美”。 可他从没想过要废黜太子,毕竟李承乾是他和长孙皇后的第一个儿子,是他亲手立的储君。可他忘了,他自己当年,也是从“秦王”一步步走到“太子”,再到“皇帝”的。他当年能凭着军功和威望,动摇李建成的地位,如今李泰凭什么不能? “儿臣不敢等。”李承乾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委屈,“李泰的人在府外盯了我半年,我宫里的太监,有三个被他收买了,连我吃的药,都要先经他的人过目。父皇,您让我怎么等?等他像当年您对付大伯一样,给我安个‘谋反’的罪名,然后在某个清晨,让我死在宫门外吗?” 李世民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长孙皇后临终前的模样。她拉着他的手,反复叮嘱“善待太子,勿起争端”,可他终究是没做到。他总以为,自己能比父亲李渊做得好,能平衡好儿子们的关系,可到头来,还是让权力的猜忌,在自己的家庭里生了根。他当年恨李渊偏心李建成,可如今,他不也在偏心李泰吗? 殿外传来一阵雨声,淅淅沥沥的,打在琉璃瓦上,带着深秋的凉意。李世民睁开眼时,看见李承乾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哭。这个从小被他寄予厚望的儿子,此刻像个迷路的孩子,再没有半点太子的架子。 他忽然想起李承乾小时候,因为足疾走路不稳,摔在御花园的石子路上,却咬着牙不肯哭,非要自己爬起来。那时候他还夸过儿子“有骨气”,可现在,这骨气却变成了逼宫的勇气。 “你可知,谋反是灭族之罪?”李世民的声音软了下来,带着一种连自己都没察觉的疲惫。他知道,按律李承乾必死,可他下不了这个手。这不仅仅是父子情,更是一种恐惧——他杀了兄弟,若再杀儿子,后人会怎么评说他?会说他是个为了皇位,连亲人都能斩尽杀绝的暴君吗? 李承乾摇摇头:“儿臣知道。可与其等着被李泰害死,不如拼一把。就算输了,至少死得明白,不像大伯,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输在了‘嫡长子’这三个字上。” 李世民沉默了。他挥了挥手,让侍卫把李承乾带下去,关押在东宫的别苑里,暂时不议罪。看着儿子被拖走的背影,他忽然觉得很累。他治得了天下,却治不好家里的猜忌;他能让百官臣服,却留不住儿子的信任。当年他以为,只要自己做得足够好,就能弥补玄武门的过错,可现在才明白,有些东西一旦种下,就会像影子一样,跟着下一代走。 后来,李世民没有杀李承乾,只是把他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他也没立李泰为太子,反而立了年幼的李治——他怕李泰当了皇帝,会像自己当年一样,对兄弟下手。可就算这样,他心里的那道坎,终究是没过去。每当夜深人静,他坐在太极宫的窗边,总能听见玄武门的箭雨声,还有李承乾那句“不想落得和李建成一样的下场”,在耳边反复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