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阎应元守江阴孤城,有满人大将全身铁盔铁甲手持大刀登城斩杀数人,其铁甲厚重刀枪不能入,应元命士卒以钩镰枪环而攻之,铁钩如林,勾住铁甲将其拖倒不能站立,刀斧手持重斧斫(砍)其颈,终断其头杀之,脱盔称其头,重十八斤。 那会儿江阴城被围已经两个多月了。城墙垛口处的砖石被炮轰得坑坑洼洼,守城的百姓和士兵们眼睛里全是红血丝,手里的刀枪磨得发亮,却也磨不去满身的疲惫。城外的号角一吹,大家就知道,新一轮攻城又要来了。 这天晌午,日头毒得像要把人烤化。满人那边突然没了动静,城墙上的人正纳闷,就见一架云梯“哐当”一声搭在了垛口上。紧接着,一个黑铁塔似的身影顺着云梯往上爬,铁甲片子碰撞着,发出“哗啦啦”的响声,隔老远都能听见。 “是那铁壳子!”有个老兵喊了一声,声音都发颤。前几天这满人大将就试过攻城,一刀劈断了城楼的木柱,有三个弟兄没躲过,当场就没了气。这会儿他爬得飞快,转眼就露出了戴着铁盔的脑袋,手里的大刀一晃,寒光直晃人眼。 “砍他!”一个年轻后生举着长刀就冲了上去,刀刃结结实实地劈在那大将的铁甲上,只听“当”的一声脆响,刀被弹飞了老远,后生自己反倒震得虎口发麻。旁边两个士兵挺着长枪刺过去,枪尖戳在铁甲上,跟戳在石头上似的,只留下两个白印子。 那大将“嗬嗬”笑了两声,大刀横扫过来,一个士兵躲闪不及,被劈中肩头,惨叫着滚下了城墙。另一个想往后退,被他一把抓住衣领,像拎小鸡似的提起来,狠狠掼在城砖上。城墙上顿时乱了阵脚,有人往后缩,有人急得直跺脚,嘴里喊着“杀不死啊,这可咋整”。 就在这时,阎应元站在城楼台阶上,手里的令旗猛地一挥。他眼睛瞪得溜圆,嗓子因为连日喊话有些沙哑,却透着一股子狠劲:“慌什么!拿钩镰枪来!” 几个扛着钩镰枪的士兵听见指令,立马往前冲。这钩镰枪本是用来勾马腿的,枪头带个弯弯的铁钩,锋利得很。阎应元指着那满人大将,又喊:“别硬碰硬,勾他铁甲缝!” 士兵们一下子明白了。三个人一组,挺着钩镰枪绕到那大将身后。最前面的一个瞅准铁甲连接处的缝隙,猛地把铁钩送了进去,使劲一拧。“咔哒”一声,铁钩死死勾住了铁甲。 那大将察觉不对,回身想砍,可另外两根钩镰枪已经从左右两边伸了过来,一根勾住他的胳膊,一根缠住他的腿。“使劲拽!”有人喊了一声,三个士兵一起往后拉,那大将本来站得稳稳的,被这么一拽,顿时一个趔趄。 更多的钩镰枪围了上来,铁钩密密麻麻地挂在他身上,像是给这黑铁塔缠上了一圈铁荆棘。“一二三!”不知是谁喊了声号子,十几个人一起发力,那大将再也站不住,“噗通”一声摔在城砖上,铁甲撞得地面咚咚响。 他想挣扎着爬起来,可铁钩勾得太紧,一动就扯得铁甲“嘎吱”响,怎么也起不来。这时候,两个扛着重斧的壮汉挤了过来,他们是城里铁匠铺的伙计,平时抡大锤习惯了,这会儿双手举着斧头,眼睛瞪得通红。 “为了江阴!”其中一个喊了一声,重斧带着风声劈了下去,正砍在那大将的脖颈处。铁甲再厚,脖颈衔接的地方终究是弱点,只听“咔嚓”一声脆响,斧刃陷了进去。另一个壮汉紧接着补上一斧,这一下更狠,直接把脑袋劈了下来。 城墙上静了片刻,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有人捡起那颗人头,摘了铁盔,找了杆秤一称,好家伙,十八斤重!那铁盔被扔在一边,阳光下闪着冷光,可这会儿在守城的人眼里,再厉害的铁甲也挡不住拼命的劲头。 阎应元抹了把脸上的汗,往城下看了看,满人因为主将被杀,攻城的势头明显弱了。他转过身,拍了拍那几个用钩镰枪的士兵:“好样的!记住了,再硬的骨头,也有能啃动的法子。” 城根下,百姓们听见杀了那铁壳子大将,纷纷提着水和干粮往城墙上送。有个老婆婆颤巍巍地给士兵递上一块饼:“孩子们,吃饱了,咱接着守!” 就是凭着这股子劲,江阴孤城硬是守了八十一天。后来有人说,那天斩下的不光是一颗人头,更是斩碎了满人“不可战胜”的气焰。城墙上的血迹干了又湿,可守城的人眼里的光,从来没暗过。 出处:据《江阴城守纪》及地方文献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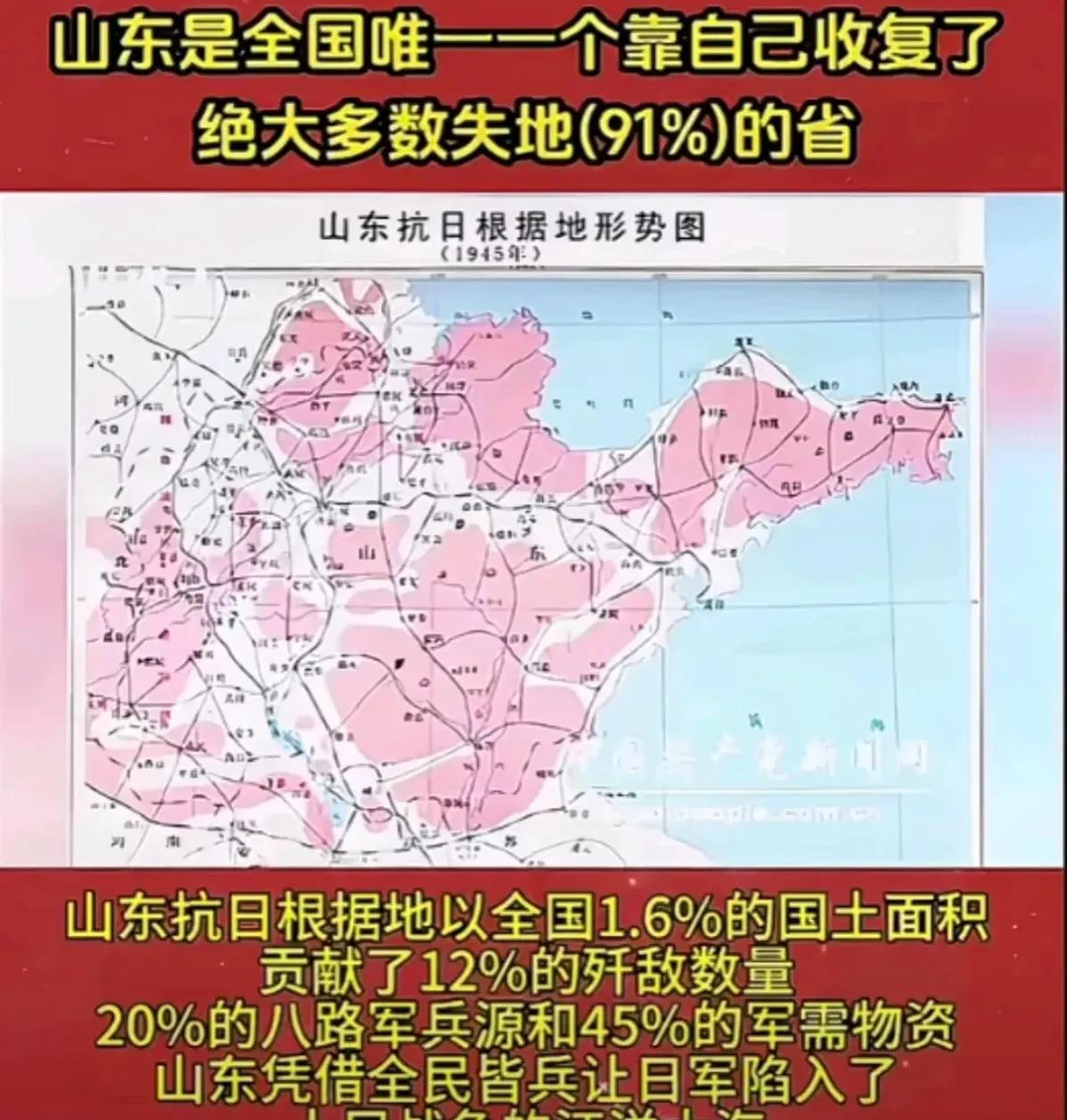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