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四川,一95岁老人公园散步,遇到一位96岁老人,两人闲聊时竟发现她们是74年前进藏的同一批女兵,谁知,一番交流后又知道一个天大的消息!两位老人顿时相拥而泣! 公园里,两个老太太在长椅上晒太阳,95岁的闫家琪和孙女坐在一起,听着不远处广场舞的音乐,眯着眼笑。没过一会儿,长椅另一头也坐下个头发全白的老人,两人对上眼神,都笑了笑。 随便聊了几句,发现对方只比自己大一岁,96岁的彭家英和95岁的闫家琪一下子就亲近起来。话题很自然地滑到了年轻的时候,闫家琪随口说自己当过兵,谁知彭家英一下来了精神:“我也当过兵!进藏修路的!” 空气仿佛停顿了一下,“你说的……不会是1950年那会儿吧?”闫家琪的心跳漏了一拍,“对呀,解放军十八军,我还是文工队的。” 听到“十八军文工队”这几个字,闫家琪猛地站了起来,手都有些抖,一把抓住彭家英:“我也是十八军文工队的!” 两个加起来快两百岁的老人,就这么揭开了一个尘封了74年的身份谜团。更巧的是,她们不仅是战友,彭家英还是闫家琪当年的班长,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兵,七十多年后竟在公园的长椅上才算真正“认识”。四目相对,两位老兵紧紧抱在一起,眼泪止不住地流。 她们很快发现,虽然同在一个文工队,彭家英还是班长,但在当年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两人其实并不熟。部队一进藏就分散作业,任务重得喘不过气,根本没有串门聊天的机会。 彭家英是湖南人,当年从长沙参军,被分到甘孜工地,每天就是背石头、修路,一双手全是茧子。而闫家琪是成都本地人,参军的初衷很实在,就是为了一口饱饭。 她的队伍负责啃川藏线上最硬的骨头,雀儿山段,后来她又调去附近的医院当了护士。听起来,她们的青春轨迹似乎并无交集。 彭家英聊起1951年在甘孜的一次窑洞塌方,她被埋了半截,差点没命。闫家琪听到这儿,猛地一怔,脱口而出:“原来那天塌方,里面有你!我当时就在附近的医院,听说文工队出事了,我们护士都跑过去帮忙,我还给伤员送过药!” 彭家英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记忆瞬间被激活:“怪不得!我就记得有个小护士给我包扎,还塞给我一块红糖,说吃了就不疼了。当时我还想,这小姑娘心真好!” 七十多年前,在生死一线的雪域高原,一个是被埋在土里的重伤员,一个是匆匆赶来救援的小护士。她们以这种方式擦肩而过,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却在危难中完成了战友间最真切的扶持。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她们聊起在高原上开垦荒地,用最原始的工具种出粮食;聊起劳动间隙用歌声驱散疲惫,用舞蹈点燃希望。那些熟悉的旋律,就是她们刻在骨子里的青春。 进藏后不久,两人就因工作调动彻底分开,这一别,就是74年。可当年那份在冰天雪地里相互取暖的情谊,早已沉淀下来,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当聊起牺牲的战友时,气氛沉重下来。彭家英轻声说起她最好的姐妹何淑芬,就在那次塌方中牺牲了。这么多年,她一直不知道何淑芬埋在哪里,这成了她心里一个巨大的疙瘩。 “我知道!”闫家琪突然说,“前年我儿子去西藏,特地帮我找到了甘孜烈士陵园。我们十八军牺牲的战友都在那儿,何淑芬的名字就刻在碑上。” 彭家英听到这话,浑身一颤,压抑了几十年的情绪瞬间决堤,抱着闫家琪泣不成声。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这份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牵挂,在今天的重逢中找到了归宿。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们被同一面旗帜召唤,怀着同样的理想,踏上了同一片蛮荒的土地。她们一起挨过饿,一起受过冻,一起在鬼门关前擦肩而过,也一起埋葬过身边最亲密的战友。 这种经历,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同事”或“朋友”关系。它是一种身份认同,是一种生死相托的信任。每个从那段岁月走出来的人,都是幸存者,也都背负着逝者的记忆。 他们的生命,从踏上进藏路的那一刻起,就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所以,74年的岁月可以改变容貌,可以模糊记忆,却无法磨灭这种烙印在灵魂深处的连接。 当闫家琪和彭家英再次相遇,她们不需要重新认识,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关键词,就能瞬间唤醒沉睡的过去。因为她们辨认的不是对方的脸,而是彼此身上那股相同的、属于十八军老兵的气息。 聚会后,儿孙们张罗着让两位老人常来常往。她们碰了碰茶杯,约好明年清明一起去甘孜,看看那些长眠的战友。对她们而言,这辈子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但只要还活着一天,心里装着的,就永远是那段激情与牺牲交织的雪域青春,和那些回不来的兄弟姐妹。 信源:央视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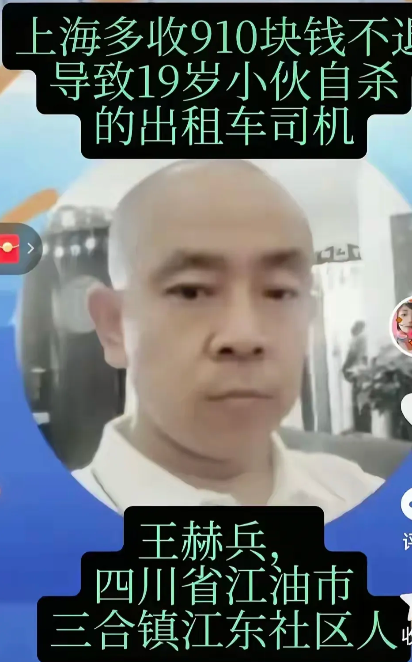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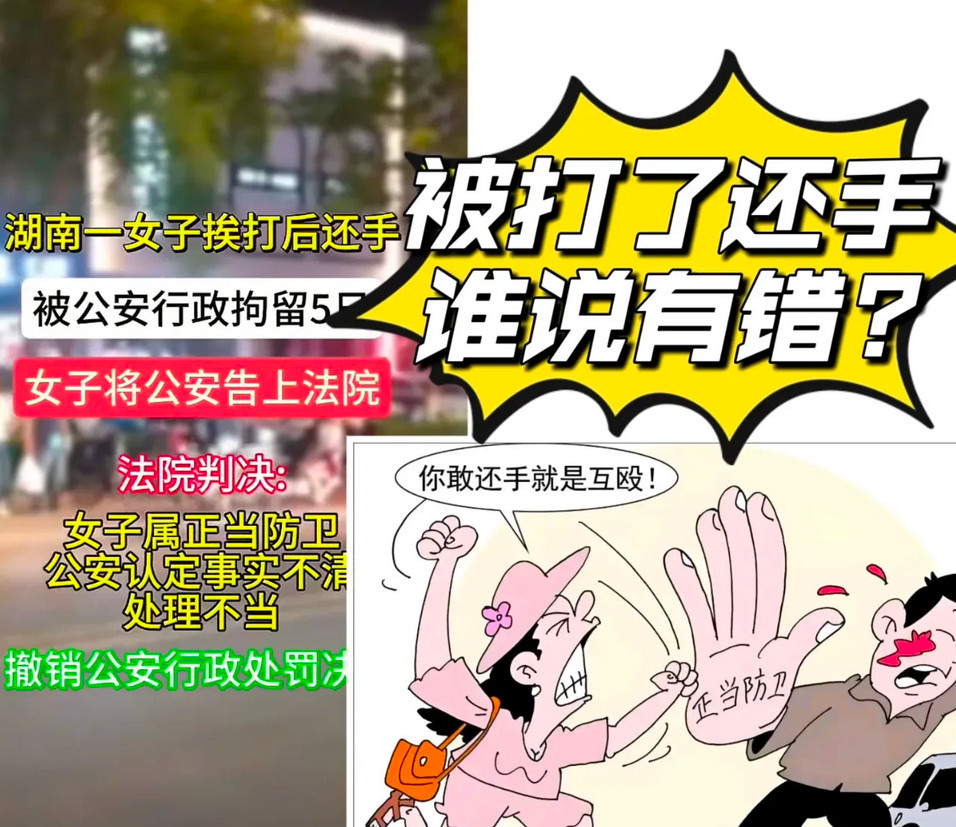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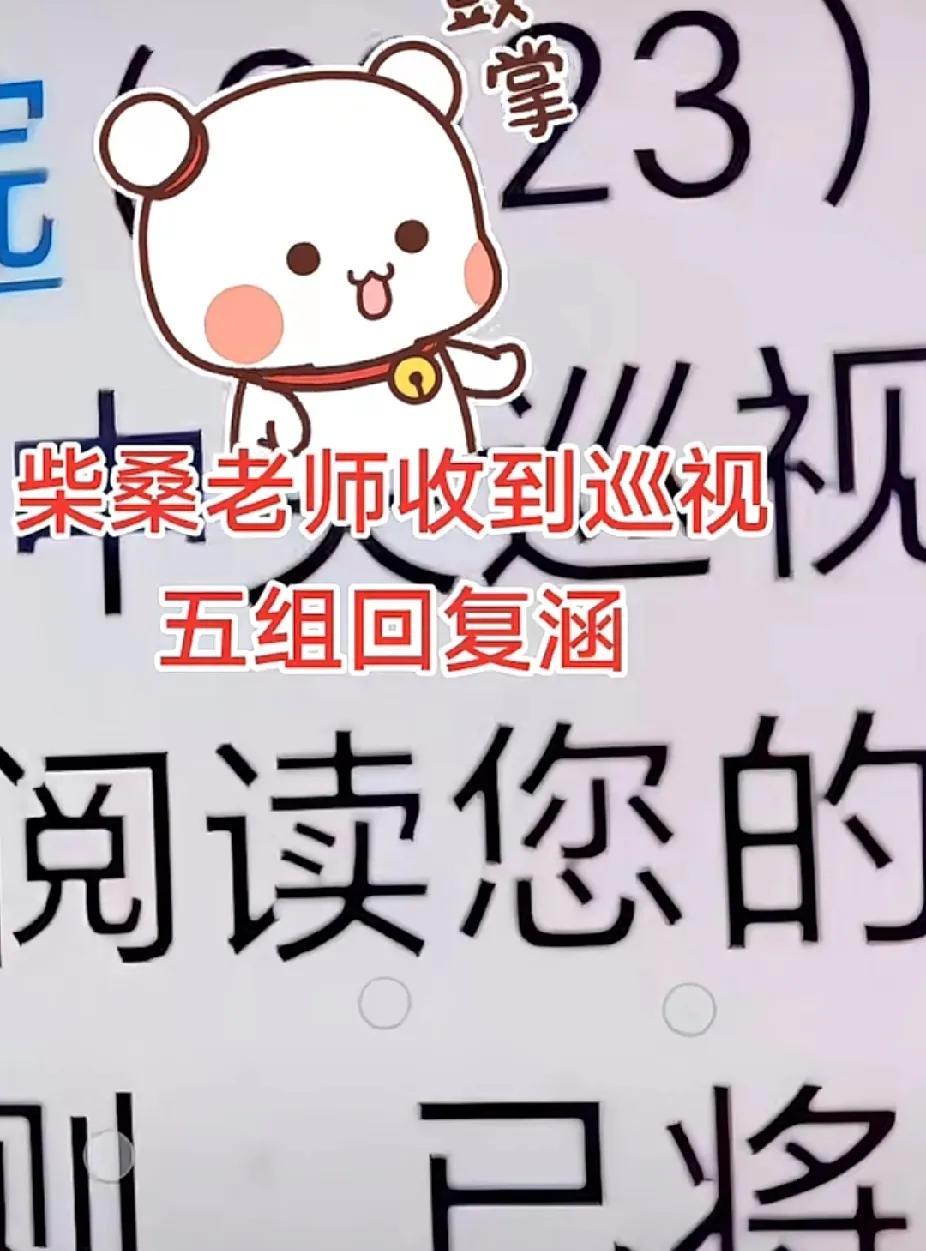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