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子玉
秦国在实力层面反超山东六国并通过蚕食、兼并战略拿到一统天下的结果有包括经济、地利、人口等多方面的优势,但王权独立绝对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只有王权独立才能调动一切资源服务于军事。而秦国能够维持王权独立的密码就是,重用山东士人。
因为,山东士人在秦国没有根基,只能完全依附于王权,完了秦王还不用担心对方坐大,威胁王权。
首先,商鞅变法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不是商鞅的过人才华,而是商鞅的非秦籍身份。想想,如果秦孝公重用具有和商鞅同样才华的秦国人来变法肯定拿不到之后那样的结果,因为,秦人首先要维护自身、家族的利益,必然没有推翻围墙的勇气和魄力,而且,有家族力量作为背书的秦人在拿到核心权力之后还会进一步威胁王权,只会让权力转移到贵族手中。
但是,重用山东士人就不一样了,由于其没有家族力量支撑就只能依附于王权,为秦王的大业冲锋陷阵,甚至将自身完全置于贵族的对立面。
看看商鞅,虽然孝公给了他极大的权力,但却根本不用担心商鞅会在秦国坐大。而且,商鞅为了持续得到孝公的信任必然会将自身才华淋漓尽致地发挥,甚至不惜彻底得罪贵族。
结果是,孝公既拿到了秦国变法成功的结果,让秦国崛起,还进一步强化了王权,一举两得。
等到惠文王即位之后,又以牺牲掉商鞅的方式平息了贵族的情绪,稳定了秦国秩序,然后以商鞅变法所转化的军事、经济优势开始尝试东出。
此后,重用山东士人打击贵族势力以维护王权的独立性就成为历代秦王的常规操作手法,典型就是秦昭王。
众所周知,秦昭王即位之后其权力就被以宣太后为代表的楚系外戚势力所垄断,形成了宣太后主内、其弟弟魏冉和华阳君主外的格局。尤其是魏冉,其在秦惠文王时期就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又凭借拥立昭王之功成为秦国庙堂的主宰。史书记载:“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得出的信息是:穰侯魏冉以宰相的身份负责政务;华阳君和昭王的两个同母弟弟高陵君和泾阳君负责军务。
昭王呢,倒成了垂拱而治的角色。
也就是说,在孝公、惠文王、武王之后,秦国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贵族群体——以宣太后为领头羊的楚系外戚势力。
当时,昭王的王权被极大稀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范雎与昭王的对话中得以印证。范雎在首次见昭王时就直指对方的痛点:“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
而事实是,昭王也承认了自己没有独立的决策权:“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
义渠之事清晰的还原了秦国不正常的权力结构。
为什么昭王当时要以宾主之礼来接待范雎,就是因为,范雎指出了他的权力痛点。当时,昭王对范雎的超规格接待让在场的人是大为侧目,史书对此的形容是——“群臣莫不洒然变色易容者”。
说通俗点就是,大家都受惊了。
这也是王稽在带范雎入秦的途中碰见魏冉,对方为什么会怀疑的原因,魏冉不想昭王引入山东士人来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更怕秦王引入商鞅、张仪式的精英造成对楚系的毁灭性打击。

魏冉当时控制着秦国庙堂 图源/剧照
当范雎被昭王重用之后,他自然明白自己的主要使命,那就是为昭王夺回王权,将昭王与楚系外戚的矛盾转移到自己身上。当然,这种事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首先就是将昭王包裹成被动者的角色。对此,范雎就将昭王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的事实讲了出来:
“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
呵呵,这些昭王当然清楚,也感同身受,只是要借范雎的口说出来。
当然,楚系外戚执政对秦国、秦王的危害也必须由范雎讲出来:“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于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无与昭奸。大者宗庙覆灭,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
范雎将楚系外戚执政对于秦国、秦王的危害讲得是明明白白。对于昭王的反应,史书的记载是“大惧”,曰“善”。
大家可以想一件事,以昭王之英明、之雄才,他难道想不到这些吗?不可能。只是在秦国庙堂的人事都被楚系所控制的情况下他没法直接与楚系短兵相接。如果事情做得急了,可能连王位都会失去。所以,解决楚系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将秦王与楚系的矛盾转移到第三者身上,让秦王成为被动者的角色。
范雎呢,为了在秦国立足,他只能冒着生命危险为秦王冲锋陷阵。
最终,昭王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将楚系外戚势力的核心从庙堂驱除,达到了收回王权的目的。
当然,范雎也拿到了相应的分红,被昭王拜为宰相。同时,昭王还封范雎为应侯。
当是时,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范雎帮助昭王收回了王权 图源/剧照
封侯拜相,范雎通过为昭王回收王权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人生巅峰。以范雎在魏国和秦国的人生际遇也可以看出秦魏之间的差距:
秦国不拘一格降人才,而魏国的权力却只能被贵族和宗室所垄断。人才战略不同,两国的强弱差距自然也会越来越大。
这一点,我们从王稽的行为中也能看出来。王稽以谒者的身份出使魏国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挖掘人才,他当时可是连郑安平这样的小角色都不放过:“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
郑安平救了范雎,是将范雎作为对未来的投资,于是就果断向王稽推荐了范雎,于是就有了范雎被王稽带入秦国的事。
至于范雎在魏国的悲惨遭遇这里就不再多说,熟悉历史的朋友都应该清楚。
这里,笔者不得不怀疑一件事,可能王稽的主动求贤都是昭王的刻意交代,让其在魏国寻找可以协助自己破局的精英。因为,事实已经证明魏国的土壤最容易产生商鞅式的大才。
只能说,范雎入秦和秦国的用人传统有关,也和秦昭王解决权力问题的需求有关。
当然,当范雎为昭王解决了权力问题之后,他依然是昭王控制秦国庙堂的一枚要棋,因为,作为外来人,范雎只能完全依附于王权,为昭王冲锋陷阵,解决棘手问题。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客观地讨论另外一个问题,范雎对秦国最大的贡献到底是不是远交近攻的战略。
对于远交近攻的战略,笔者个人的观点是,昭王其实也能想出来,只是在楚系执政的情况下他无法实行而已。就像汉武帝为了削藩所出台的“推恩令”,不是汉武帝想不出来,而是他为了避免和诸王的冲突借由主父偃的嘴将这个策略讲了出来而已。
推恩令是阳谋,其难点不在于提出的问题,而在于落地。因为,所谓的推恩令其实就是当年贾谊为汉文帝所建言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案。
同样,远交近攻的战略本质也是阳谋,其重点不在于提出的问题,而是如何落地。只有将楚系从决策层剔除,才能落地这个战略。
所以,范雎的主要使命还是为昭王解决权力问题。
只不过,范雎为了稳妥起见是先拿魏冉越过韩、魏而攻齐的行为说事而已。同时,这也是范雎测试昭王的真实心态而做出的试探,史书的原话是——“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
和当年的商鞅一样,范雎在决定正式冲锋之前也要对秦王的意志进行测试。
但是,和商鞅不同的是,范雎对秦国的贡献相对有限,其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对秦昭王个人,是始终为秦王解决权力问题的存在。
长平之战后,昭王为什么对白起趁势灭赵的军事行动紧急叫停,就是因为,昭王怕白起凭借灭国的军功在外独立。

昭王对白起并不放心 图源/剧照
对于这件事,大家都认为是范雎为了个人权势干扰了昭王的决策,实际上,对秦军灭赵行为叫停的真正决策人正是昭王,只不过,昭王要将自己和白起之间的矛盾转移到范雎身上而已。
范雎呢,正是在理解了昭王的心理之后才建议昭王召回白起的。你想,若是范雎真是干扰了秦国灭赵的大事,昭王岂不恨死了范雎,从昭王之后还继续重用范雎就能看出来,范雎这次也只不过是替秦王冲锋而已。
当然,白起心里自然也明白这一点,而他,也只能将情绪输出在范雎身上,史书记载:“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
呵呵,什么是帝王术,这就是。每次在读秦昭王的历史时笔者想的最多的一个人就是唐高宗李治,这两人在权术层面绝对属于同频者,都善于隐藏。
最终,白起因为态度问题还是被昭王赐死。只是,昭王也同时将舆论的压力转移到了范雎身上。
白起之死意味着秦昭王对楚系的洗牌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而纵观范雎的职业生涯,其最大的贡献也不过是为昭王解决了楚系问题而已。
但是,这也意味着范雎为自己培养了更多的敌人,为了避免商鞅的命运,他最终选择急流勇退,将蔡泽推了上去。范雎的精明由此可见。
总之,和商鞅一样,范雎对秦国最大的贡献就是维护了王权的独立性,保证秦国能够集中资源落地开拓战略。
历史,一定要刺穿表层看本质。
写文不易,看完记得点个“赞”。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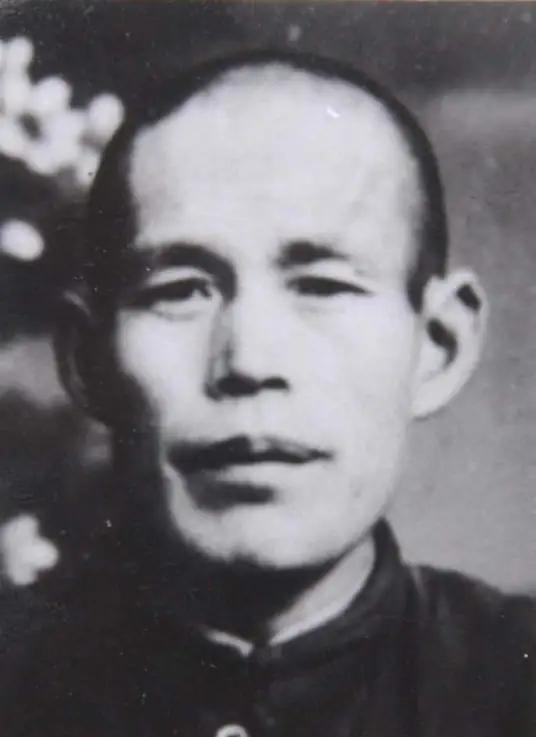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