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从总体熏陶和推动了基佐,为他的欧洲文明史观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但具体而言,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法国学者早期往往较多接触本国及英国思想、较少获得德国学识不大相同的地方是,基佐的文明史观受益于英法德三国著名史家思想的直接滋养。

将基佐引入欧洲文明史殿堂的是英国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1807年,年仅20岁的基佐认识了保林尼·德·默兰(后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她很快便发现了基佐的史学天份,积极鼓励基佐重译、注释和校正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基佐花了四年的时间,于1808-1812年完成了这一工作。期间,基佐的史学兴趣日趋强烈。
他说,“基督教巩固的历史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我阅读了教会诸神父的著作和德国作家记叙这个时期的那些伟大作品。从来没有任何学术研究这样紧紧地把我抓住。正是由于这些学术研究以及康德的哲学把我引向德国文献研究的。”

事实上,吉本的著作不仅将基佐引向了其他历史资料和历史著作,更重要的是,吉本的著作本身就是欧洲文明史中少有的精品。
虽然作者的主要历史题材是战争和政治,该书不仅以其史料丰富、视野广阔令人称道,而且作为“抓住历史连续性这个观点的第一位作者”,吉本在欧洲史上搭起了一座桥梁,将古代与近代的历史连接了起来。
基佐在其文明史著作中并没有直接提及吉本,但基佐的文明史的时间跨度及历史持续发展观,都与吉本的文明史观有相似之处。
可以认为,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已经在无形之中深深影响了基佐的史学兴趣及社会历史观。

事实上,在吉本的著作将基佐引向德国学界之前,基佐就已经显示出偏爱德国学术的倾向。早在日内瓦学习期间,他就接触并喜欢上的德国文学和哲学。
回到巴黎后,他对康德、赫尔德和席勒的兴趣远甚于对伏尔泰和康迪纳克的兴趣。
当时他还写过很多赞扬德国文学和哲学的文章,以致他的朋友指责他太德国化,而他自己后来也在回忆中说,自己年轻时很像德国人。
在吉本激发起他的历史连续性观念之后,基佐开始深入德国历史哲学领域,因而他的文明史观中很大一部分理论来源于德国学界。

康德哲学是基佐特别喜爱的,康德所研究的对象不是伦理学所研究的单独的个人,而是整个人类;他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突出地表现为个人乃至群体与整个人类之间的矛盾;他强调“如果历史从总体上考察人的意志自由的表现,那么,它就能够发现这种自由的一个合规律的进程。”
康德的目的论深深影响并体现在基佐的文明史中,以致圣伯夫批评说,“基佐的著作构成一条一环扣一环、一个环节也不能缺少的链子。他的目的,象支配和组织现在那样,支配和组织过去。我怀疑,一个人是否能够这样完整和确定地掌握他所叙述的历史的导因。”

康德的历史哲学在他的学生赫尔德那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基佐沿着这一路径研究了赫尔德及其思想。
他曾大力称赞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巨著《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一书。
赫尔德既具有开阔的历史和文化视野,又重视民族文化,注意挖掘各民族文化的价值,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历史主义。
他认为各民族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并没有高下之分,每一阶段都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经过程,它们具有各自的特色,在当时都是不可必缺的,具有类似的重要性;认为人类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同它们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相联系的,人类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民族精神;认为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反映了统一性,它们都统一于一个更高的有机整体。
赫尔德这种将历史视作文化史,重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规律性,强调存在即有其合理性的观点,是对康德思想的发展,它们在基佐的文明史中都有所体现,如基佐关于欧洲文明(包括法国文明)的发展历程的进步观念,就有追随赫尔德文化观的痕迹。

此外,萨维尼的《中世纪罗马法史》论证了罗马法尽管受到蛮族入侵的震动,但在西罗马帝国覆亡后,仍然残存下来的历史;强调罗马法律史的连续性,强调法律是一个民族整个生活的表现。
它不仅成为基佐文明史观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基佐文明史认识论的有力工具。

在《法国文明史》中,基佐也视法律为民族生活的表现,他多次提到萨维尼并引用其法学史研究成果阐述欧洲文明的历史进程;他赞扬萨维尼渊博而胜任的详述了各种事实,认为《中世纪罗马法史》是一部富有哲理的历史,又是一种关于历史事实的广泛的进步的编纂法的研究;但他也批评了萨维尼缺少联系的史学观念,认为萨维尼不但丝毫没有想把自己研究的特殊历史同人类文明和天性的一般历史加以比较,而且甚至在自己的课题范围内,也没有费心去把各种事实作任何系统的联系。
因而导致它们完全孤立,除了日期的关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关系。在基佐看来,这样一种关系并不是真正的关系,它既不赋予事实以意义,也不赋予事实以价值。
尽管基佐一度非常偏爱德国著作,德国学者对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身为法国人的他也仍然可以算是法国史学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孔多塞、圣西门等人史学思想的继承者。

基佐对某些理性主义思想是持批判态度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向启蒙思想家学习。
启蒙思想家们的规律观念、进步观念、自由观念也对他有较大影响。
他是巴黎“18世纪哲学爱好者”沙龙的常客和由孟德斯鸠信徒组成的“空论家派”的主要领导成员,便可作为佐证。
在笔者看来,孟德斯鸠把政治现象放置在历史的一般规律下加以说明,他的历史规律性观念和政治制度观念影响了基佐。

基佐的文明史中也特别重视在历史语境下分析各种制度的结构及其命运。伏尔泰以历史视野影响了基佐。
伏尔泰的历史视野比孟德斯鸠开阔,孟德斯鸠主要关注政治制度,伏尔泰重视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各国的风俗习惯。
在他的名著《路易十四时代》开篇之处,他就明志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
基佐也特别重视人类精神的进步,强调人的发展。

孔多塞给了基佐文明进步的强大信念,他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了分析,提出人类历史发展要经历的十个阶段,认为后一阶段总比前一阶段进步;历史的进步是和人类理性在每一个时代的发展状况相制约的;历史并不是英雄人物所创造的英雄业绩,而是人类理性觉醒的产物;历史进步的阶段,基本上就是相应于人类理性发展的阶段。
可以说,基佐的人性发展观有些许孔多塞的影子。

此外,同时代的长辈圣西门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对基佐也有影响。
圣西门坚信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规律性;财产问题是社会矛盾的根源,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旧制度不断衰落,必须由新的制度取而代之。
他还指出,“中世纪形成的神学和封建体系,比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政治和宗教体系更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人类的文明。它最终在十五世纪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使现代的各族人民比古代的各族人民高出许多。”

基佐欧洲文明史观中所蕴含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辩证法思想,在克罗齐看来,具有时代的共性:“19世纪前半世纪的史学符合唯心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哲学,19世纪后半世纪的史学符合自然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因此,就历史学家而论是无法区别其历史思想和哲学思想的,二者在叙述中是浑然一体的。”
确实,基佐十分强调哲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历史学家兼有哲学家和画家的职责,“失去画家的职责,历史仍是有用的;但如果失去哲学家的职责,历史将浮于表面甚至是有害的。”
所以我们可以同意汤普森的说法,即“基佐本质上是史学思想家而不是历史著作家。”

正是这种史学思想家的倾向,使基佐的文明史观与伏尔泰的文明史观有明显的不同。
众所周知,在近代史家中,伏尔泰以其《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被尊称为“西方文明史之父”,他与基佐一样,关注人类文明的发展,拥有整体史观念、进步史观念和文明史观念,后世学者们也往往据此将基佐的欧洲文明史观视作伏尔泰世界文明史观的发展形态。
但事实上基佐史学中的哲学气质不同于伏尔泰,他对伏尔泰文明史采取的是批判式继承方法,直接从伏尔泰文明史观中继承的东西不多,相反,两者之间有较大差别。

其一,对文明蕴意的认识不同。
基佐较多从制度和法律层面认识文明,较少述及风俗等精神层面的文化现象。
伏尔泰则将着力点置于风俗、技艺等精神文化层面。
基佐明确将文明史研究限定在欧洲社会(其实主要是西欧社会)上,他认为东方文明缺乏持续进步的动力,否认东方文明的发展进步性的事实,带有较浓厚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而伏尔泰的文明史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将整个世界置于进步观念中,尽管他的世界史观背后隐藏着欧洲主义的实质,但他的世界整体观念还是超越于基佐欧洲整体史观的。

其二,对文明发展状态的认识不同。
基佐从长时段角度,强调人类的发展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渐进式累积,认为包含中世纪在内的每一阶段发展进程中,人类理性都将随文明的进步而提升;文明进步源于社会与智力的和谐发展。
伏尔泰则相信,人类理性是先验的、不变的;人类的发展受偶然性影响;中世纪是粗野的、荒谬的、黑暗的,只有古典文明和近代文明值得关注;文明进步的希望只能寄于开明君主身上。

其三,对事件因果关系的认识不同。
基佐不仅关注事件的因果关系,而且特别强调具体事件与文明的关系。
他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文明发展的主题展开,支蔓多被略去,用他自己的话说,“各种重大事件、社会危机和社会所经历的各种情况,使我们感到兴趣的仅仅在于它们与文明的发展的种种关系。
我们询问它们的仅仅是,在哪一些方面它们反对它或促进了它,它们给了它什么,它们拒绝给它什么?”而伏尔泰只关注事件的因果关系和人类的直接动机,他对历史的阐释仅限于发现特殊原因,而不思考基佐所研究的那些更广泛意义上的一般原因的作用。

基佐文明进步史观为何与伏尔泰文明进步史观有如此大的区别呢?除前述基佐学术中的德国倾向外,基佐与伏尔泰所处时代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说,进步运动在18世纪时还没有完全显示其魅力,而到19世纪则已成为一种显著的事实;18世纪是理性主义的世纪,而19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则在基佐身上体现为浪漫主义的“怀乡性”和对理性主义的强烈批判意识。
因而,在基佐的文明史中,他“精力充沛地反对启蒙时代哲学家,尤其是康迪拉克、伏尔泰和苏格兰派哲学家等的理性主义教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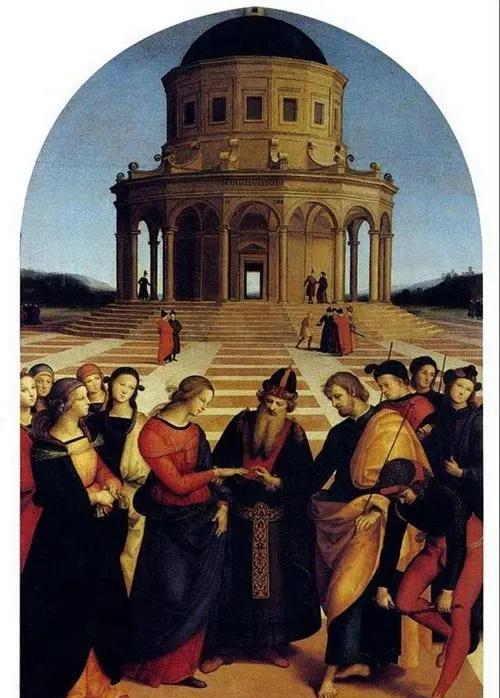
总之,基佐的欧洲文明进步史观是西方史学思想中的瑰宝。
他将“欧洲”与“文明”有机结合,以长时段、以整个时代为单位写作欧洲文明史,展示自身文明进步史观的做法,对后代史家,尤其是对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有较大影响,如从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一书中不难发现基佐文明史观的影子。
同时,基佐对近代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和中国学者梁启超等也有所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文明史的发展。
当然,不可否认,基佐的欧洲文明史观也存在许多不足,如他虽然强调了文明发展的规律性和持续性,却又“保留了超自然的信仰,尊重宗教,痴迷于伦理学”。
但总体而言,基佐的文明史观,既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关照之情,也对史学理论的发展有所裨益,其史学意义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