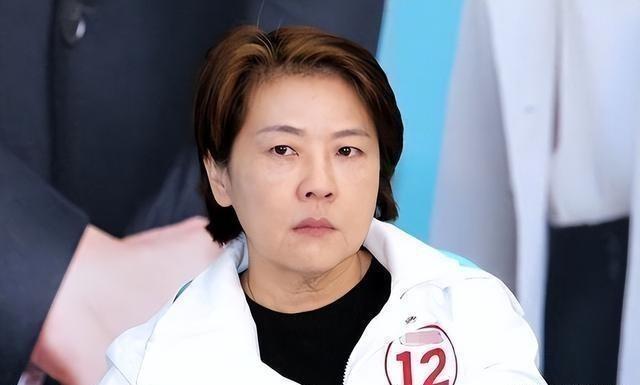李在明确实聪明,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尹锡悦,先把检察厅废除了。然后,新设立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分离了检察机关的起诉和调查功能。 自1948年设立以来,这个机构逐渐演变成集侦查、起诉、指挥警察于一体的“超级权力体”。它不仅能直接调查从贪腐到叛国的所有案件,还能决定是否对嫌疑人提起公诉,甚至能指挥警察配合办案。 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权力结构,让检察厅成为韩国政坛的“总统克星”——李明博因受贿被判17年,朴槿惠因亲信干政获刑22年,尹锡悦夫妇更是在任期内被检察厅调查并相继入狱。 李在明对这种权力架构的警惕,源于他自身的“检察恐惧症”。2025年初,还是总统候选人的他身陷5起刑事案件,检方甚至在庭审中要求判处两年监禁。 但当他6月正式入主青瓦台后,这些案件突然全部延期审理。这种戏剧性反转,暴露出韩国司法体系“看人下菜碟”的致命缺陷——当检察权成为政治工具,任何总统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更深层的改革动力,来自文在寅与尹锡悦的前车之鉴。2017年,文在寅曾试图通过缩小检察侦查范围、设立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来制衡检察权,但2023年尹锡悦凭借检察总长身份当选总统后,立即用“检侦恢复”总统令推翻改革,将检方直接侦查范围扩大到反恐、选举等敏感领域。 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轮回,让李在明意识到:不彻底拆解检察厅的权力架构,任何改革都只是政治秀。 2025年7月1日,李在明政府发起第一波攻势——将尹锡悦任命的检察高层全部换血。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李昌洙等9名检察官或主动辞职或被调离,这些曾对金建希涉嫌操纵股价案作出无嫌疑处理的检察官集体退场,为改革扫清人事障碍。 紧接着,7月3日李在明在就任“满月”记者会上抛出核心主张:“同一主体不能同时掌握侦查权和起诉权。”这为后续改革定下基调。 真正的较量在9月7日达到高潮。执政党、政府、总统办公室联合发布的组织架构调整方案显示:新设的公诉厅将专注起诉环节,重大犯罪调查厅则负责侦查,两者分别隶属于法务部和行政安全部。 这种设计相当于把原本集中于检察厅的权力,切割成三块——公诉厅管起诉,调查厅管侦查,行政安全部通过人事权形成间接制衡。更微妙的是,改革方案特意避开“废除检察厅”的表述,而是通过修改《政府组织法》实现机构更名,试图规避“违宪”争议。 但争议随之而来。反对者指出,将侦查权划归行政安全部下属机构,可能使调查沦为政治工具;支持者则认为,分离起诉与侦查能防止“未审先判”的司法乱象。 典型案例是2025年4月的文在寅案——检方以“易斯达航空案”为由起诉文在寅,被进步阵营指责为尹锡悦的“司法报复”;而金建希案中,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先作无嫌疑处理,后被特检法推翻,更暴露出检察权滥用风险。 这场改革能否破解“检察魔咒”?从制度设计看,公诉厅与调查厅的相互制衡,确实能减少单一机构权力过大的风险。但新问题也随之浮现:行政安全部长掌握侦查机关人事权,是否会催生新的权力寻租? 检方失去补充侦查权后,如何防止警方权力滥用?更关键的是,当改革方案需经国会审议、设置一年过渡期时,保守派势力是否会利用这段时间反扑? 李在明的改革实验,本质上是韩国司法体系从“人治”向“法治”的艰难转身。当公诉厅检察官开始专注起诉材料整理,当调查厅探员奔波于犯罪现场,这个国家或许能摆脱“总统入狱循环”。 但制度变革从来不是单线程进程——如何平衡司法独立与行政监督,如何防止权力切割后的部门掣肘,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李在明是成为韩国司法现代化的奠基人,还是另一个被权力反噬的政治标本。 这场改革会走向何方?是真正实现司法公正,还是沦为新的权力游戏?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