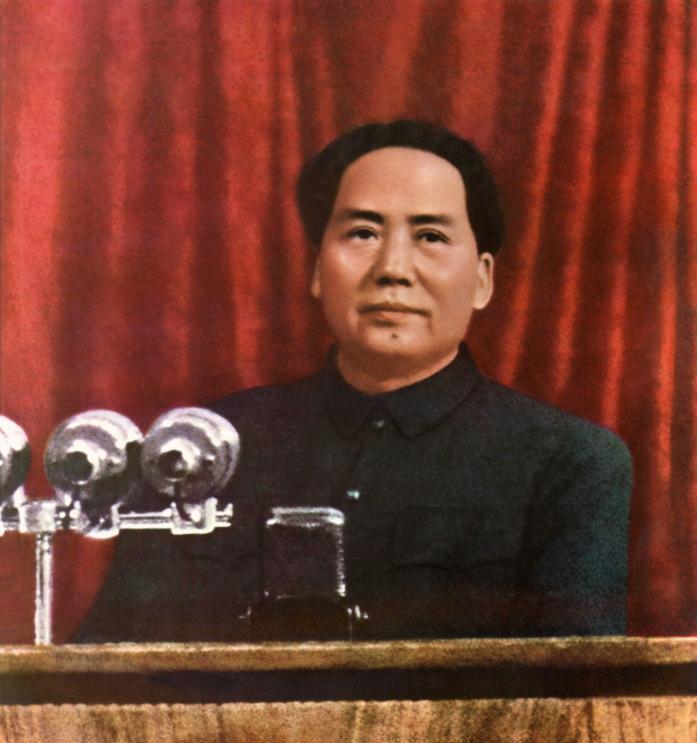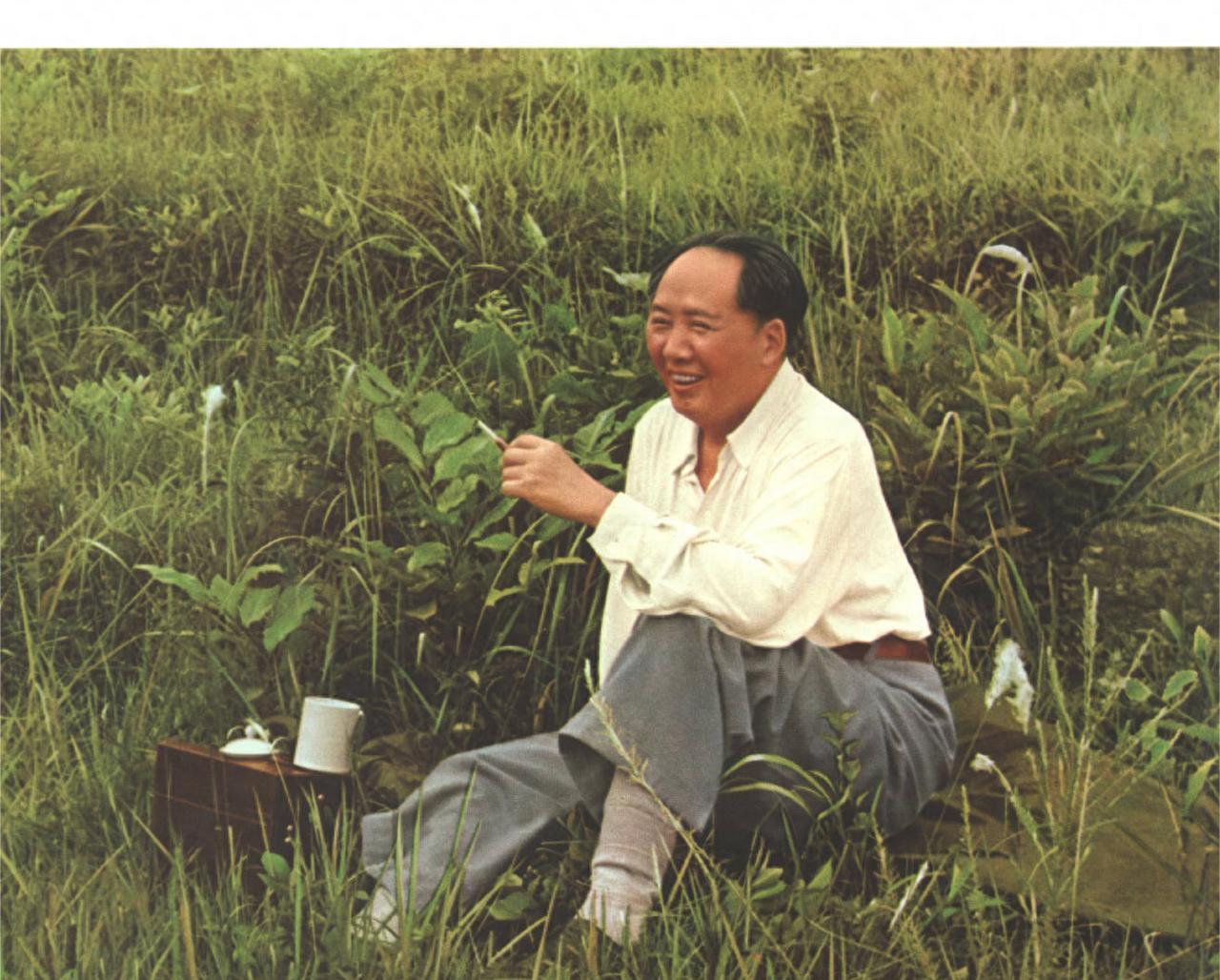拨乱反正后,各种针对毛主席的言论甚嚣尘上,陈云说:“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个思想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进行思想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 陈云多次提到毛主席提倡学习哲学,并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面来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全党工作的指导作用。他曾深情地回忆说,我到延安后,毛主席让我学哲学。我系统地学了几年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使我受益匪浅,"在延安学习前,我的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习后,讲话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陈云把自己学习哲学的心得概括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陈云在他所负责的经济建设等各项领导工作中,都是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及时总结经验,提出切实、正确、有效的方针政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 毛主席是集传统文化与现代哲学的大成者。大约在1909年之前,他接受的教育几乎全是传统的。1902年,大约九岁的毛主席在家乡韶山冲的南岸私塾发蒙。私塾先生教的是老一套:摇头晃脑死记硬背。从《三字经》《百家姓》这样的启蒙读物开始,接着是《幼学琼林》,再往后就是儒家经典“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轮番上阵。先生只管教读、背诵和理解是次要的。好在毛主席天资聪颖,记忆力超群,那些拗口的句子、深奥的道理,硬是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脑海里。即使后来离开私塾,进了些标榜“新式”的学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主席钻研的重点还是“国学”。 特别是1913年到1918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五年,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老师杨昌济。杨先生推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思想,他本人的人格魅力也极具感染力。在杨老师的悉心指点和自己废寝忘食的钻研下,毛主席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不再是浅尝辄止,而是更深入、更系统。那时,毛主席心中向往的,正是儒家那套“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他坚信,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光有本事还不行,关键得先向内用力,刻苦修养自身的人格,只有当内在的境界达到了某种理想的高度,外在的事业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宏大的气象。 浸润毛主席心灵的,不止是正统的儒家经典,还有带有强烈湖湘地域特色的“湘学”。特别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王船山)和晚清的曾国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主席和同学们经常跑到长沙的“船山学社”去听讲演,甚至专门跑到王夫之的家乡衡阳曲兰去探访遗迹。 王夫之的思想深深吸引了青年毛主席。毛主席在自己的《讲堂录》里特意抄录了王夫之的一句话:‘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这句话点明了圣贤境界高于单纯的豪杰气概,也暗示了成就圣贤需要豪杰般的意志和实践能力。 另一个对他影响巨大的人物是曾国藩。在晚清那个动荡的年代,曾国藩被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奉为楷模,评价他达到了儒家推崇的‘立德’(树立崇高的道德)、‘立功’(建立显赫的功业)、‘立言’(留下有价值的言论)‘三不朽’的完美境界,享有“中兴名臣”、“一代儒宗”的美誉。毛主席对这位湖南前辈非常敬佩,在1917年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直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在《讲堂录》里,他也摘抄了不少曾国藩的语录,比如关于改变社会风气,强调要‘厚’(宽厚不忌妒他人)和‘实’(踏实不说大话空话,不好虚名,不搞花架子,不谈过高玄远脱离实际的道理)。可以说,是湘学这股刚健务实、重视实践和担当精神的传统,加上湖南近代以来涌现的诸多英雄豪杰事迹,深深地感染了青少年时代的毛主席,催生了他对那种融合了内在道德光辉与外在事功建树的圣贤型理想人格的真诚向往与追求。 就在毛主席沉浸在儒家经典的世界里时,外部世界的风浪已经拍打到韶山冲的边缘。1909年春夏,辍学在家的毛主席第一次间接地触碰到了西方文化,读到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对于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身处偏远山村的少年来说,这两本书无异于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窗户。书中提到的“君主立宪”的政治蓝图,发展工商业、富国强兵的经济主张,都是他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书中流露出的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满腔热忱,更是让年轻的毛主席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可以说,正是这些书中描绘的图景和忧患意识,成为促使他不久后毅然走出封闭的韶山,外出求学寻找救国之路的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