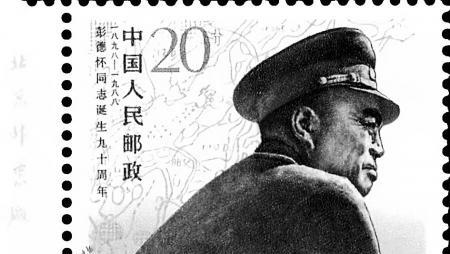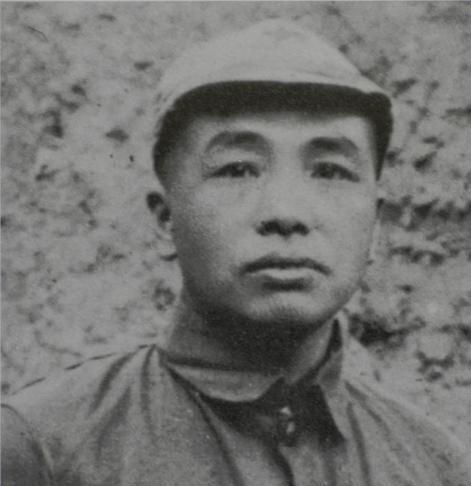彭老总一直把毛主席看作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战争年代,他与毛主席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有争论,和平时期亦是如此。但这些分歧并不表明彭德怀就反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用他的话说就是:"毛主席百分之九十九的正确,难道就连百分之一的错误都没有?"庐山会议上,他以极大的勇气,对"大跃进"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历史证明:彭德怀当时的意见有不少是正确的。 回想1916年3月中旬,彭德怀正式加入了湘军第2师第3旅第6团第1营第1连,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士兵。此时的湘军,规模并不大,只有两个师。第1师师长是赵恒惕,第2师师长为陈复初,旅长是陈嘉佑,团长是鲁涤平,营长是刘铆,连长则是胡子茂。 这一年,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是一个激烈动荡、风云变幻的年代。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狼子野心,公然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政权。1916年元旦,袁世凯更是胆大包天,公然复辟帝制,改元洪宪,妄图再次登上皇帝的宝座,然而他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便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灰溜溜地下了台。以云南为首的南方几省,奋起反抗,发动了护国战争,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恶行径。 彭德怀入伍不到3年,在全国就爆发了两次南北战争,局势愈发紧张。 1917年秋,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依仗着手中的武力,野心勃勃地当上了北京政府国务总理。他控制中央实权后,为了实现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便出兵攻占湖南,企图以此为跳板,“兵下两广,饮马珠江”。他接过谭延闿提出的“湘人治湘”的口号,改派陆军次长、湖南乾城人傅良佐接替谭延闿的湖南督军职务,这一举措遭到了湖南军阀的强烈反对。1918年初,傅良佐派北洋军第8师师长、第20师师长为湖南军正、副总司令,向退守衡阳、宝庆一线的湘军发起猛烈进攻。 彭德怀所在的第6团,在与傅良佐部的一次战斗中,形势极为危急。袁植率部在衡阳渡湘江,彭德怀奉命为后卫。部队已退到江右岸,可袁植还在左岸。这时,一股敌人迂回到袁植的侧后,距离袁植只有1000米左右,情况万分危急。彭德怀眼疾手快,发现敌人后,立刻对袁植说:“赶快沿江走,我在这里掩护你!”袁植在彭德怀的掩护下,成功脱险。而彭德怀直到确认袁植安全后,才下令撤退,敌人也未猛追。两人会合时,袁植心有余悸地说:“好危险,没有注意到侧后,几乎做了俘虏。”这次战斗,让彭德怀在部队中声名大噪。 军阀纷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湘军内部完全是封建军阀统治,走私贩毒,克扣士兵饷银,为了争地盘,抢财源,经常发生内讧,“今日归汉,明日归曹”,局势混乱不堪。至于吃喝嫖赌,一个军官有数个姨太太更是普遍现象。而士兵们除了服从之外,没有别的自由。任何违反军官命令的行为都是非法的,轻者要受笞责、禁闭,重者要军法从事,判刑、杀头。这一切,让彭德怀感到忿懑、失望,他对旧军队的幻想逐渐破灭,心中开始思考新的出路。 在此期间,彭德怀结识了营部文书、团训练队语文教员黄公略。黄公略是湖南湘乡县人,身体单薄,眼睛很大,眉毛淡淡的,与彭德怀是同庚人,也是同年投奔湘军的。他原名汉魂,字家祀,爱读兵书,特别喜爱受书张良于圮上的黄石公,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黄公略,又叫黄石。彭德怀对他的好学和书法、绘画才能很钦佩,曾写道:“公略是一位求知欲很高的人。”连年的战争,让农村的一些小知识分子也不得安生,既读不起书,也安不下心教学。 鲁涤平的参谋肖文铎把他的内弟李文彬从宜章县的乡下介绍到湘军来,安排在彭德怀的班里。班长彭德怀见他好学上进,为人谦和,和他相处得很好。李文彬高小毕业,他教彭德怀学习文化,班里的士兵常见他俩在晚饭后,坐在床铺前写字作文,气氛十分融洽。彭德怀把他介绍给黄公略。他们三人都热血方刚,满怀爱国热忱,志趣相投,互相砥砺,成为好友。李文彬写信告诉家里人说:“我要追求光明,扫除邪恶,已将文彬之名改为灿。”从此,他改名李灿。 彭德怀还结交了20多个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失业小手工业者出身的士兵做朋友,同黄公略、李灿一起,大家相约以救国救民为宗旨,“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讨小老婆);不扰民。”在旧军队中,由于他们恪守不移,洁身自好,始终未随浊流而沉沦,成为了黑暗中的一股清流。 彭德华带着痛恨社会的不平和挣脱苦难的愿望从军后,几年的军阀混战使他的幻想破灭,但他并未灰心,继续寻求出路。可是真正的出路在哪里?他还不清楚。他看到的只是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为军阀卖命的士兵多是同他一样苦的弟兄。他立志救贫扶难,心中燃烧着一团炽热的火焰。1920年夏,他与李灿、王绍南、张荣生、席洪全、祝昌松、魏本荣等6人秘密组织了扶困济贫性质的团体“救贫会”,在他任排长的排里开展了秘密活动。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士兵和百姓,虽然力量微薄,但却如同一颗星星之火,在黑暗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