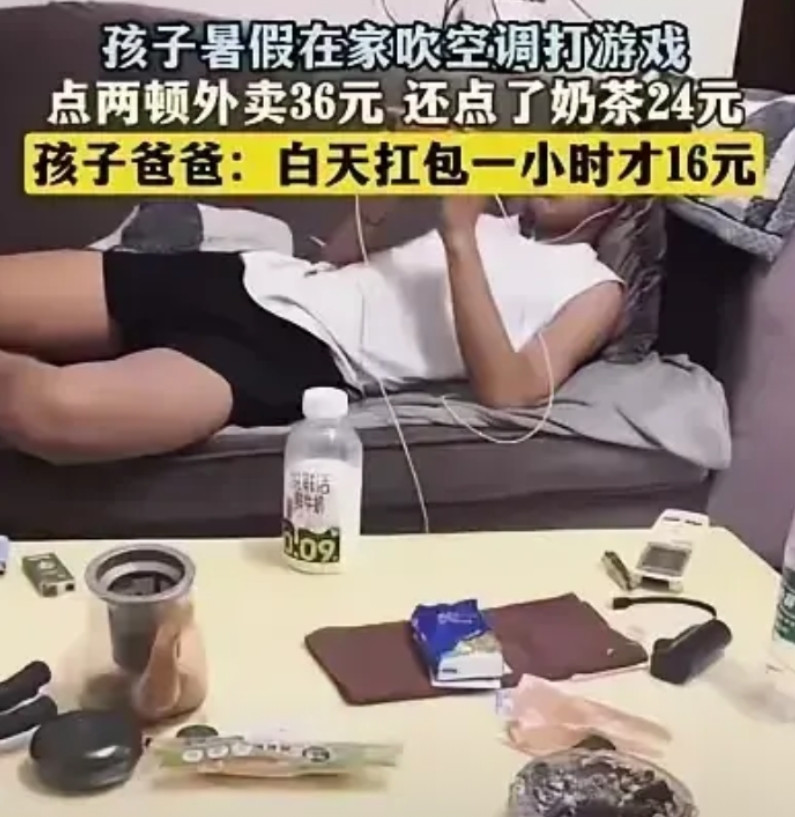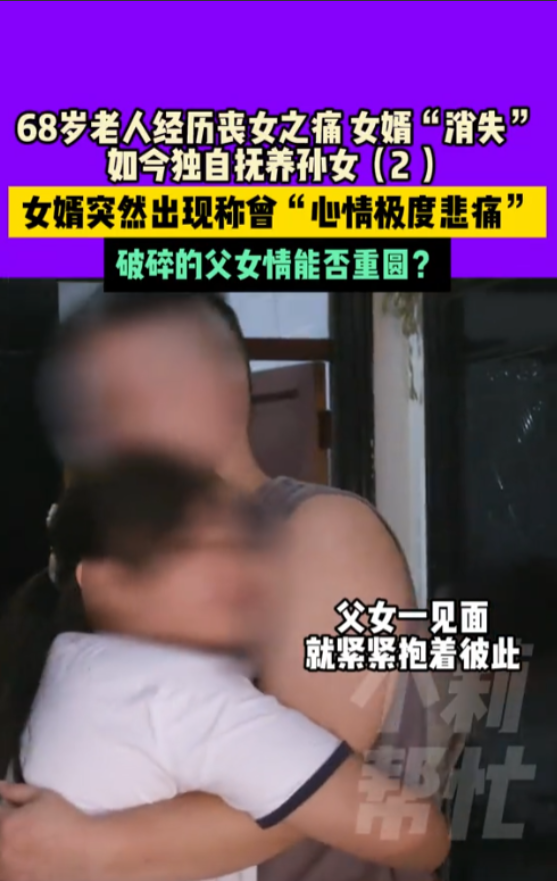1998年,大学教授何家庆来到深山调研。在调研期间不一定能吃上饭,由于太过饥饿,不得已向村民讨要饭菜。不料,村民居然端来一碗猪食,万万没想到,何家庆不仅接受了,他还泪流满面的吃了起来。
很难想象,这个瘦到脱形、衣衫褴褛的人,是安徽大学的植物学教授何家庆。他肩上那个洗到发白的帆布包里,除了几页笔记,就剩一张折角的地图。村民们看他的眼神,从好奇到敬佩,最后都管他叫“何老师”。
1949年的安庆码头,何家庆的母亲早逝,全家就靠老爹拉板车过活。父亲的腰被压弯了,可一个念头没弯:“娃啊,有书念才有出路!”就这样,他硬是把儿子送进了学堂。
何家庆也懂事,上学靠助学金,放学就帮爹拉车、捡破烂。后来考上安徽大学,学费又成了天大的难题。还是老师同学你五毛我一块,给他凑齐了钱。父亲攥着他的手说:“要记得帮过咱的人。”这句话,从此就刻在了他心里。
大学毕业后,何家庆留校搞植物学研究。可他总觉得,这些花花草草不能只待在标本馆里,得能让山里人吃上饭才行。一查资料,他心里“咯噔”一下:偌大的大别山,植物资源竟然没有一次完整的普查。
可如果想要去调查,得要钱,但是钱从哪来,八十年代,大学老师一个月工资几十块,进山一趟却要上万。他跟自己较上了劲,结婚没添一件新衣,靠着咸菜馒头硬是攒了六七年,攒下三千多。
临行前,老父亲颤巍巍地捧出一个木盒子,里面是四千多块钱的一毛两毛,还有一张烟盒纸,写着:“共产党供你读书,要对得起人民。”
1984年春天,何家庆背着帆布包进了山,翻了三百多座山,不知蹚过多少河。他被蚂蟥咬得满腿是血,也曾摔下山崖被猎人救起,暴雨天只能和牛挤一个棚,有一次,他看老乡把桂花苗种在背阴坡,又对着满山的猪草发愁没饲料,才猛然惊醒:山里人不是懒,是没人给他们指条路。
而他的考察报告,很快就获得了国家领导的批示。也正是在大别山,他认准了一种作物魔芋。这东西耐阴耐瘠,产量高,能吃能入药,简直是给贫困户量身定做的,光有成果不行,得有人手把手地教。1990年,他被派到绩溪当科技副县长,这下轮到当地人看傻眼了。
一个县长,蹬辆破自行车到处钻山沟,衣服上补丁摞着补丁。他办“野草展览会”,让乡亲们第一次知道脚下的杂草也能换钱;看蚕农亏本,他卷起裤腿蹲进蚕房教技术;洪水来了,他蹚着齐腰深的水帮人抢救桑苗,还把自己的出差费都垫了进去。
他自费引种的魔芋大获丰收,几百户人家因此挣到了实实在在的票子。他离任那天,乡亲们把路都堵了,送他一面“焦裕禄式县长”的锦旗。
他早就听说西部山区比大别山更穷。1998年春天,50岁的何家庆给家里留了封信,揣着全家两万七的积蓄就“失踪”了。他要一个人,徒步考察八个省的贫困山区。
三百多天里,他在西南的深山里翻山越岭,走坏了十几双胶鞋,满脚是血泡叠着血泡。饿急了,他真就蹲在猪圈旁吃过馊掉的糊糊;被矿老板抓去当苦力砸石头,好不容易逃出来又遇上山洪。
路上被抢了两次,丢了四千多块钱,他只是把裤腰带捆得更紧,继续往前走。起初,山民当他是骗子,他就蹲在土坡上教孩子们认字。慢慢地,大家信了。看他累倒在草垛上,有人会咬牙杀了家里下蛋的母鸡给他熬汤;看他腿肿得走不动,几个后生会轮流背他过山梁。
这个大学教授一路讨饭回到家,一百多斤的人,瘦得只剩八十斤挂零,更糟的是,医院查出他得了癌症。他却很平静,让家人录下视频:“眼角膜没病变,给山里娃留着。”医生红着眼圈说,教授全身也就这器官还能用了。
六十多岁,他又盯上了栝楼。这种藤蔓,在中药和食品市场都是宝贝。他再次一头扎进江淮丘陵,建示范田,写专著,自费申报专利。他说自己不图名利,就图“农民能把荷包鼓起来”。
2019年秋天,何家庆走了。可他种下的东西,却留了下来。大别山的药材、绩溪的魔芋、西南山沟里新起的小楼、江淮丘陵的栝楼产业,都成了他活过的证明。
在他去世后,贵州、云南、四川的山村里,许多人家会在祠堂为他点上蜡烛,贴一张白纸,上面就写着“何老师”三个字。有老人回想起当年那碗猪食,眼含热泪地说:“咱给得起的,只有这点,还好他肯吃。”
何家庆手写的教材,至今还贴在村委会的墙上,油迹斑斑,没人舍得撕。他教的是如何在石头缝里蹚出一条路,如何把知识变成饭碗,变成孩子们的学费,变成山里人日子里的底气。
何家庆教授的一生做到了他年少时立下的誓言,“位卑未敢忘国忧”是何教授经常放在嘴边的话,对此我们只能用一个过去我们很熟悉现在已经很少提及的词,那就是“革命的傻子”,千言万语,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铭记,现在有很多“何家庆”在为我们的美好生活而努力。
信源:央广网——一本日记 走近“布衣教授”何家庆;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儿女英雄传丨脚下有泥何教授 心中无我大先生




![我说女儿不努力有什么错?[惊恐]](http://image.uczzd.cn/14631652214321372655.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