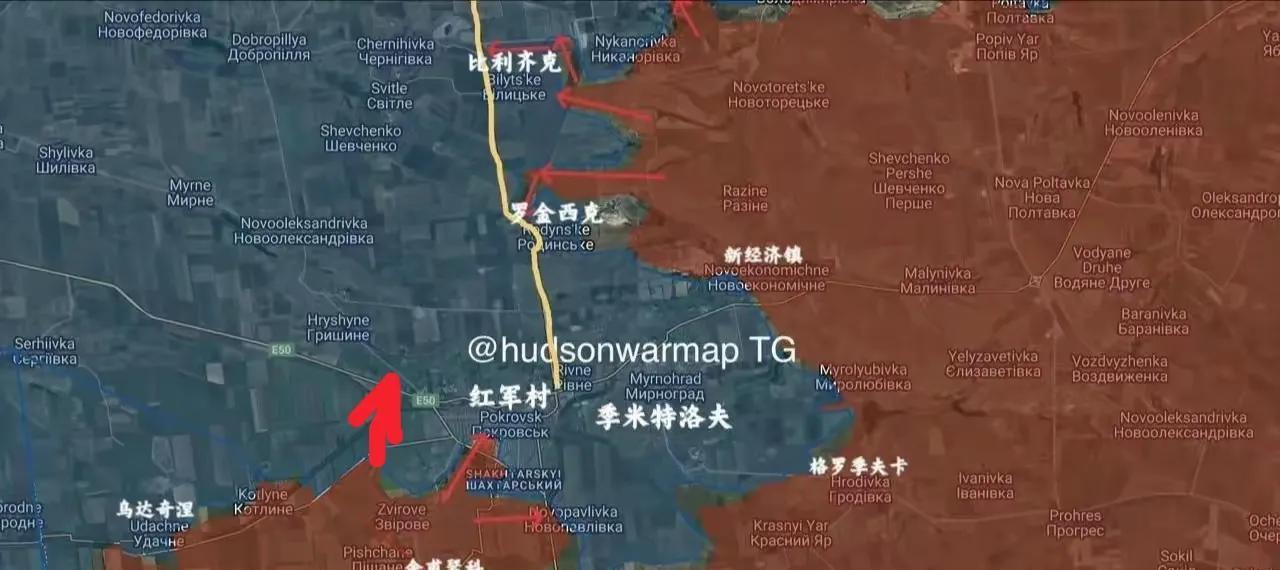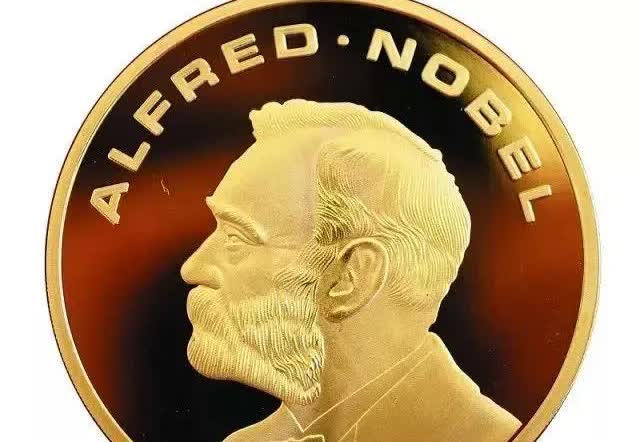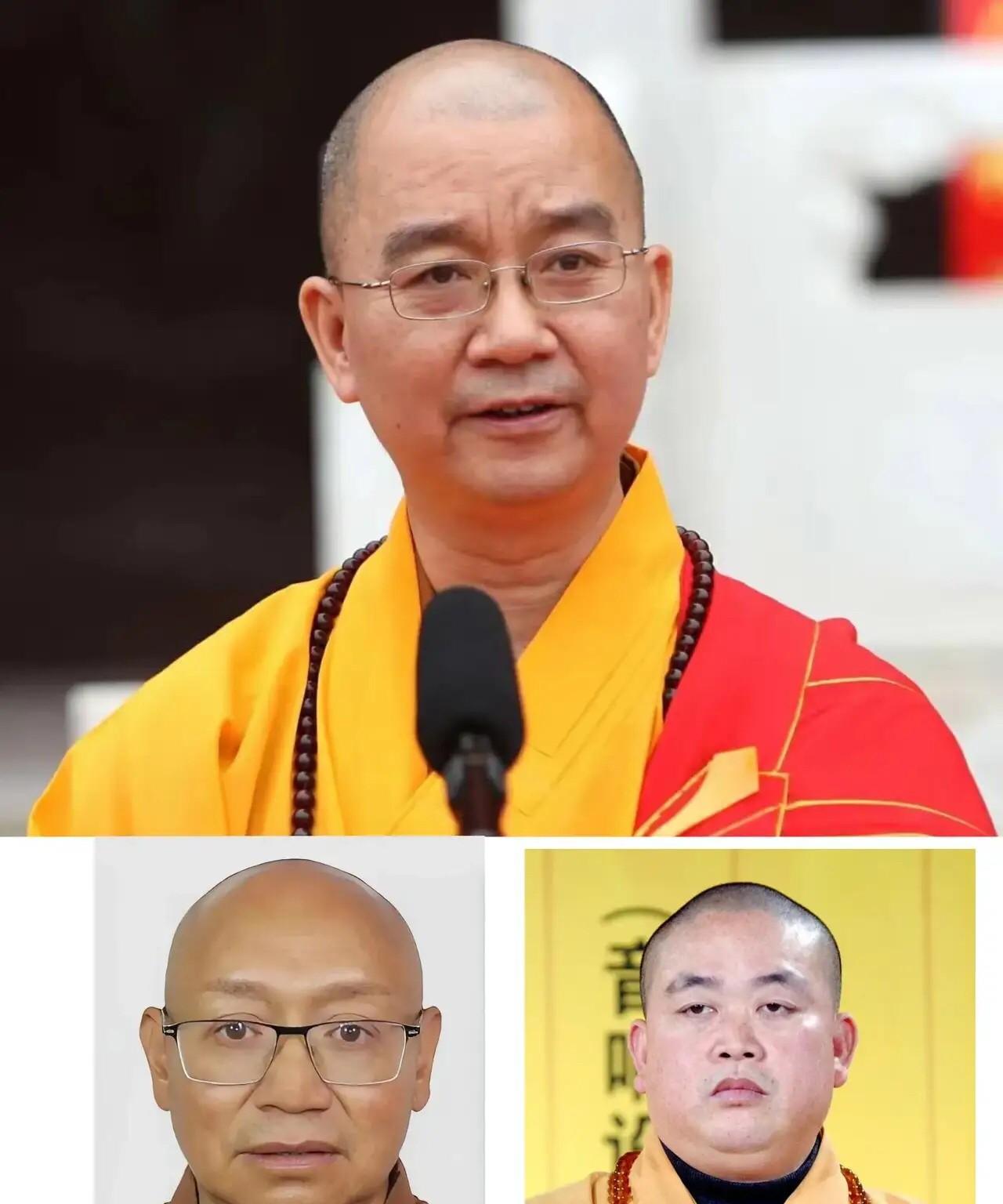一次,张恪智到马未都家吃饭,酒意正浓时,便开始借钱。马未都老婆便说:“你之前向我们借了6000,都过去5年了,你准备啥时候还?” 马未都,1955年出生在北京,祖籍山东荣成,算得上文化圈里响当当的人物。小时候家里条件一般,他小学没念完就辍学,后来下乡插队,干过农活,1970年代回城后在工厂当铣工,天天跟机床打交道,铁屑飞得到处都是。他闲下来就爱读书,啃过《红楼梦》《简·爱》,还从叶圣陶家借过《高老头》。1981年,他写的小说《今夜月儿圆》登上《中国青年报》,一整版刊出,读者反响热烈,编辑部直接把他调到《青年文学》当编辑。办公室里书稿堆得老高,他跟同事聊文学,改稿子,日子过得充实。1980年代末,他跟王朔、刘震云几个朋友搞了个“海马影视创作室”,写出《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这样的热门电视剧,名气更大了。他对古董着迷,经常逛琉璃厂、潘家园,淘瓷器、家具,眼睛一亮就停不下来。1993年,他出书《马说陶瓷》,讲收藏讲得深入浅出,读者当宝贝一样捧着。1996年,他一咬牙,辞了出版社的铁饭碗,拿出积蓄办观复博物馆,成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的馆长。后来他上《百家讲坛》,讲收藏讲得风生水起,2008年还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五名,版税745万,收藏界也给了他“十大人物”称号。 张恪智是个书法家,具体生平没多少记载,只知道1980年代跟马未都混得挺熟。他靠写字谋生,字写得遒劲有力,路边摆摊时用树枝蘸墨在地上写,围观的人都夸好。马未都一眼相中他的才华,觉得这人不该埋没,就拉他到编辑部干活。张恪智去了以后,果然凭一手好字让同事刮目相看,大家没事就找他写对联、题字,他也乐在其中。跟马未都关系好得跟兄弟似的,经常往马未都家跑,聊书法、聊文学,气氛热乎。可他日子过得紧巴,欠了不少外债,脸上总挂着愁容。马未都知道他难处,帮他不少忙,但也慢慢发现他有些毛病,比如烟瘾大,抽起来没完没了,还不爱收拾,烟灰弹得满地都是。这点让马未都妻子贾宏伟挺烦,可碍于面子没说啥。张恪智的才华没得说,但生活习惯和经济状况让他跟马未都的友情埋下了隐患。 1980年代的北京,物价低,工资也低,普通人月收入几十块,6000块钱是个大数目,能买台彩电或者一辆摩托车。那时候马未都收入不错,稿费、工资加上收藏古董的眼光,家里攒了点钱,算得上小有余裕。张恪智就不一样了,他字写得好,可没稳定收入,靠卖字和零星活计过日子,欠了不少债。马未都看他愁眉苦脸,问了才知道他欠了外人2000块,债主催得紧。他没多想,觉得朋友有难得帮一把,就掏钱给他。张恪智拿了钱,千恩万谢,说一定还。没过多久,他又找上门,说还欠4000块,实在还不上。马未都犹豫了下,还是借了。这6000块他没跟妻子贾宏伟商量,贾宏伟后来听说,气得不行,觉得老马太好说话,钱借出去没个影。她憋着火,没当面发作,但对张恪智印象差了不少。 五年过去了,张恪智没提过还钱的事,照旧常来马未都家串门。他烟瘾还是那么大,聊起书法眉飞色舞,可一说起钱就支支吾吾。马未都心软,不好意思催债,总想着朋友有才华,日子好了自然会还。贾宏伟却看不下去了,她觉得张恪智仗着马未都好说话,把这当理所当然。某天晚上,马未都请张恪智吃饭,酒喝了不少,张恪智脸红脖子粗,话也多了起来。他突然提到手头又紧,想再借点钱。贾宏伟一听,火气蹭地上来,当场问他五年前借的6000块啥时候还。这话问得直白,张恪智愣在当场,支吾几句,没说出啥像样的话。马未都想打圆场,可贾宏伟没给面子,气氛僵得不行。张恪智吃完饭就走了,第二天听说他收拾东西,连夜坐火车去了四川。马未都挺不是滋味,觉得妻子问得太直接,让张恪智面子挂不住,回头还埋怨了她几句。贾宏伟不服,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6000块不是小数,凭啥当没这回事。马未都叹气,觉得朋友之间不该闹成这样,可张恪智一走,音讯全无。 张恪智去了四川后,跟马未都彻底断了联系。马未都一开始还托人打听,拿着张恪智留下的几幅字到处问,可四川那么大,找人跟大海捞针似的,慢慢就没消息了。他日子忙起来,收藏古董、写书、筹办博物馆,生活重心全变了。1980年代末,他跑遍北京的古玩市场,琉璃厂、潘家园没少逛,手里攥着放大镜,盯着瓷器、家具看半天。1996年,他把多年积蓄砸进去,办了观复博物馆,展厅里摆满明清家具、青花瓷,开了中国私立博物馆的先河。2008年,他上《百家讲坛》,讲收藏讲得家喻户晓,书也卖得火,版税收入好几百万。那6000块的债,他早就放下了,偶尔跟老朋友聊起张恪智,只说可惜了他的字,别的没多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