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哺育八女一子,却有八个不同的父亲,到底是美化还是丑化?1994年莫言的母亲于山东高密县去世,莫言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小说《丰乳肥臀》。莫言把母亲描绘成一位承载苦难、命运多舛的民间女神。她生养众多儿女构成的大家族,不可避免地卷入中国社会历史舞台。 莫言出生在一个人口颇多的家庭,作为众多兄弟姐妹中的一员,他是一个“被忽略”的孩子。他对童年自己的描述,带着几分自嘲:“相貌奇丑、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这样的自我认知,或许正是他后来作品中人物性格复杂多变的根源。 现实文化氛围对作家成长的影响,往往体现在家庭、社会、教育等多维度的交织作用中。莫言的文学之路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生轨迹,恰恰印证了文化环境对作家创作风格的深刻塑造。 莫言小学五年级辍学的经历,看似是教育的中断,实则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特殊养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过早离开校园反而让他避开了当时教育体系中可能存在的思想束缚。这种"因祸得福"的经历,使他能够更自由地汲取民间文化的精髓。高密东北乡的乡土气息、民间传说、方言土语,都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这种来自底层的文化浸润,远比课堂上的条条框框更能滋养一个作家的想象力。 童年经验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影响,在莫言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时期的体验往往会在人的潜意识中留下深刻印记。莫言自己也曾坦言,童年的记忆对作家而言具有特殊意义。他在《碎语文学》中的表述,与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的观点遥相呼应,都强调了童年经验对创作欲望的启蒙作用。这种跨越时空的共识,揭示了创作心理学中的一个普遍规律。 高密东北乡的农村生活,构成了莫言文学世界的底色。尽管他20岁后离开了农村,但那些童年记忆中的乡土场景、人物形象、生活细节,都成为他创作中反复出现的母题。这种记忆不仅没有随时间淡化,反而随着距离的增加而愈发鲜明。 苦难的童年经历往往能造就独特的文学视角。莫言辍学后的放牛生活,表面上看是一种被迫的孤独,实则为他提供了观察自然、思考人生的独特空间。在那个没有玩伴的田野里,他学会了与自然对话,培养了敏锐的观察力。这种看似痛苦的经历,恰恰磨砺了一个作家最需要的品质——对生活的细致体察和独立思考能力。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段孤独的时光为他日后创作中展现出的丰富想象力和细腻笔触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莫言现象并非孤例。在中外文学史上,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许多杰出作家都有过辍学或非正统教育的经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文学巨匠。这提醒我们,对作家而言,生活的体验、文化的浸润可能比系统的文学训练更为珍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正规教育不重要,而是说文学创作需要多元化的养分。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鲁迅与莫言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精神传承线索。这种传承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在文学精神内核上的深刻共鸣与创造性转化。鲁迅笔下那个麻木愚昧的"看客"群体,在莫言的作品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更丰富的内涵。 鲁迅在《药》和《阿Q正传》中塑造的"看客"形象,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这些围观革命者被处决、欣赏阿Q游街的民众,构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群体画像。鲁迅以冷峻的笔触描绘这些场景时,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观察者的姿态。正如研究者王吉鹏所言,鲁迅像是一个站在适当距离之外的远观者,用文字再现那些触动他心弦的人生百态。这种创作姿态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批判意识。 莫言对"看客"主题的处理,既有继承又有突破。在《檀香刑》中,他将这个主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小说中围观酷刑的民众,与鲁迅笔下的"看客"一脉相承,但莫言的笔触更为复杂。他不仅描写了围观者的麻木,更深入到行刑者的内心世界。赵甲这个刽子手形象的出现,为"看客"主题增添了新的维度。通过展现行刑者精湛的技艺和复杂的心理活动,莫言让读者看到了暴力美学背后的社会机制和人性困境。 复仇主题的嬗变也体现了两位作家的精神对话。鲁迅笔下的复仇往往带有启蒙主义的色彩,如《铸剑》中黑衣人的复仇就蕴含着对封建专制的反抗。而莫言作品中的复仇则更多地与民间伦理和乡土文化相联系。《红高粱家族》中的复仇叙事,既保留了传统复仇文学的快意恩仇,又融入了现代人对暴力与正义的复杂思考。这种处理方式,使古老的复仇主题获得了新的阐释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对鲁迅的继承始终保持着创造性的距离。在接受采访时,莫言多次强调自己不是简单地模仿鲁迅,而是在消化吸收鲁迅精神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文学表达。这种态度体现了一个成熟作家的自觉意识。正如他在谈到《酒国》创作时所说,重要的是继承鲁迅的批判精神,而不是复制其表现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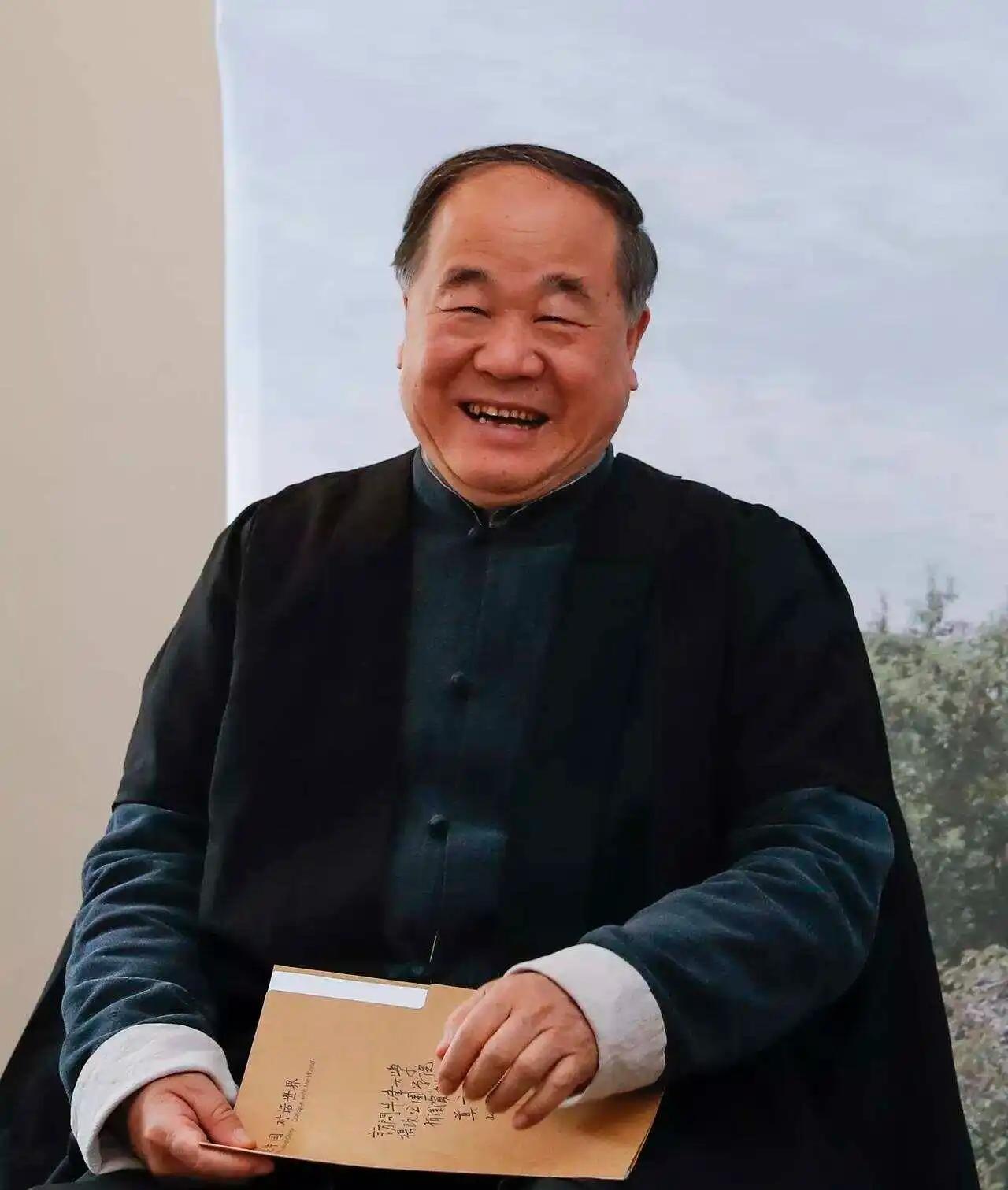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