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隆二十年的深秋,四十二岁的袁枚正在随园竹影下煮茶。青瓷壶里翻涌的武夷岩茶腾起白雾,他忽然想起三年前在山西巡抚衙门的那场“茶局”——裴中丞命人端上熬煮半日的浓茶,茶汤黑如药汁,他硬着头皮喝下,舌尖发麻了整日。此刻他轻啜新茶,笑叹:“世人饮茶如牛饮,哪知茶中有天地?”
一、茶案上的“战场”江宁城皆知,随园主人待客有三不喜:不喜焚香、不喜琴箫、唯茶不可将就。某日钱塘诗人蒋士铨来访,见袁枚正对着茶童发火:“这虎跑泉的水,定是你路上晃散了‘活气’!”原来袁枚煮茶必用特制锡壶,壶内设九曲铜胆,纵快马运送泉水亦能保持鲜活。蒋士铨暗笑其迂,待一盏龙井入喉,竟觉往日所饮皆成俗物。
这般讲究引来不少趣事。袁枚五十寿辰时,门生献上景德镇名家所制“百子贺寿”茶具,他抚着壶身摇头:“胎骨太厚,藏了三分茶香。”转头却用起粗陶小盏,说是某年雪天在龙井村老茶农处所得,盏壁留着经年茶垢,“这才是吃茶的器物”。
二、武夷山上的顿悟五十三岁那年,袁枚的茶道迎来转折。他游历武夷山,初见僧人奉上的深褐茶汤,蹙眉暗忖:“这莫不是煎糊的草药?”勉强入口,苦涩直冲喉头。老僧笑而不语,次日带他登天游峰。晨雾未散时,但见砂砾岩缝间茶树虬曲,僧人采下三片嫩芽:“此茶长在石髓,需历七泡方显真味。”
红泥炉上,茶过三巡,袁枚额角渗出细汗。待第六泡时,喉间忽涌清甜,如月下听松,空山落泉。他掷盏长叹:“往日自负知茶,今日方知舌根尚浊!”自此将武夷茶奉为至尊,在《随园食单》记下:“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

随园的黄昏常飘着茶烟。袁枚煮茶时最喜观察火候,称武火如将军破阵,文火似美人梳头。某日雷雨骤至,他突发奇想接雨水煮茶,写就“瓦铛日取三升水,满院松风听煮茶”之句。侍女墨琴打趣:“老爷的茶诗,倒比茶汤还浓。”
最绝的是他独创的“茶醒诗魂”法。每遇文思枯竭,便令书童取狮峰龙井三克、虎跑泉半壶,待茶烟透窗时泼墨挥毫。那卷被后世称为“茶香帖”的《试茶》手稿,至今可见斑驳茶渍,学者笑言:“这怕不是袁子才洒的茶汤?”
四、最后的茶约嘉庆二年春,八十二岁的袁枚病卧在床。听闻扬州盐商送来明前狮峰新茶,他挣扎坐起:“取我的荷叶盏来!”枯手摩挲着跟随半生的茶盏,忽对弟子说:“茶之妙处,在似有还无之间。当年嫌裴中丞茶苦,如今想来,倒是他比我早悟得人生真味。”
三日后,随园茶烟散尽。人们整理遗物时,发现他枕边紫檀匣里整齐码着十二片茶叶,旁注小楷:“甲戌年谷雨,狮峰绝顶古茶树所采,留待他生再品。”茶早已枯黄,轻嗅却余一缕兰香。

这位“茶痴”文人用一生诠释:茶中真味不在喉舌,而在方寸灵台。从嫌弃武夷茶的固执,到七泡后的顿悟;从苛求器皿的狂狷,到临终前的释然,一杯茶里,照见的何尝不是人生的淬炼与超脱?三百年后,当我们在西湖畔饮着狮峰龙井时,或许还能听见随园竹风里的那声轻叹:“茶有道,饮者需以魂相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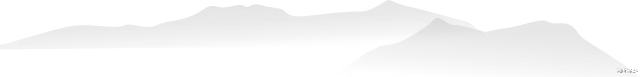
本文来源:图文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如有侵犯到您的权益,请留言告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