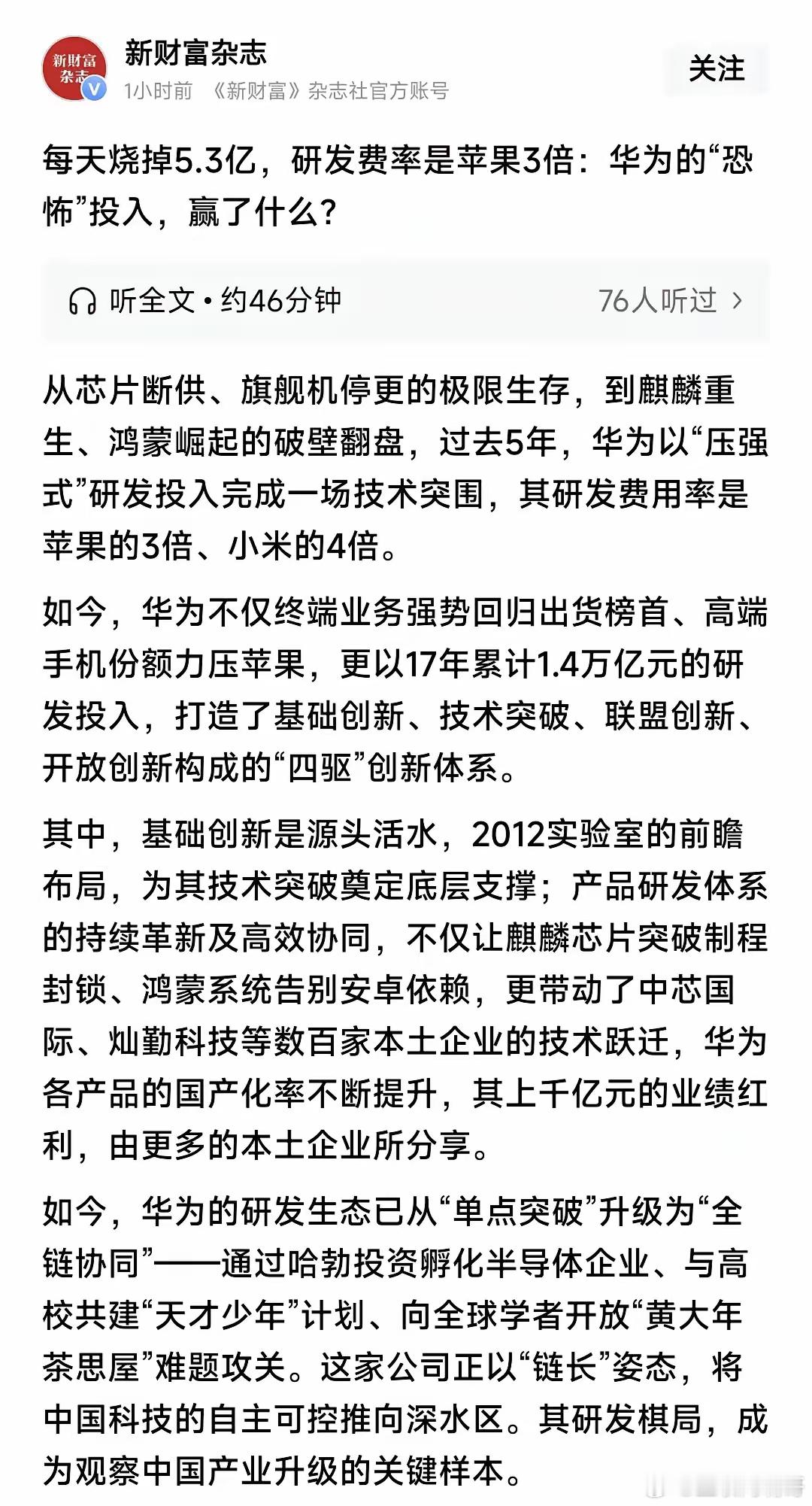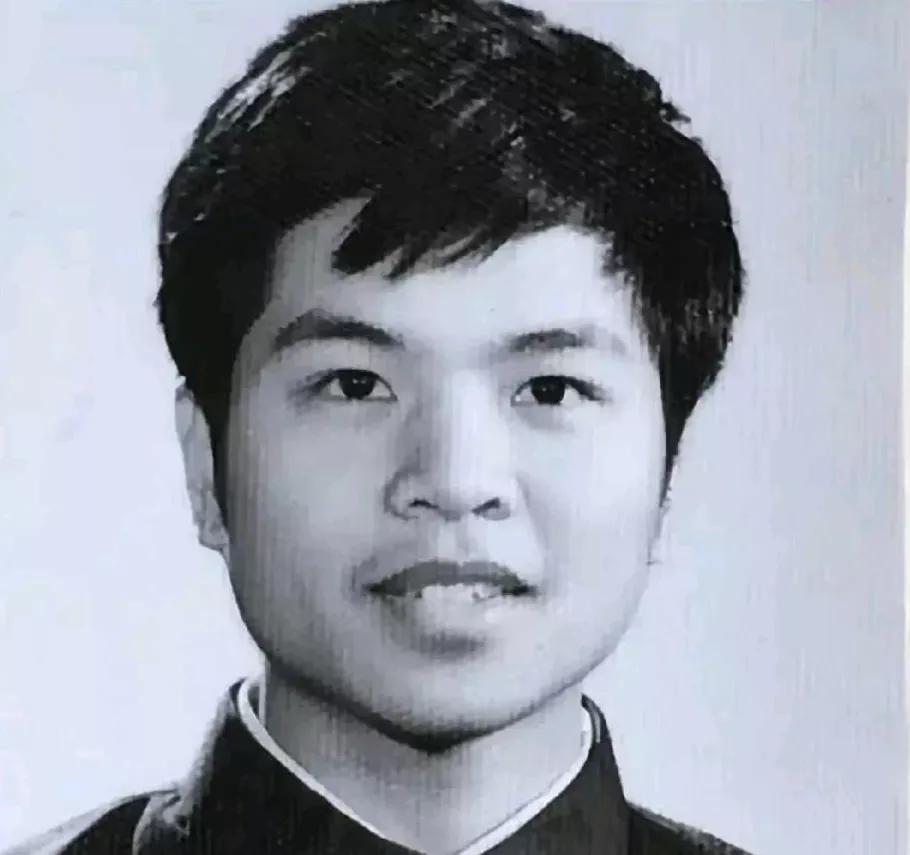1996年,黄大年公费留学后加入英国籍,死也不愿回国,国人怒骂吃里扒外,他却不痛
1996年,黄大年公费留学后加入英国籍,死也不愿回国,国人怒骂吃里扒外,他却不痛不痒。谁料,12年后他却对妻子说:“回国,不答应就离!”妻子傻眼了,没想到美国航母竟也吓退了100海里。黄大年生于1958年广西南宁,那时候家里条件一般,但他从小就爱学习。父母管得严,他每天放学回家先写作业。1977年高考恢复,他考上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专业跟地球探测沾边。大学四年,他埋头苦读,毕业后留校当老师,一边教书一边搞研究。1982年他正式入职,几年下来积累了不少经验。1992年,国家公派他去英国利兹大学留学,他在那边学地质专业,接触到先进设备。1996年他拿到博士学位,英国公司看中他,给他高薪和永久居留。他想了想,就加入英国国籍,进了ARKeX公司,带团队研究航空重力梯度仪。这技术能从空中探测地下资源和目标,精度很高。国内听说他入籍,很多人写信骂他吃里扒外,他收到那些信也没啥反应,继续搞他的项目。在英国,黄大年领导300多人的团队,专注航空重力学和深地探测。他们的项目应用到飞机和舰船上,能精确探测复杂环境下的地球深部。这不光用于找石油天然气,还涉及军事方面的潜艇攻防。航空重力梯度仪就像给地球做CT,能穿透地表看到几百米深的东西。黄大年在那边干得风生水起,团队拿下多项成果。国内一些人觉得他不回来是背叛,但他专注工作,没理那些声音。2008年,吉林大学通过千人计划发邮件邀请他回国任教。他考虑后决定回去,这事在圈子里传开。2009年12月,他从伦敦飞回北京,签了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的合同。他的回国消息对外公布,引起不小反响。2010年年初,美国推出重返亚太计划,跟日本韩国新加坡在黄海外海搞金色眼镜蛇军演,华盛顿号航母参加。这演习地点靠近中国领海,明显是示威。中国公布黄大年回国并签约的消息,他的专业领域跟深海探测相关,能反制美军的技术优势。美军情报部门分析后,调整演习地点,后移约100海里,远离原定区域。这事被解读为黄大年的影响力,他的技术能让中国在潜艇探测上缩小差距。航空重力梯度仪比传统声纳先进,能探测更深海域,即便潜艇噪音低也能发现。黄大年回国前,美军在这技术上领先,中国潜艇部署受限。他的专长提供反制方案,改变了局面。黄大年回国后,很快就接手国家重大项目。2010年2月,863计划十二五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启动,他成领军人物。这项目齐了团队和设备,就缺他这样的专家。他组织上百人攻坚,专注超高精密机械、电子技术和光纤技术。7年里,他们取得多项国际专利,覆盖军事、航空和地质勘探领域。中国在这些空白上实现弯道超车。同期,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项目也启动,黄大年深感责任重大。他觉得这能帮国家追回失去的30年时间。在深探专项第九项目讨论会上,黄大年提出买国外先进设备,升级关键部位。这思路像军工逆向研究,但当时地质界很多人不认可,觉得不符合自力更生传统。他坚持说中国落后太多,得站巨人肩膀上。最终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首席科学家董树文支持。他去世界多地调研,回北京后提出建移动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这平台含地质和地球物理数据,能实时分析探测结果。他预算高,能买两套设备,但解释说只买一套,连后台数据带回来,升级插件后再卖回去。董树文和其他同行起初不看好,但黄大年拿到经费后马上行动。他购入设备,引入项目管理系统,把任务分到每月每周每日,用电脑记录工时。团队考勤严格,有人抱怨说科学家不是机器人。他坚持目标必须完成,自己带头干997,全年无休。每天晚上他登录系统跟踪进度,解决反馈问题。2014年下半年,团队完成24个插件升级,原公司看到成果想买。他谈成合作,换来深入交流。中国在航空梯度深探领域突破瓶颈,提升软件设计,成了翘楚。黄大年还研究无人机平台,自费在地质宫门前建机库。执法部门视作违建要拆,他用各种办法保住。团队先后研制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和地壳1号万米超声钻探装备。中国成全球少数掌握万米钻探技术的国家,国外杂志评价中国进入深地时代。他的工作强度大,身体每况愈下。心脏病加重,还查出胆管癌晚期,但他坚持岗位。2016年11月,他在航班上晕倒,抱紧笔记本电脑,嘱咐助手交给国家。2017年1月8日,他去世,享年58岁。2018年3月,黄大年当选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2019年9月,他获最美奋斗者称号。他的事迹激励科研工作者,很多人投身地质领域。他用实际行动展现对国家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