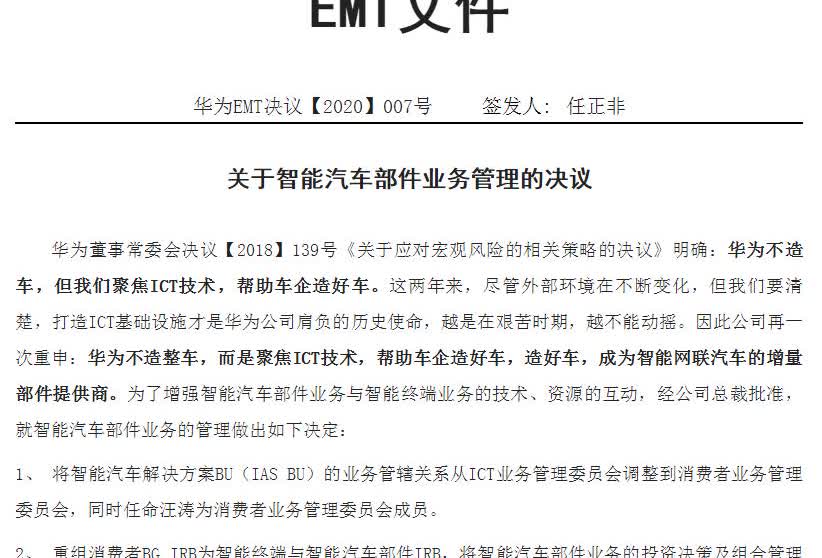汪滔,中国神秘的CEO,是如何一手创立大疆的?他一手缔造的大疆,其无人机却飞上
汪滔,中国神秘的CEO,是如何一手创立大疆的?他一手缔造的大疆,其无人机却飞上珠峰、飞进白宫,几乎无处不在,占据了全球超七成市场,成了中国科技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外界常用“可怕”来形容大疆,这份“可怕”究竟从何而来?是源于它创业初期那段近乎“内部坍塌”的至暗时刻,还是后来直面市场强敌的“外部威胁”,抑或是近几年遭遇地缘政治“围剿”时所展现的惊人韧性?汪涛出生在杭州一个中产家庭,从小就是个航模死忠粉,尤其迷恋遥控直升机。16岁时,父母奖励他一台,可因为操控太难,没几天就摔坏了。这份挫败感没有让他放弃,反而激发了他钻研飞行控制的念头。后来,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电子系,读到大三,觉得课程理论太多、实践太少,索性退学。这个项目最终只得了C,也断送了他出国深造的机会。不过,这次失败却让他被香港科技大学的“创业教父”李泽湘教授记住了。李泽湘看中的,正是汪涛身上那股“是来真的,要搞东西”的劲头,不仅破格录取他为研究生,还给了他极大的自由,任由他旷课继续搞研究。没过几个月,汪涛就捣鼓出了一套能稳定飞行的系统,并以1.5万的成本卖出了5万块,第一次尝到了商业的甜头。李泽湘老师随即建议他去深圳创业。2006年,汪涛借款20万,在深圳一间20平米的仓库里,创立了大疆,主营业务就是飞控系统。汪涛把“极致”二字刻进了大疆的基因。从一颗螺丝的扭矩,到调试方案的细节,他都追求完美,甚至半夜想到解决方案也要立刻打电话给员工。可这种近乎偏执的风格也带来了麻烦:工资低、节奏快、要求高,许多员工干了几天就走人,连最初跟着他的两个兄弟也相继离开。最难的时候,公司只剩他和一名出纳,账上不到两万块,眼看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更糟的是,一名离职员工还偷走了飞控技术,在外面自立门户生产销售。汪涛想维权,却掏不出70万的律师费。创业第一年,技术没成熟,团队散了,钱也快烧光,难道大疆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坐以待毙显然不是汪涛的性格,他再次敲开了导师李泽湘的门。李泽湘二话不说,拉上哈工大的朱小蕊教授,联手投了100万。这笔钱成了大疆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投资。比钱更重要的是人,李泽湘还引荐了一批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毕业生加入。这支技术过硬的团队,迅速把大疆的飞控技术推上了新的高度。到2009年,大疆的飞控系统已能在海拔4400米、6级大风的珠峰下完成近距离拍摄,技术实力站上了世界之巅。汪涛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飞控技术再顶尖,也只是卖给几千个航模发烧友,市场太小,这不符合商业逻辑。他要做的是“人人都能用、用得起、会飞的照相机”。恰好此时,新西兰的代理商反馈,客户对多旋翼无人机的需求远超直升机模型,汪涛敏锐地察觉到,只做飞控已经落后,多旋翼航拍才是真正的入口。可就在这时,对手已抢占先机,2010年,法国公司Parrot发布了全球首款消费级航拍无人机AR.Drone,用App就能操控,一键起飞,价格也亲民,迅速火爆欧美。虽然Parrot的体验差得一塌糊涂,飞几米就偏航甚至摔机,但它的出现着实让大疆出了一身冷汗。汪涛别无选择,只能破釜沉舟:放弃直升机业务,全面转向多旋翼,并且从只做飞控,升级为提供完整的成品整机。这意味着,团队几乎要从零开始。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大疆用一台“精灵”无人机,不仅打破了国外的行业标准,还亲手制定了属于自己的规则。随着大疆日益强大,大洋彼岸的警惕也随之而来。2017年起,一场系统性的打击拉开序幕:美国陆军以“网络安全隐患”为由禁用,内政部叫停所有中国造无人机;商务部将其列入“实体清单”;国防部甚至给它扣上“中国军队旗下公司”的帽子。美国封锁的理由无非两个,表面上的理由是“安全问题”,担忧大疆无人机收集情报;但拨开这层迷雾,更现实的原因恐怕是“抢饭碗”的游戏——美国本土无人机产业起步太晚,市场份额被大疆远远甩开,只能借助行政力量打压,试图扶持本国企业。但这长达八年的制裁,非但没能击垮大疆,反而激发了它惊人的韧性。大疆一边加大自主研发,拿出自己的芯片和操作系统,摆脱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一边积极开拓欧洲、亚洲、非洲市场,用物美价廉的产品迅速弥补了损失。即便在多年的围剿之下,到2023年,大疆依旧占据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70%以上的份额。未来,在中美科技战持续、各国对手紧追的背景下,大疆还将面临更多挑战。但它过往的表现已经证明,这家公司总有办法解决麻烦。它将如何继续它的“可怕”征程,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