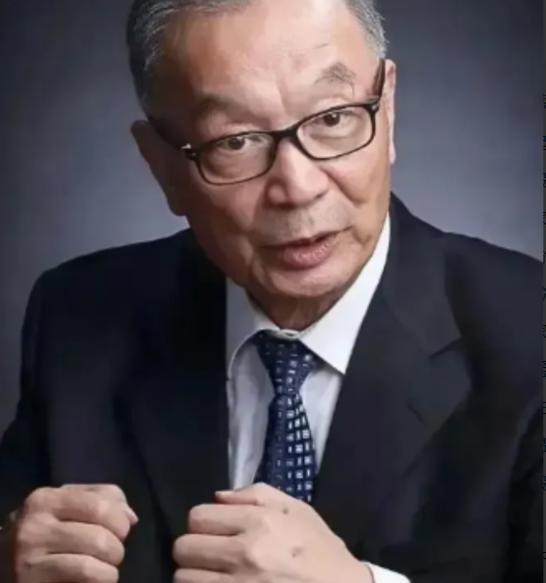现在全网最尴尬的女人可能就是这位当街应急的姑娘了。你以为她想在大庭广众下难堪吗
现在全网最尴尬的女人可能就是这位当街应急的姑娘了。你以为她想在大庭广众下难堪吗?有目击者说,姑娘当时抱着个鼓鼓的书包,急得额头都冒冷汗,一路小跑着找厕所,问了两个便利店都说“内部厕所不对外”,导航上显示最近的公厕在1公里外的商场里。她后来蹲在路边绿化带时,还特意用书包挡着,肩膀一抽一抽的,估计又急又委屈。换作是你,要是赶时间接孩子,突然肚子疼得直不起腰,周围连个能应急的地方都没有,你能怎么办?总不能真的硬扛到出问题吧?再说女性如厕排队这事,根本不是“忍忍就过去”的小事。国家早在2016年就规定,城市建成区公厕密度要达到每平方公里3-5座,可去年有媒体调查,像深圳福田CBD、上海陆家嘴这些人流量密集的地方,实际密度还不到2座,有的写字楼周边,连个移动公厕都找不到。更别说女性如厕时间本就比男性长——生理结构不同,加上很多妈妈要带孩子、有些姑娘要补妆,排队10分钟都是常事。去年我在西安旅游,景区女厕所排了20多个人,前面的阿姨急得直拍腿,说“再等下去就要尿裤了”,最后还是工作人员临时开放了员工厕所才解了围。那些嘲笑姑娘“没素质”的人,怕是没经历过这种“急到绝望”的时刻。有次我闺蜜出差,在高铁站赶车,还有10分钟就要检票,突然想上厕所,女厕排了长队,男厕没人,她跟保洁阿姨好说歹说才进去用了残疾人隔间,出来时差点误了车。她说那时候根本顾不上尴尬,满脑子都是“千万别迟到”。这位当街应急的姑娘,说不定也是遇到了类似的急事,只是没那么幸运找到临时解决方案而已。更讽刺的是,很多城市宁愿花大价钱建网红打卡点,也不愿多建几个公厕。去年郑州某商圈建了个“星空走廊”,花了几百万,可周边3公里内只有两个公厕,还经常排长队;反观杭州,在地铁站、公交站附近加建了不少移动公厕,还特意标注“女性优先通道”,有的公厕里还配了母婴台、卸妆棉,细节做得特别到位。其实公厕才是最能体现城市温度的地方——它不用多豪华,只要够多、够方便,就能让普通人少点尴尬,多点安心。现在姑娘的视频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有人把她当成“反面教材”,却没人问一句“为什么她找不到厕所”。我们真正该关注的,不是她“失不失态”,而是怎么让城市的公共服务跟上——多建几个公厕,合理分配男女厕位,在人流密集区设置临时应急厕所,这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毕竟,谁都可能遇到“来不及”的时刻,少点指责,多点解决问题的办法,才是一个城市该有的样子。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