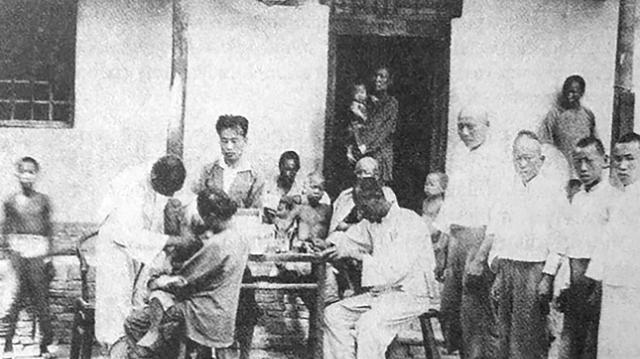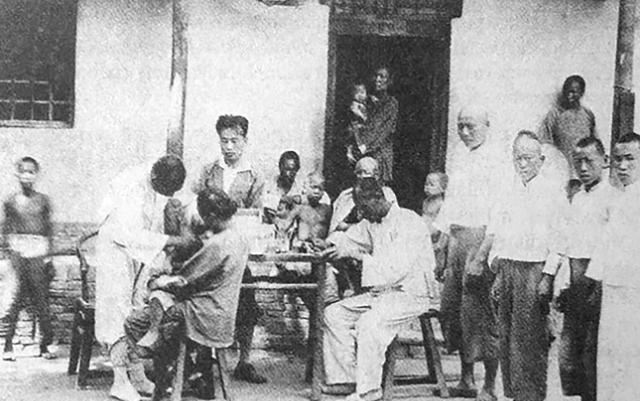建国前,解放军出现奇怪一幕:入城后,清除中南海淤泥16万吨,当时在水下到底都挖到
建国前,解放军出现奇怪一幕:入城后,清除中南海淤泥16万吨,当时在水下到底都挖到了啥?主要信源:(澎湃新闻——中南海:红墙往事)1949年初春,北平刚解放不久,城里头许多大事小情都得从头收拾。中南海这地方,过去是皇上家的园子,后来北洋政府、国民党也都用过,可连年战乱,根本没人好好打理,房子也旧了,湖也淤住了,看着实在不像个样子。但新中国马上要成立,中央机关总得有个地方办公,中南海就被定下来了。不过在那之前,得先把它彻底清理一遍。最要紧的就是那几个湖。多年没清过,淤泥越积越厚,水都发黑发臭了。这还不算,谁也不知道湖底下还藏着什么。万一是武器、炸弹什么的,那可太危险了。所以清淤这活儿,不光是搞卫生,更是排除隐患。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的部队。那时候人手工具都简单,没什么机械,主要靠战士一锹一锹挖、一筐一筐抬。二月初天气还冷着呢,湖面刚化冻,水刺骨得凉,战士们卷起裤腿就下去了。先把水抽干,露出来黑乎乎的淤泥,有的地方深得能陷进去半个人。清淤可不是轻快活儿。战士们分成几班,昼夜不停地干。一开始挖出来的都是烂泥、碎石头、枯树枝子这些寻常东西。但越往深里挖,就越出稀奇玩意儿。最先挖出来的是武器。枪啊、刀啊、子弹啊,啥都有,全都锈得不成样。有的枪管子弯了,刀也缺了口,子弹更是锈成一疙瘩,根本不能用。看样子是过去几十年里不同部队留下的,说不定是军阀混战时候扔的,也可能是日本人或者国民党撤走时没带走的。这些铁家伙堆在湖边,跟座小山似的。有一回,一个小战士在泥里摸着个冰凉的铁环,掏出来一看,是副手铐。锈是锈了点,但机关还没坏。他觉着好玩,就往自己手腕上一扣,结果"咔嗒"一声锁上了,摘不下来了。急得他满头大汗,最后还是班长拿钥匙给捅开的。大伙都笑他,说这是"中南海送给他的见面礼"。除了武器,还有些意想不到的发现。有一回,一个战士的铁锹碰着了硬东西,挖出来一看,是个沾满淤泥的银镯子。擦干净了,上头还雕着精细的花纹。后来陆陆续续又挖出不少好东西:玉佩、银元宝、铜钱串,还有碎了的花瓶瓷片。银元宝底下还刻着字,大伙儿传看着,猜是哪个年号的。这些八成是清代皇室留下的物件,不知怎么掉进湖里,一埋就是这么多年。每挖出这些金银首饰、古钱瓷片,战士们都特别小心地拿布包好,做好记录往上交。他们知道,这些老物件能帮人们了解过去的皇家生活和战争历史,都是宝贵的文物。整个清淤工程干了三个多月,前后清理出十六万吨淤泥。你算算,这得是多少筐、多少车才运得完?战士们真是下了大力气。等淤泥清干净,湖底露出来,是平整的沙石地。这时候才能放心说,湖里头再没什么危险东西了。完事之后,中南海接着就开始大修。房子该补的补、该刷的刷,路重新铺,树也修剪了。等中央机关搬进来的时候,中南海已经焕然一新,既保留了老园子的气派,又能满足新政府的办公需要。从那以后,它就一直是中国最核心的地方之一了。回过头看,当年清湖清出来的那些东西,就像是把过去几十年的乱世都给挖了出来。武器弹药是打仗留下的痕迹,手铐可能关联着某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而鱼和藕呢,倒让人想起这地方本来是个有活气儿的园林。解放军战士们这一通忙活,清走的是淤泥,也是旧时代的沉渣。这段清湖往事,不仅让中南海重现光彩,也成为北平解放初期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实际工作。后来人们常说,中南海的清水,是从解放军战士们的汗水里捞出来的,这话一点也不假。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