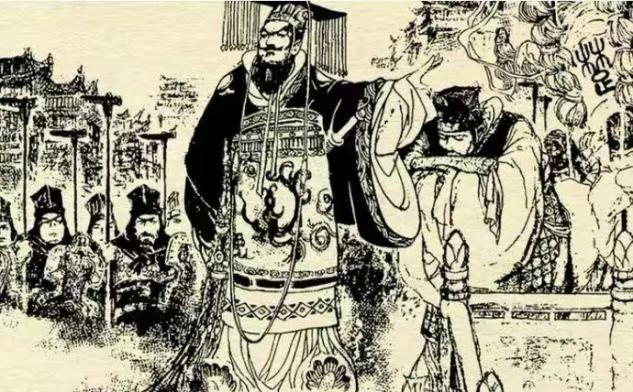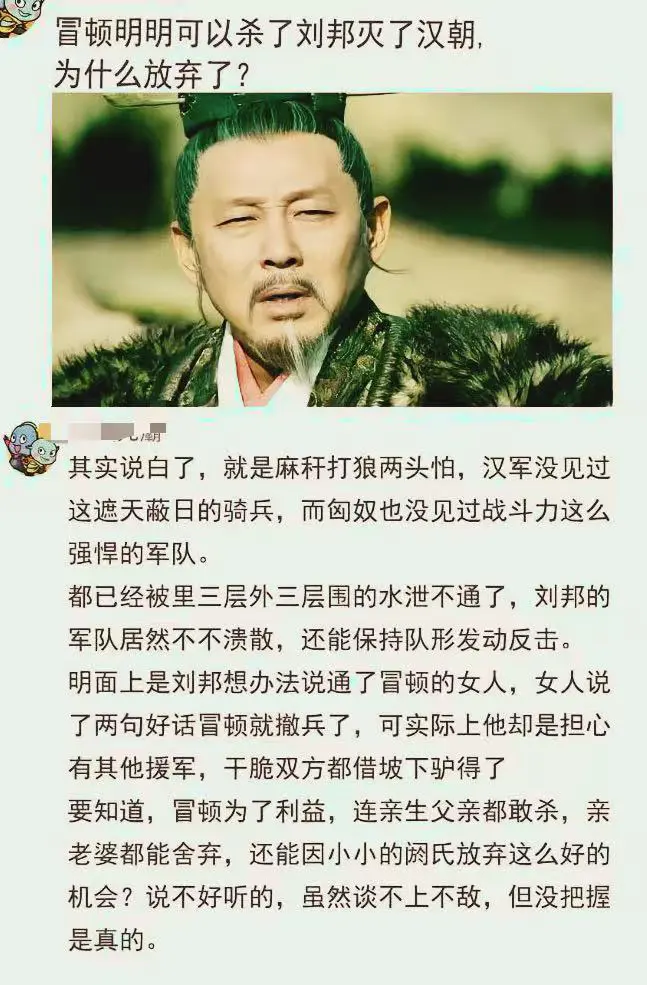前言:公元前453年,晋阳之战的硝烟尚未散尽,新兴的魏氏便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从晋国卿族到战国霸主的蜕变。在魏文侯的改革风暴中,这个处于四战之地的国家迅速崛起,其魏武卒横扫四方,击败了齐、秦、楚等传统强国,开创了战国时期的第一个霸权体系,且时间长达百年之久。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公元前225年,黄河之水以雷霆之势倾向大梁城墙,其国宣告灭亡。在《史记》的斑驳竹简中,其国最后的三年时光被浓缩成简简单单的两句话,“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整整三年,这个昔日的霸主竟没有值得载入史册的内政举措、外交博弈墩或军事行动。鄂G君不禁想问,这是为何?

晋阳之战后,三家分晋
一、霸权之巅的战略膨胀1、变法图强
赵韩魏三家分晋时,魏氏是比较尴尬的,其底蕴比赵、韩略显薄弱,参照自晋文公时期开始的六卿制度,赵氏先后3人出任正卿,累计执政45年,韩氏1人,执政34年,魏氏1人,执政5年。最关键的是其领地被韩氏隔离成了东西两部,几个传统强国均与之相邻,占据了智氏地盘的赵氏还压在它头顶上。
公元前446年,继承家业的魏文侯决心振作,化地缘压力为进取动力,他任用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在运城盆地实施精耕细作,使魏国粮仓充盈。之后,西门豹治邺,修建十二渠,引漳水溉田,将东边的盐碱地改造成膏腴之地。国富了,剩下的就是强军,吴起创立的武卒制度将魏国的军事专业化推向巅峰,五万重甲步兵成为横扫列国的武装洪流。

西门豹治邺
2、制霸诸侯
在魏武卒的金戈声中,魏国开启了四面扩张的狂飙模式。西线战场,吴起率军连破秦军,夺取河西之地七百余里,秦人被迫退守洛水以西;东线战场,三晋联军攻入齐长城,斩首三万,俘获齐康公;南线战场,屡败楚国,夺取大梁周边战略要地,并借机吞掉了韩国的河内地。北线战场,从赵国手里夺取了漳水南岸,顶住了赵国南进中原的基地,并跨域吞了中山国,兵锋直抵燕国,俨然成为中原主宰。
这种军事胜利催生了危险的战略错觉,魏武侯、魏惠王在位期间继续维持多线作战态势。公元前393年,武侯同时向秦、郑两国开战;公元前383年,武侯派军攻打赵国,三晋同盟自此破裂;公元前373年,武侯派军伐齐;公元前341年,惠王伐韩攻楚。这种四面树敌的扩张策略,使魏国在巅峰时期就埋下了衰亡的种子。正如《战国策》所载:“魏王恃其强,数伐诸侯,诸侯皆患之”。

魏国巅峰时期的形势
二、霸权衰落的转折密码1、志满则骄
人贵有自知之明,魏国自魏文侯之后的历代君主均无自知之明,明明是魏文侯打下的底子厚实,才让魏国得以强大,他们却将魏国的强盛和自身能力挂钩,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想想魏文侯,从不打无用之仗,到了魏武侯就开始乱打一气了,战略目标极度混乱,军事上的胜利并未换来什么实质性的收获,反倒是自身在不断被消耗。
瞧瞧魏惠王,桂陵之战的惨败已经给魏国敲响了警钟,他还颇为自信地率先称王,并主动停止西线与秦国的战争,让秦国得以安全变法,转头撕毁和齐国的和议,继续发动对外战争,结果马陵之战一来,魏国精锐尽丧,威势扫地,整个中原的战略平衡被打破,昔日的警钟演变成了丧钟。

马陵之战
2、内外格局
连年被魏国欺压的秦国力行图强,经商鞅(因魏惠文弃之不用而投附秦国)变法而焕发新生,其耕战体系逐渐释放出惊人之力;齐国在威王治下悄然崛起,与秦国一道对魏国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楚国原本在和三晋争战中胜少败多,结果魏武侯听信谗言,致使吴起跑到楚国搞变法,楚国国力显著提升。北边的赵国亦通过胡服骑射完成质变。这些力量如同精密齿轮,将魏国推入战略绞sha网。
外部格局的剧变加速了魏国霸权的崩塌,而其内部治理的全面溃败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魏惠王后期在连横和合纵之间左右摇摆,错失中兴良机,其宗室贵族把持军政,使得“宗室非军功不得属籍”的制度形同虚设,再加上连年争战使得经济疲敝,比如因水利失修而导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当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传奇落幕,魏国最后的智慧也随之湮灭。

商鞅变法
三、黄昏中的战略瘫痪1、伊阙之战
秦国之所以在与魏国的军事斗争中长期处于劣势,概因魏文侯西出黄河,夺取了河西和上郡,并结合山河之利,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秦国形成压制。可惜因后继之君的庸碌,防线一再收缩,公元前333年,魏惠王割阴晋(今陕西甘泉南)予秦,致使魏国西长城洞开,紧接魏惠王错用公子卬为帅,致使龙贾麾下的8万精锐河西军团尽丧,魏国不得不将河西献给秦国。
公元前328年,魏惠王又在张仪的诓骗下将上郡(今陕北)仅剩的15城送给秦国,让秦国可以心无旁骛地渡河西进,攻略其运城盆地。公元前293年,秦军再度出关,试图彻底打通东进通道,魏昭王联合韩国出动24万大军在伊阙(今洛阳龙门)御敌,可惜两军互相观望,被秦军各个击破。自此,中原门户洞开,秦军可轻易抵近大梁(今开封)。

伊阙之战
2、集体失能
从魏昭王到魏安釐王、魏景湣王,史册中记录最多的就是某某年,秦攻魏,夺取多少城。其国已无任何可倚仗之力。经济上,“大县数百,名都数十”的繁华已成过往,取而代之的是“民力罢敝,府库空虚”的惨状;军事上,除了信陵君的昙花一现,其它时间甚至拿不出本钱来整军备战、构建防线;外交上,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联秦,完全没有主动权和应有的章程。
待到魏王假(景湣王之子)继位,魏国已经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了,唯有保持静默状态,不是不敢为,而是没有资本。当秦军抱着灭国之心而来时,魏国朝堂上争论的不是如何抗敌人,而是“割地”或“合纵”,无人想到大梁城防的致命弱点。这种集体性战略失能,使得经营上百年的魏都竟在黄河水攻下迅速陷落。

战国大后期的魏国
四、关键变量:那些被魏国给错过的人才1、范雎和尉缭子
治国首在用人,魏文侯善用人才,才有了魏国的百年霸业,而他的后继者却白白让魏国流失了许多人才,其中甚至有不少顶尖人才。除了前文中提到的商鞅和吴起外,还有范雎和尉缭子等,后面的这两位都是超一流的战略家,而这恰恰是魏国所欠缺的。范雎是根正苗红的魏人,他在陪同须贾出使齐国期间仗义执言,维护了魏国尊严,可最后不仅未得到提拔和重用,还差点丧命。
弃魏奔秦的范雎给秦国带去了著名的“远交近攻”之战略,让秦国稳步前进,不断蚕食邻国土地。尉缭子同样是到的秦国,他给秦国制定了“笼络燕齐,稳住魏楚,消灭韩赵”的战略方针,并提出“赂其豪臣,以乱其谋”,让嬴政收获颇多,比如赵国柱石被秦国离间致死,齐相后胜因被秦国收买,屡屡劝谏齐国不备战、不助它国御秦。

远交近攻
2、公孙衍和魏章
前文中提到的魏国河西防线洞开,这个离不开公孙衍对秦国的助力,他本是魏国河西人,弃魏投秦后,亲率秦军夺取阴晋、消灭龙贾、占领河西。后再度回到魏国任职,一度搞出“五国相王”的中兴景象,可惜魏惠王意志不坚定,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让他无法全力发挥。
魏章是秦惠王手底下的名将,他曾率军打赢了丹阳之战和蓝田之战,前面一战让楚国损兵8万,将领70余人,后面一战直接打垮楚国集全国之力组建起来的30万大军,使得楚国彻底失去汉中的控制权和应付秦国的主动权。值得一提的是,魏章和张仪在秦国上演了将相和,而张仪同样也是魏国人。

五国相王
结语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魏国的兴衰轨迹犹如一部生动的战略教科书。其崛起印证了制度创新的决定性作用,其衰亡揭示了战略透支的毁灭性后果。当霸权的光环蒙蔽了战略理性,当军事胜利滋生出扩张躁动,即便强如魏国也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总而言之,魏国最后三年的空白恰似一面铜镜,映照出了战国时期的残酷法则。
其一,当一个国家失去战略方向时,连最后的挣扎都显得苍白;其二,人才的流失比土地的丧失更加致命;其三,没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再辉煌的霸业也终将沦为历史尘埃。这种跨越时空的战略警示,对于现下的国际风云仍具有强烈的镜鉴意义——真正的强大不在于四面出击的威风,而在于审时度势的智慧。
参考文献:《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