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戏曲研究界时时有一种危机感,大体说来,这种危机可以有两个层面的解读:一是研究出现停滞,缺少新的令人振奋的突破。长期以来,戏曲史研究者大多依循王国维当年开创的治学模式,主要将戏曲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进行研究,将研究对象限定于戏曲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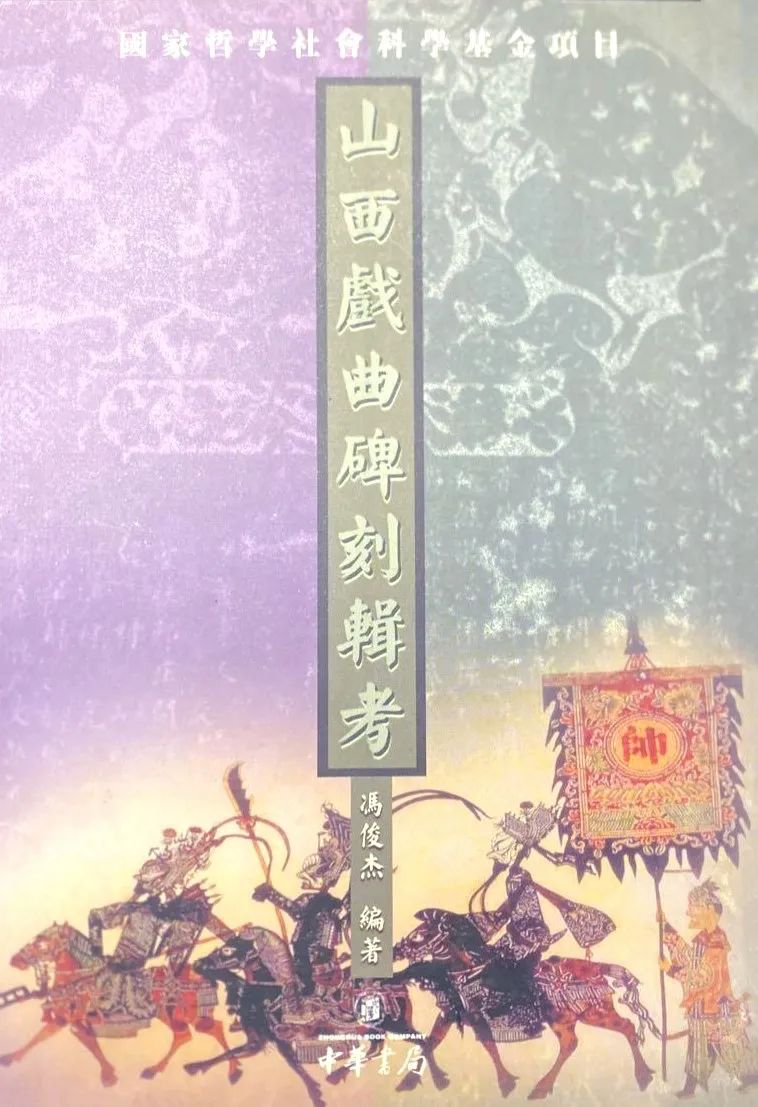
自然,剧本也是戏曲的重要组成因素,不是不能研究,但是如果以偏概全,将戏曲研究完全等同于剧本,使目光局限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忽视了戏曲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的其他特性,这种研究就存在问题了,正如邓绍基先生所言:“完备的中国戏曲史著作实际上应当是戏曲文学史、戏曲理论批评史、戏曲声腔史、剧场史、演艺史(戏班剧团、角色行当和脸谱扮装等)诸多方面的综合、系统著作。”(《山西戏曲碑刻辑考》序)
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整整一个世纪,戏曲史研究基本上就是在这种以偏概全的状态下进行的,尽管也有一些关注舞台艺术的戏曲史家不懈努力,但一直无法扭转戏曲研究的这种文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这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学术积累,当戏曲的文学资源得到比较充分的挖掘后,研究出现危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不过,如果放宽眼界,从整个戏曲研究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态势来看,这种危机还没有达到威胁学科生存的地步,甚至可以说,危机的到来是一件好事,是一个良机,可以以此为契机,对整个学科近百年来的发展演进状况进行反思,吸收新的学术资源,对学科内部结构进行一次新的调整。

《宋元戏曲史》
事实上,经过几代学人的辛勤耕耘,进行学科内部结构调整的学术条件已经具备,近几十年来,基于考古挖掘的戏曲文物学研究、基于田野调查的泛戏曲形态研究和基于广阔历史背景的戏曲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戏曲研究的三个新增长点,成果斐然,生机勃勃,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也正是因为这些新的发现和探索,使戏曲史研究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危机,那就是原先支撑戏曲史研究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框架已经无法容纳新的文献和成果,显得陈旧过时,或者说无法对戏曲发展演进的真实景观进行有效解说。
危机是突破的前兆,这样,重写戏曲史就成为研究取得突破的一种标志,成为戏曲研究者的一种默契和共识。事实上,近些年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在从事这项重写工作,他们或创办刊物,进行探索和呼吁,如胡忌主编的《戏史辨》初、二、三编的出版,或进行戏曲史的写作,如台湾学人曾永义撰写的《戏曲演进史》。

《戏曲演进史》
可以预期,在今后数年中,随着一批新成果的陆续面世,戏曲史研究将会进入一个新的收获期。
仅就戏曲文物研究这一块来讲,可以说它是戏曲史研究的一个新的支撑点。经过数代学人的不断探索和积累,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它的发现改变了中国古代戏曲特别是宋元戏曲文献资源严重缺乏的局面,改变了以往仅仅以剧本为依据的不利情况,对戏曲舞台表演、剧场建筑、戏曲民风习俗等方面有新的揭示。同时它还有着方法论上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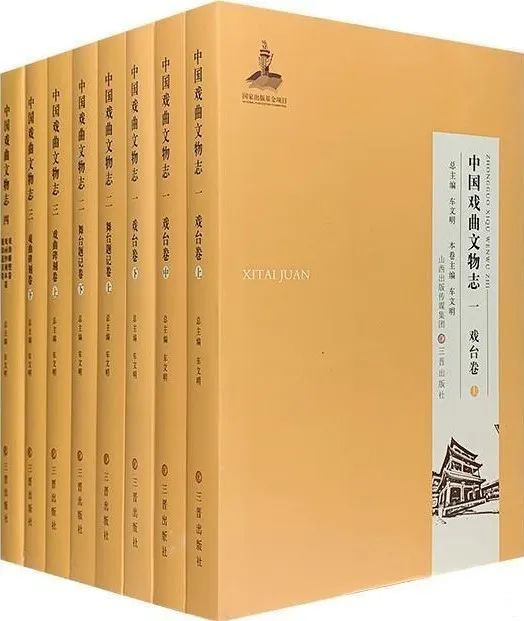
《中国戏曲文物志》
老实说,如果仅仅依靠书面文献,明清以前有关戏曲舞台表演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无法进行。但是,戏曲文物研究借助地下文物的挖掘和地面文物的调查,部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使一些学术悬案得到完满解决。
可以说,它对戏曲史研究不仅提供了观点上的文献支持,而且还逐渐改变了戏曲史研究的学科性质,使其变成了一门多学科密切配合、具有很大包容性、开放性的学科,与诗文、小说那种纯案头的文学研究形成明显的区别。
就目前戏曲史研究的状况而言,王国维在二十世纪之初所归纳的两重证据法显然已不能准确阐述戏曲史研究的模式,书面文献研究、文物考古与田野调查等多种研究方式的有机融合已经使戏曲史研究成为三重证据法的典型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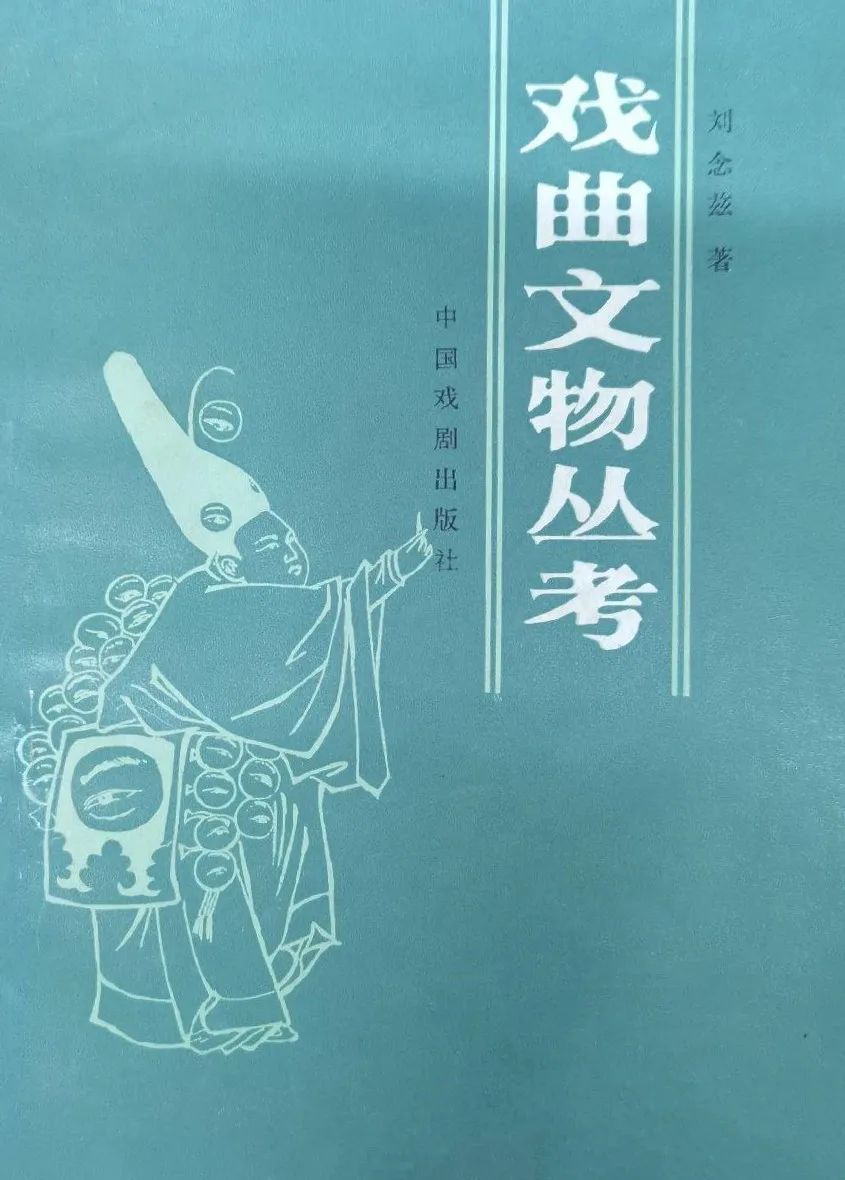
《戏曲文物丛考》
在戏曲文物学的学科形成过程中,卫聚贤、齐如山、傅惜华、张次溪、赵景深、周贻白、徐苹芳、刘念兹等先辈学者付出了很大努力。他们的关注、提倡和研究对学术风气的孕育和研究方法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示范作用。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戏曲文物的研究开始形成规模和风气,并得到学术制度上的保证。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戏曲文物学的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山西师范大学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两家科研单位,尤其是前者,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断努力,依托当地极为丰富的文物资源,已经形成了一支较为齐整的研究队伍。
近些年来,他们先后出版了《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戏曲文物研究散论》(黄竹三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车文明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戏曲文物通论》(黄竹三、延保全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戏曲文物志》(车文明主编,三晋出版社2016年版)、《中国戏曲文物与演出叙论》(黄竹三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等著作,构建了一个中国戏曲文物学的学术体系,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
目前他们设立有专门的戏曲文物学硕士点,使戏曲文物的研究有了后备人才上的保证,实现了研究工作的可持续性,一批年轻的研究者正步入这一领域,同时创办了《中华戏曲》刊物,注重刊发戏曲文物方面的研究成果。
山西是一个文物大省,当地的戏曲研究者充分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特色,为戏曲史研究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当然,地利只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便利,它还需要研究者的不断开掘和辛勤劳动才成形成学术优势。
别的省份比如河南,尽管也有很丰富的戏曲文物资源,但在戏曲文物的研究上要落后于山西,虽然也有廖奔、杨健民等研究者进行过调查研究,相继出版了《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廖奔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剧场史》(廖奔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杨健民著,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河南戏曲文物》(冯建志、刘明阁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著作,但未能在河南学界得到积极回应。

《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
尤为重要的是,虽然该省也有不少高等学府和学术机构,拥有相当的学术力量,但直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设立专门的戏曲文物研究机构,形成一支专门的戏曲文物研究队伍,丰富的文物资源与单薄的研究力量的投入形成很大的反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自然,虽然已有一定的学术积累,但戏曲文物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还应该算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总体上还处在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整合阶段。
还有不少更为系统、深入的工作要做,比如要尽可能多的发现新的戏曲文物,进行戏曲文物的普查,拓展新的文物资源;对已发现戏曲文物进行认真准确的辨析、整理和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将所发现的一件件具体文物放在中国戏曲史形成、发展与演进这个大的背景下,使其有机的融入到戏曲史研究中,成为恢复和阐释戏曲史原生态的有效文本。在这方面,还是有许多潜力可挖的,它也应该是戏曲文物学今后努力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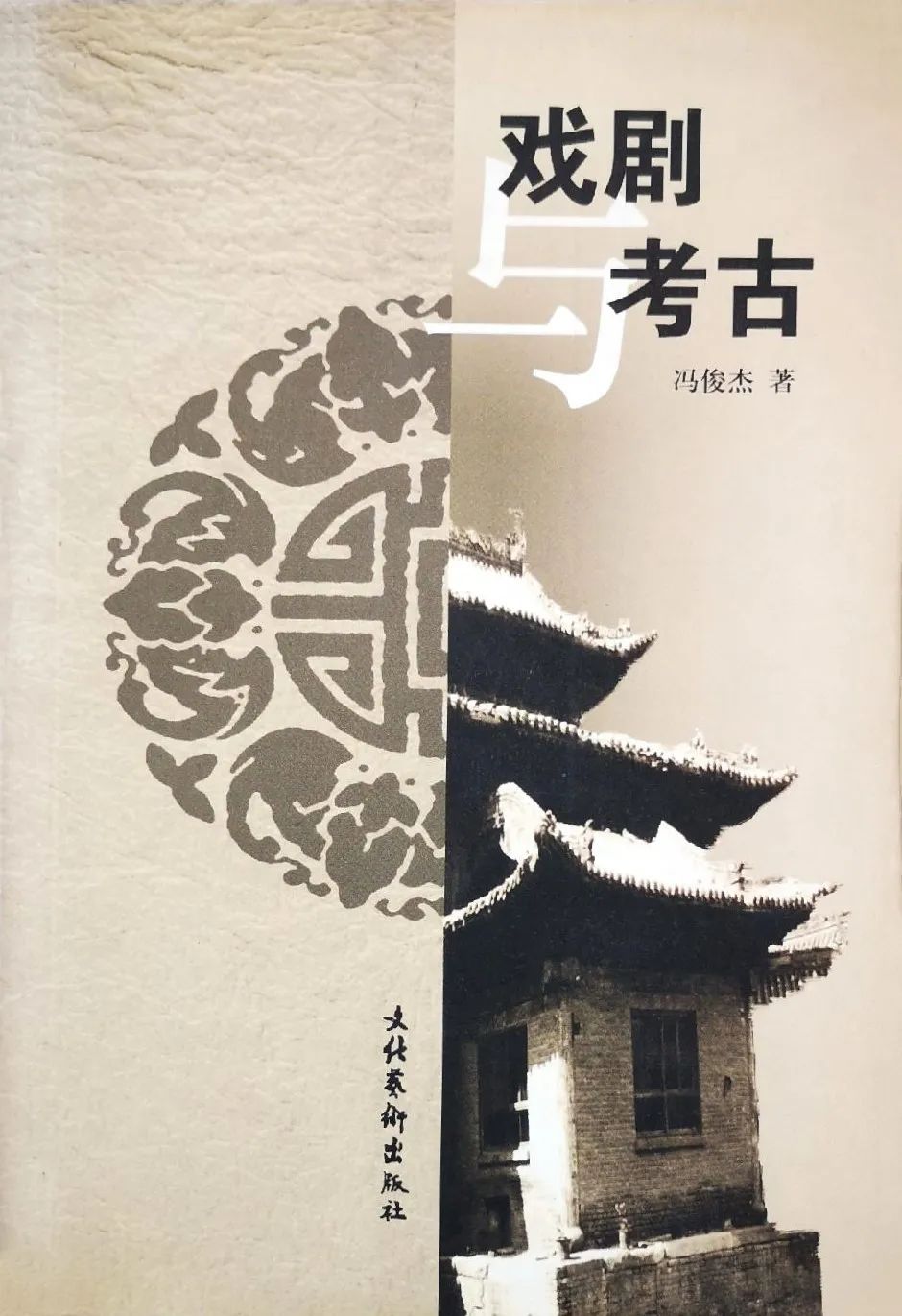
《戏剧与考古》
从这个背景和角度来看,冯俊杰先生出版的《戏剧与考古》、《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二书所进行的正是这样的基础建设工作,也正是从这个背景和角度,才能更为清晰地凸显这一工作的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
两书虽然性质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所涉及的都是同一个领域,是戏曲文物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即戏曲神庙建筑和戏曲碑刻。
《戏剧与考古》一书是作者该项研究的论文集,由于题目的相近,论文间有着内在的内容关联,故该书可看作是一本较为全面论述神庙与中国戏曲关系的著作,它涉及到神庙舞楼的创建普及、神庙剧场的改革完善、神庙戏曲碑刻的辑考、神庙祭祀与戏曲民俗等诸多问题,基本上涵盖了社庙与戏曲关系的各个方面。

《中国戏曲文物文献汇编▪戏曲碑刻(一)》
后者则辑录了一百块山西戏曲碑刻的碑文,以明代以前的戏曲碑刻为主,并对每一块戏曲碑刻的基本情况及其所透露的戏曲信息进行考订介绍。正如作者本人所言:“关于创修戏楼和祀神演剧之事,多是些只言片语,散落在这些重修祠庙的碑刻中,然而一旦经检选并综合起来,就会显示出极为可贵的戏曲史料价值。”(《山西戏曲碑刻辑考》前言)
这种具有原创性的资料汇编和研究有助于对戏曲史研究的丰富和深化,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
两书虽然在性质上有所差异,但在写作上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考述建立在丰富而坚实的文献基础上,言必有据,力戒肤泛之语。这些戏曲文物多系作者等人积年调查所得,凝聚了研究者的大量心血。

《中国戏曲文物通论》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将戏曲文物、田野调查与书面文献进行相互印证,不仅增加了立论的力度,而且具有方法论方面的启发意义。三种研究方式的有机融合,构成了戏曲史研究的立体景观。
总之,这是两部厚重朴实,有着相当份量的戏曲文物学研究著作,作者为之付出的大量劳动和心血必将赢得学界的尊重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