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这原本在江湖流人、兵伍中兴起的娱乐方式,随着时日的推移,渐渐从江湖走向闺阃,从广场街衢走向后堂深院,在妇人女儿中流行开来。

《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
小说在闺阁深院的盛行,在宋元间并未见记载,关于女性读者唯一肯定的说法是在成化年间。在嘉定发现的成化间说唱词话,就是埋藏在当地宣氏家族的一座女墓中。
这令我们想见,可能在15世纪,闺阁中阅读词话已经颇为盛行了;正是因此,家人——也或是应“她”的要求——才将“她”生前嗜好的词话作为一种纪念埋在了她的墓中。
成化间说唱词话可以说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早的明代词话,明代通俗小说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


当章回小说兴起时,是否存在着女性读者,如果有,有多少,又是哪些人?要追究这些问题,几乎是极为困难的,因为没有谁对此做过哪怕是最粗略的统计。那么,我们只能退一步,先来推衍当时究竟有多少女性可以阅读小说。
(一)影响女性阅读的几个因素
伊恩·P·瓦特指出,由于大量闲暇时间的存在,文学,包括小说已成为女性主要的消遣物。[1]
不过,就章回小说而言,长期以来人们或者视之为文人士子把玩的艺术品,或者视之为市井百姓沉迷的消遣物,而很少有意识地去辨别读者的性别。
一些研究者偶尔也注意到了女性阅读与小说内容的关系,[2]不过这些评论都只是零星半点的,淹没在对小说意蕴的整体论述中。
直接受伊恩·P·瓦特的影响,在小说史中专门论述中国白话长篇小说女性读者的,大约是西方的何谷理和马兰安。[3]他们认为女性走向小说的阅读,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识字能力,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阅读机会,包括相当的自由度、足够的经济能力与充裕的空闲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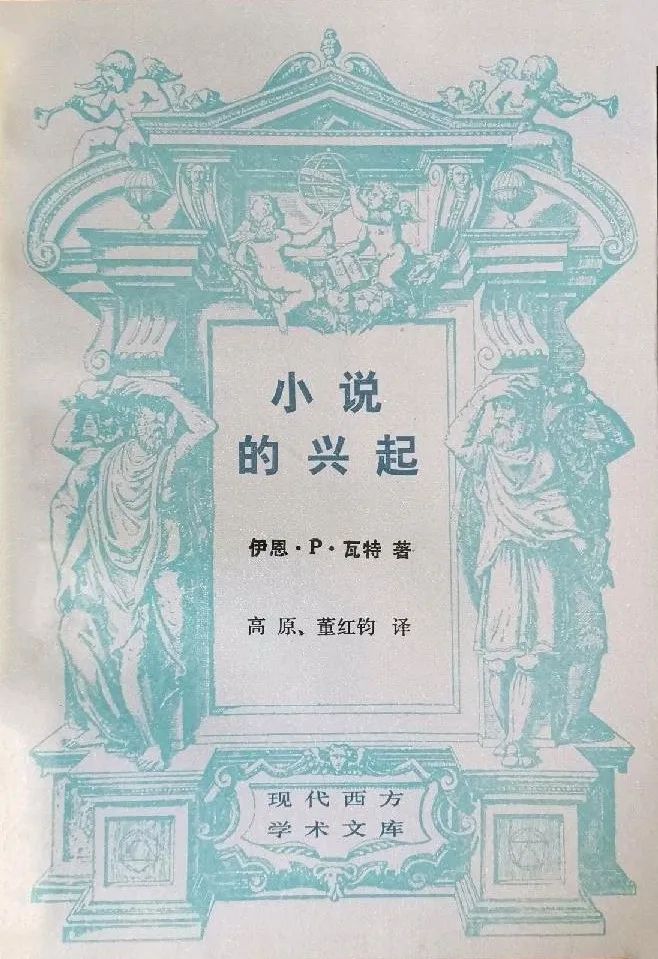
《小说的兴起》
为此,他们历数了妇女识字水平提高、出外买卖行走与出入勾栏寺庙的自由,以及大量闲暇时间的存在等现象,从而肯定了女性成为白话小说读者的可能性,并列举了明初以来女性阅读通俗读物的一些事例。
然而,这一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二人却均流露了某种怀疑。何、马二人首开风气之先,将女性阅读纳入了中国通俗小说史的研究,为后人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不过作为最初的论述,他们主要还是侧重于一种“有什么”、“是什么”的事实介绍,而没有继续追究女性阅读与章回小说兴起之间的逻辑关联。
也许,何、马二人毕竟一个侧重于十五世纪的词话,一个侧重于十七世纪的章回小说,那么,在十六世纪,当章回小说在词话以外蓬勃兴起时,女性阅读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多少女性、又是什么样的女性,她们是因为什么原因、又是以什么方式参与章回小说的阅读与创作呢?
如果我们按照何、马的思路,或者说,按照瓦特关于西方十八世纪小说的兴起与女性读者之关系的考查,继续搜索资料,我们仍然会陷入同样的困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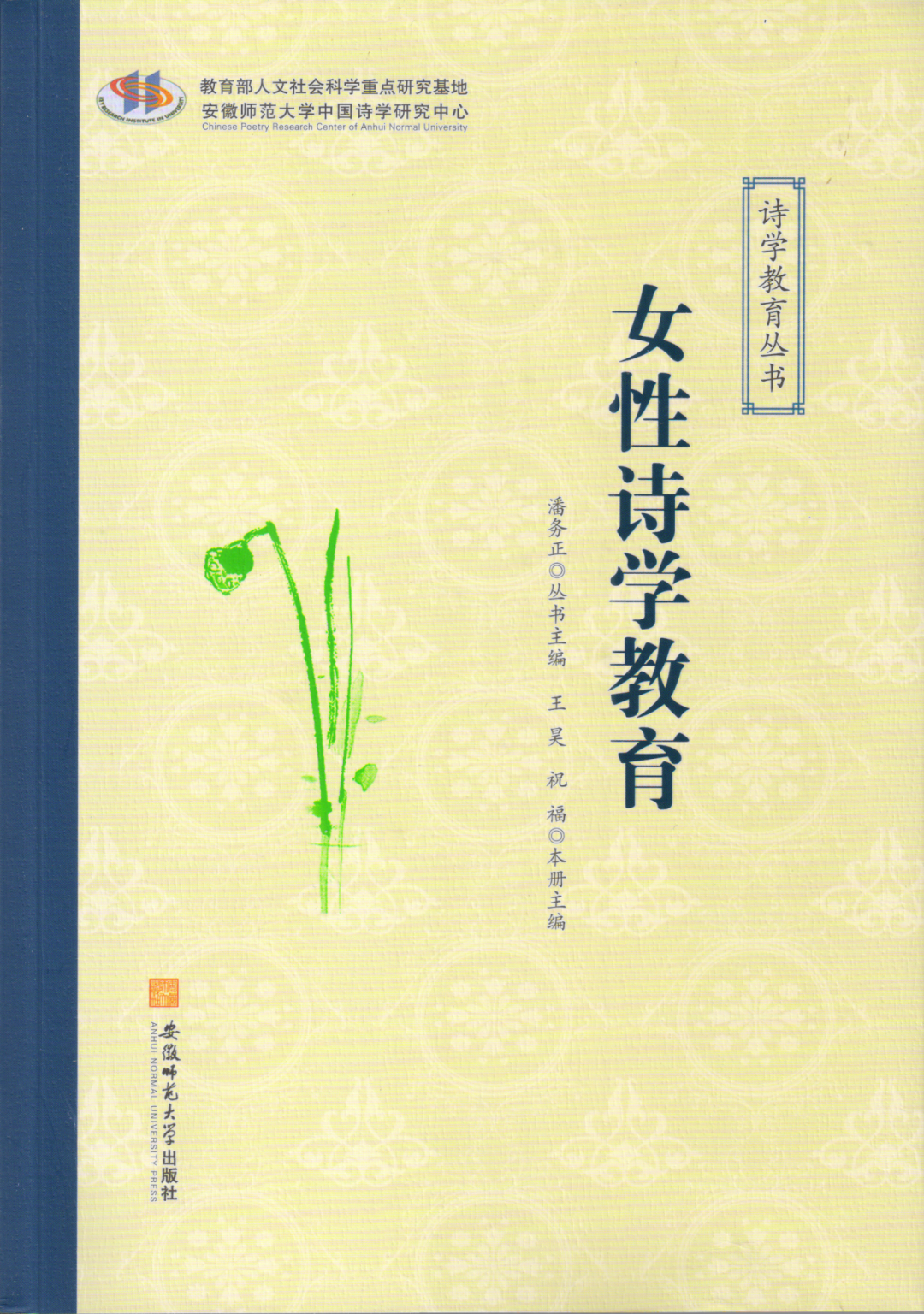
《女性诗学教育》,王昊、祝福主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
首先,以女性识字的普及程度而言,我们发现,自朱元璋以来,普及女性教育已成为明代突出的社会现象。事实上,从宫学(包括各级官学)到家学再到坊学、寺庙之学,等等,[4]其兴盛程度可能已远远超越了前代,甚至连清后期也远远不如。
例如,清代宫室并不重视女性教育,清末一个宫女曾经谈到宫女连太监都不如,太监还有机会学习,而宫女“绝对不许认字的,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5]
这一规矩与明太祖的旨令恰恰相反,如此来看,马兰安用1930年的统计数字来推测明代妇女的识字水平可能在百分之一左右,其实并不妥当。[6]
其二,何谷理特别指出,“由于手工生产的发展,出外工作的机会提供给了下层妇女新的自由。”[7]其实,自宋代以来下层妇女所参与的工作远远不止手工业。[8]
到了明代中叶,随着经济的发展,宋代的种种女性行业重新活跃起来,一应饮食、买卖、杂役、说唱伎艺中,都能看到女性奔波的身影,而手工业的发展进一步繁荣了这一社会现象。出外工作的自由,相应而来的是经济地位的提高,或者说一定的经济能力从整体上反过来提高了女性的自由度。
即使是不从事各种买卖劳作的女性,也日益走出家门,汇入各种娱乐与宗教活动中,以至于嘉靖间,海瑞要特地颁告“禁妇女买卖行走约”。[9]即使女性不能走出闺门,小说戏曲也无孔不入地进入了内宅深院,走入了女性的日常生活。
其三,女性走入小说的阅读,在瓦特来说,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她们的闲暇。不可否认,男主外,女主内,当男性奔波于外部世界时,尤其是士子将主要精力放置在经史举业上时,女性相比较有着更多的时间来自娱,这一点对具有经济能力的上层妇女来说更加明显。
田艺衡《留青日札》卷二一中就提到,“大家妇女”正是因为“骄奢之极,无以度日”,才招致一帮女先生,日夜说唱以为消遣的。

《留青日札》
需要提出的是,中国章回小说的兴起与西方近现代小说的兴起还有着很大的不同。关键就在于中国的小说与民间说话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使得很多女性在接受小说时,并不完全受识字水平、时间、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即使一些女性不直接阅读小说,甚至不识字,她们仍能通过听说、听唱、看画等各种形式来间接地接受小说,她们的喜好仍然会通过说话反映到小说中来。
再如,关于庶民能否阅读小说,瓦特还提到一个限定因素,即读者是否有独处的时间。
然而,这一点对明代小说的接受来说,有时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因为人们对小说戏曲的间接接受,常常都是一种集体性的行为,章回小说正是在这些集体行为中逐渐形成的。另外,从事说唱伎艺的女性,在小说阅读中扮演着一个特别的角色。
她们也许仅仅是靠口传身教来演说,也许也能够阅读一定的说话底本,甚至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她们既接受又传播,成为小说的一类独特的女性读者群。

《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
阅读小说既是一种消费,又是一种职业--这一独特的文化消费方式的存在,使明代女性的自由度、空闲与经济能力等等都有了一定的弹性,并与通俗文化联系起来。
女性正是从听、说、唱开始接触小说的,当她们具备一定的识字水平时,便进一步走向了小说的书面阅读。
由此来看,至明代中叶,无论是女性教育,还是女性的自由、闲暇与经济独立等等,有关事实可能都比何谷理与马兰安等研究者想象的要活跃;换言之,在中国的明代,当小说兴起时,参与小说阅读的女性,与西方小说的女性读者相比,很可能在数量上更多,所覆盖的阶层也更广。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可能,它并不能真正说明女性读者与章回小说兴起之间的关联。
(二)关于女性阅读史实的若干考察
这里不妨从具体的史料先来看一看女性阅读小说的真实情况,并进一步追索个中的意义。
在宋元说话场中,尽管不见记载,但可以推想,肯定也有出外买卖行走的女性听众在内;身为说书人的女性就更多了,如陆妙经、陆妙慧、史惠英、时小童母女、陈郎妇、胡仲彬妹、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陈小娘子等。
这些女性有的还出入于宫廷中,[10]以至于后人在提起宋元说话的兴起时,总免不了提到“宋陌头歌(盲)女”。如果那时确实有说唱底本的话,这些说书女性恐怕有不少人能够阅读。
不过,宋元时,这些女性说书者仍然是用男性话语来说唱的,她们实际与男性说书者没有什么区别。杨维祯笔下的朱桂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杨维祯全集校笺》
当思陵上太皇号,孝宗奉太皇寿,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也……此太平朝野极盛之际。今当此刀鸣镝语时,故家遗老或与退珰畸女监谈先朝故事,未尝不兴感陨泪也。
至正丙午春二月,予荡舟娭春,过濯渡。一姝淡妆素服,貌娴雅,呼长年舣棹,敛袵而前,称朱氏名桂英,家在钱唐,世为衣冠旧族,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因延致舟中,为予说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坐客倾耳耸听,知其腹笥有文史,无烟花脂粉。
予奇之曰:“使英遇思陵太平之朝,如张、宋、陈、陆、史辈,谈通典故,入登禁壶,岂久居瓦市间耶?曰忠曰孝,贯穿经史于稠人广众中,亦可以敦励薄俗,则吾徒号儒丈夫者,为不如已!”古称卢文进女为女学士,予于桂英亦云。[11]



朱女讲说的仍然是历史传奇,是忠是孝;她是女儿,却“无烟花脂粉”,而只有满腹文史;她是女中学士,连儒中丈夫也不如她。
当然,这种叙述来源于杨维桢这一男性的视角,未免带有他自身的情感色彩;但它已足以证明在元末,女性说话人实际与男性说话人没什么不同,她们只是没有性别的代言人,所谓三国五季是宋元时所有说话人(无论男性与女性)中都流行的题材,而女性的性别特色,不过成为男性文人伤今怀古、寄寓兴亡的象征。

清耕烟草堂《七修类稿》
元末王恽在词中说得更为明显,“由汉魏,到隋唐,谁教若辈管兴亡。百年总是逢场戏,拍板门锤未易当”;[12]甚至到明初,瞿佑在诗中还发出类似的感慨,“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13]
早在唐诗中,杜秋娘、琵琶女、白发宫人……作为唐代盛衰的见证已成为一种公典;这里的“宋陌头歌(盲)女”,在宋元明文人心中寄寓的不过是同一种感喟。
如果说朱桂英等人还主要是在瓦舍、勾栏演唱,她们主要运用的还是男性话语,听众也主要还是男性,但元末以来这一现象已开始发生转变。
首先是传播者、接受者与接受方式、接受地点逐渐有了改变。
元末,已有记载证明说书已转向了内宅,专为女性听众讲唱。如诗人王行,年轻时为药铺店员,白天里卖药,“迨晚,为主妪演说稗官词话,背诵至数十本”。[14]
也许,这里的女性还不怎么识字,她们主要是以“听”来接受小说,而且这一说与唱的对象主要还是普通的商贾人家,说唱者还是男性。
至明成化年间,从新近发现的《花关索记》等词话本来看,可能官宦人家的女性已经能够阅读词话本。正德年间,词话抄本的阅读在女性之间更为盛行。
据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一“小说戏文”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

《水东日记》
嘉靖万历间,在以琵琶演唱的瞽者中女性越来越多。
例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曾载:“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
稍晚,其子田艺衡在《留青日札》卷二一中道:“曰瞎先生者,乃双目瞽女,即宋陌头盲女之流。自幼学习小说、词曲,弹琵琶为生。多有美色,精伎艺,善笑谑,可动人者。大家妇女,骄奢之极,无以度日,必招致此辈,养之深院静室,昼夜狎集饮宴,称之曰先生。如杭之陆先生、高先生、周先生之类。”
在田汝成笔下,弹琵琶的瞽者还有男有女,到田艺衡时,瞎先生就已专指瞽女。
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冤狱”中还提到盗魁朱国臣曾蓄二瞽姬,教其弹词以博金钱,这里瞽女已近似家乐,而且主人还以此谋利,可见风气之盛。

《万历野获编》
说唱者以盲女为主,无疑扩大了听书者中女性的比例,从以上记载来看,盲女的说唱在上层妇女中,确实形成了比较热闹的局面。随着说唱在女性之间的兴盛,在书坊的作用下,专供女性阅读的唱本、话本也流行起来,还形成了十分兴盛的市场。
明赵美琦《酉阳杂俎序》载,“吴中廛市闹处,辄有书籍列入檐蔀下,谓之书摊子,所鬻者悉小说、门事、唱本之类。所谓门事,皆闺中儿女子所唱说也。”
由此可见,女性已成为通俗小说一类重要的读者群。
其次是说唱的内容有了改变。
走入闺阁的说唱,主要表演的是什么呢?两宋时,女性说话人与男性说话人一样,应该是讲史、小说、说经等诸家并说的。
到元末,则已逐渐以讲史为重。成化间,宣氏老太太所阅读的词话本,计讲史6种、公案8种、灵怪2种。
这里的讲史、灵怪、公案,一方面,大抵都是借古人、借妖异说话,与现实相距较远,与嘉靖元年到万历二十年间章回小说的题材内容正好相似;另一方面,所叙公案、讲史、灵怪同时突出了对家庭故事的关注。
正德时,叶盛说“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也是将历史传奇与家庭故事相提并论,但家庭故事已经占了比较重要的地位。
田汝成曾叙列过瞽女的说唱内容,“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这些故事今天都有话本流传,除济颠一事纯属“说经”一类,其余虽或与佛道类有关,却均为男女情爱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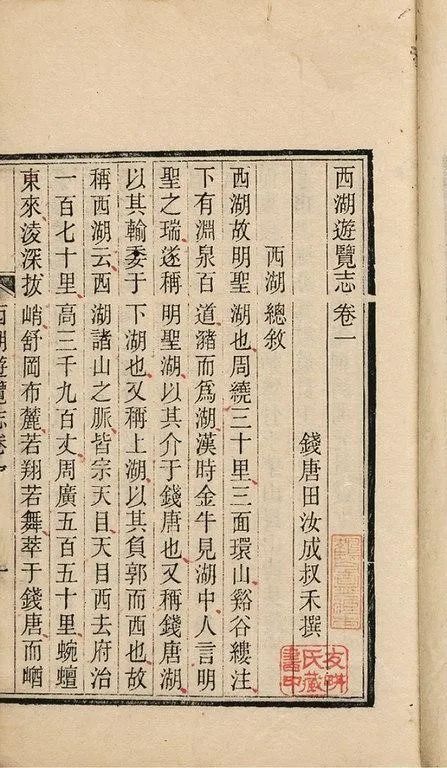
《西湖游览志》
稍后,田艺衡更指责盲女在上层妇女间的说唱,已是“淫词秽语,汗我闺耳,引动春心,多致败坏门风”。可见,嘉靖万历时,进入江南杭州闺阁的说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情语,甚至艳语。这从当时的《雍熙乐府》、《词林新声》以及《水浒传》、《金瓶梅》等曲集、小说也可以看出。
总之,自明初至明中叶,女性已逐渐成为说唱文学重要的接受群。相应地,在说唱中,情感与家庭的故事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然而,仅从这一点还很难真正说明女性与章回小说兴起之间的关联。
明代中叶所发生的社会变化仅此而已,我们并没有发现女性阅读、更无论创作章回小说的任何记载,直接从女性读者的出现来推导章回小说的兴起无疑陷入了一种困境,从而逼迫我们不得不换一条思路。


其实,有多少女性接受小说,如何接受,并不仅仅是社会文化消费景观自然的变迁,而与宋明以来,尤其是明中叶的教育俗世化运动密切相关。

《历代妇女著作考》
对明代女教的考察,绝不应仅仅考察女教的普及程度,并由此揣测女性识字水平的比例,以及推导章回小说女性读者的存在与否;而应更为深入地考察女教的具体内涵,以及不同时代女教普及者的真实动机及其实际效果,换言之,明代女教的兴起与变迁同样隐寓着一代士林精神的变迁。
如此,才能真正了解,女性读者(确切而言,应该是女教思想)是如何促进了章回小说的兴起,并进一步影响了其后来的变化。
(一)明初帝王以复古为号召,推行正统女教
关于女性教育,自古以来就有,不过将其扩大到庶民中,大约与朱熹颇有关系;但朱熹毕竟只是一个在野的理学家,普及女性教育,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思想,并付诸实践、进一步制度化,则始于明代。
早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就曾下诏命翰林学士朱升等“纂《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15]也就是说,《女诫》一书首先是为教化宫闱、以防后妃乱政而作的,因此,一开始也主要流播于宫廷与王室之间。
说起《女诫》(洪武三年成书)的修纂,不得不提到另外几部官方著作,如洪武二年为昭戒藩王而修的《昭鉴录》,洪武六年的《辨奸录》,洪武十三年废相后的《相鉴贤臣传》与《相鉴奸臣传》,洪武十九年颁赐文臣的《志戒录》,洪武二十一年训诫武臣的《武士训诫录》,洪武二十六年训导诸王及勋臣的《永鉴录》与《世臣总录》。[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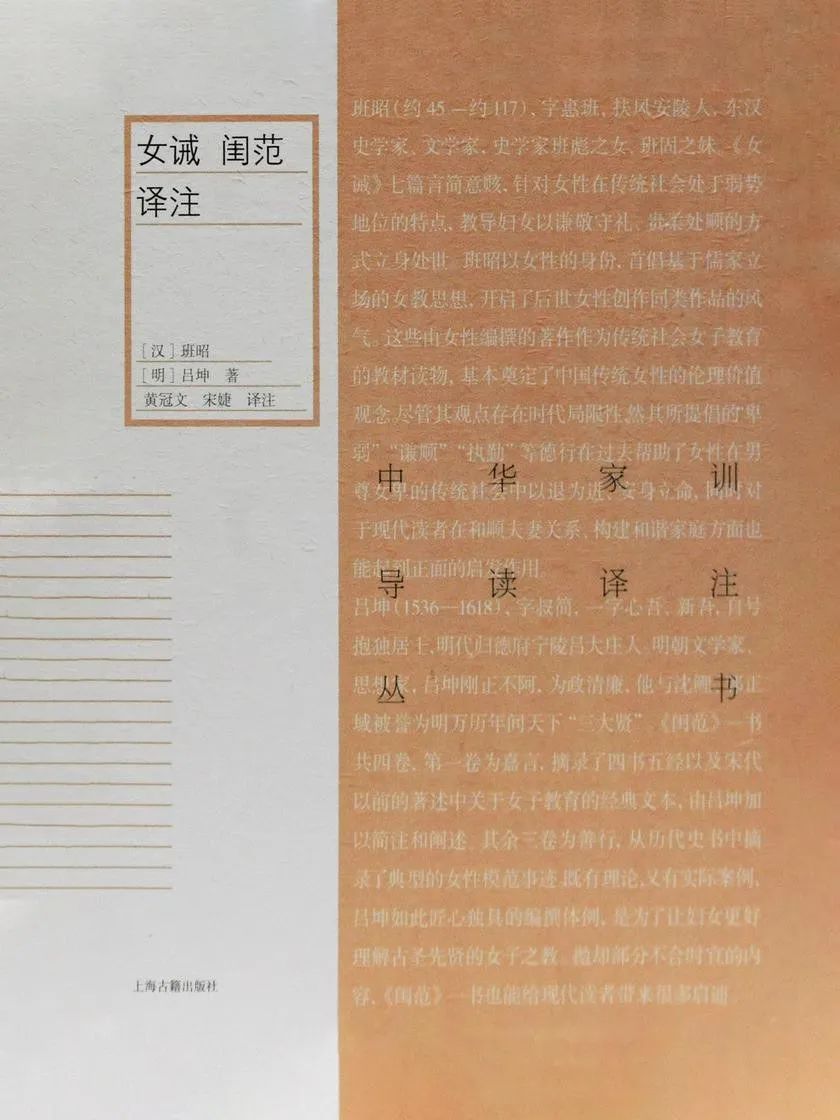
《女诫译注》
而从其修纂的次序看,以宫闱女教居首,次及藩王、宰相、文武群臣,无疑和传统儒学的“正始”观念以及《大学》修齐治平的观念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本人最重视的著作就是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因此《女诫》的修纂,可以说是明初政治中的关键一环。
永乐三年,仁孝文皇后徐氏明确提出,正是有慨于当时的“女教未有全书”,于是,托言高皇后旧训,撰为《内训》,“上以广高皇后立法之深心,下以成宫壸肃清之令范”,史誉“颇称详备,而尊姑以立言,尤得孝道之大者”。同时,又广采古代圣贤劝善惩恶之言,分类相从,凡二十篇,名为《劝善书》。[17]
这两种书最初也只是谕示皇太子与其他藩王,至永乐五年徐后辞世,明成祖乃正式刊行二书,颁赐天下,[18]并诏解缙等人辑录《古今列女传》三卷,一并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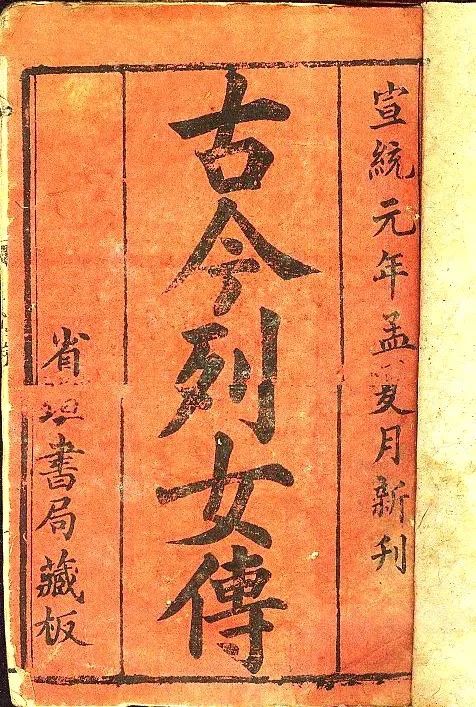
《古今列女传》
可以说,有明一代官方普及女教的思想,萌于洪武,始成于永乐,或者说,朱熹普及女教的思想经有明洪武、永乐二朝,正式被纳入明代的官方礼乐教化系统,这一过程与程朱理学在明初的官方化(其标志是永宣时官方新朱学的形成)一脉相承。
明初推行女教,不仅仅是集撰女教书籍,颁行天下;同时,还积极设帐授学,譬如,当时宫廷的女教已趋于制度化。
据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宫内教书,“选二十四衙门多读书、善楷书、有德行、无势力者任之……仍命秉笔一员提督之,所教宫女,读《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女训》、《女字经》、《女诫》、《内则》、《大学》、《中庸》、《论语》等书,学规最严,能通者升女秀才、升女史、升女官,正司六局掌印,凡圣母及后妃礼仪等事,则女秀才为引礼赞礼官也。”
尽管此书所载已是明末故事,但宣宗时曾强腐翰林编修程宗教书内廷;英宗时权庵王振原是教官出身,后来也“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可见宫内教书由来已久。[19]
由宫内教书已可以看出明代女教与女官制度的关联,不仅如此,明代女官制度与选秀制度的完善从根本上推动了女教的社会化与制度化。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便有诏宦官不得识字,而宫中诸凡文案事务俱由女官掌理;由此着手设立女官制度,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增损厘革,至洪武末年终于建立了一整套机构。
女官的设立古已有之,但要说到机构的独立、制度的完备、属员的众多,却很难与明洪武年间比。
同时,明以前朝廷所设立的女官与妃嫔往往界限不清,甚至二位一体,到明洪武时期不仅女官与妃嫔完全分开而且品秩较低,具有纯粹的职司意义,这无疑突出了对女官与女史职事能力的要求,同时也保证了女官的制度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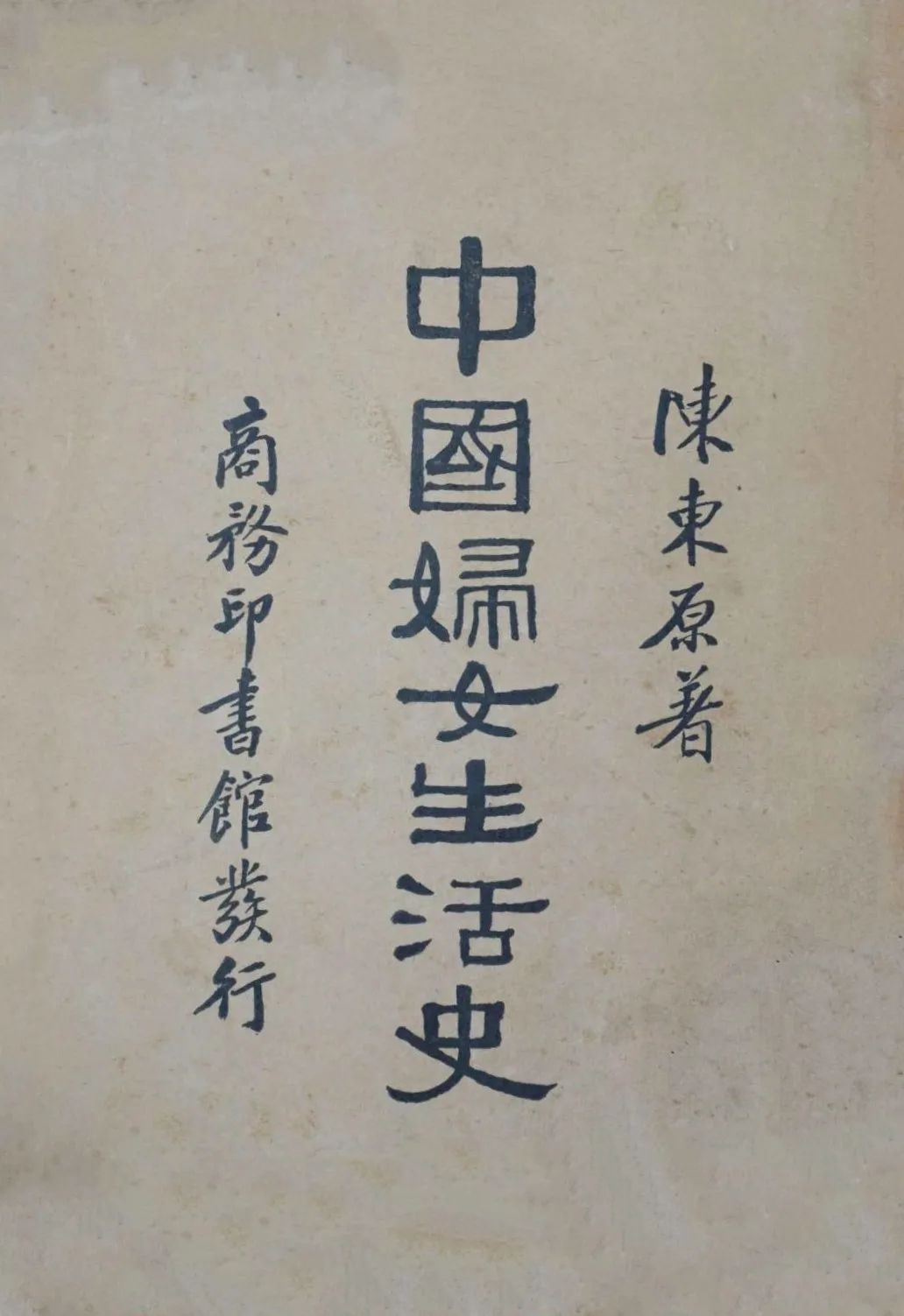
《中国妇女生活史》
同时,与女官制度相伴而定的是选秀制度。一应女史、女官以及妃嫔、宫女都选自于民间,一反历朝选女多在名门望族的传统。一应女官有品秩、有俸禄,任职数年后还可以回家,任听婚嫁。
女官制度建立于洪武,基本沿用于建文、永乐两朝;洪熙宣德以后,随着宦官势力的日益膨胀,女官职掌逐渐被宦官取代,女官制度也渐渐衰落。但终明一代,选设女官的事情并未彻底终结,而且女官、女秀才的地位一直很高。[20]
直到隆庆三年,朝廷还下诏选三百淑女补充宫官。宫廷对女性才德的重视,无疑对社会风尚是一种诱导;而且秀女选自于民间,职满后又可重返民间,这一循环进一步带动了民间对女性的教育。[21]
既然,我们说,明初官方女教不过是官方新朱学的一环,这样的一种教育,首先注重的是德而不是才,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而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官学与家学。
既以明代后宫而论,虽然也出现了不少有才华、能诗书的女子,如洪武时的女学士沈琼莲、江氏,宣德时的郭嫔(爱)、女官黄维德,成化时兴献王母邵贵妃、嘉靖时宫人张氏等,但总体上她们的文化修养并不特别突出。

《内训》
不过,与前代不同的是,有明女教明显体现出朱熹俗世化教育的思想,它的意义恰恰在于扩大了宫女妃嫔以及天下女性能读书识字者的范围。
不仅如此,这样一种女教在“正统”外衣下仍然隐藏着积极求变的意义。明成祖仁孝文皇后曾这样自述撰写《内训》的原因:“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岁而入小学,女子十年而听姆教,小学之书无传,晦庵朱子爰编辑成书,为小学之教者,始有所入。独女教未有全书,世惟取范晔《后汉书》、曹大家《女诫》为训,恒病其略,有所谓《女宪》、《女则》皆徒有其名耳。近世始有女教之书盛行,大要撮《曲礼》、《内则》之言,与《周南》、《召南》诗之小序及传记而为之者。仰惟我高皇后教训之言卓越往苒,足以垂法万世,吾耳熟而心藏之,乃于永乐二年冬,用述高皇后之教,以广之为《内训》二十篇,以教宫壸。”
仔细品味,这篇序言其实含有很大的挑衅意味。仁孝文皇后借这篇序,不仅表达了对传统教育忽略女性的不满,而且一笔抹倒历代女教之书,而以高皇后为女教第一人。
《内训》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女教思想视野非常开阔,这部书直接将女教与女子个人修身养性、国家稳定、王朝兴衰联系起来,所谓“纵观往古,国家兴废未有不由于妇之贤否”。[22]
女教在明代盛行,尤其是由女性来鼓吹,这首先说明了女性地位的提高。朱元璋与高皇后马氏从元末战乱起,患难与共;建国后,马氏以天下母自称,积极协助丈夫治理国家,朱元璋也以马氏为贤内助。
二人崛起于民间,身经离乱,深知女性对家庭、对国家的重要作用。经常被朱元璋挂在口中的“国乱思良相、家贫思贤妻”一语,正是元末明初现实的写照。[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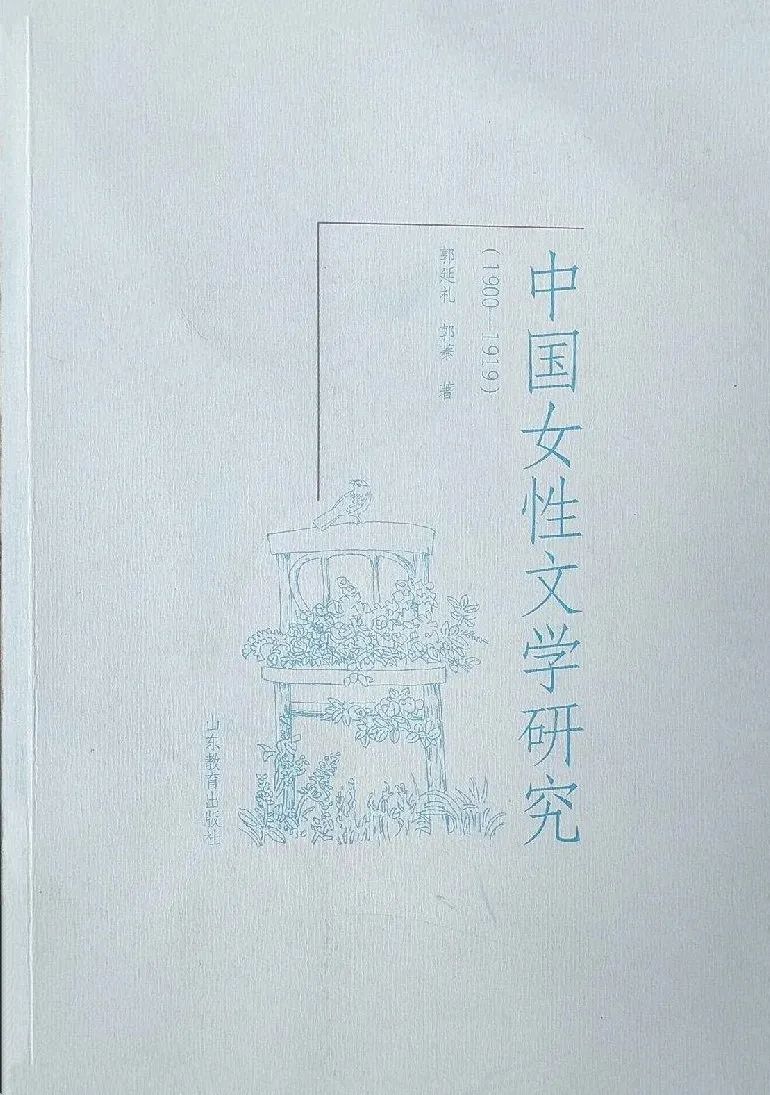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有明一代,对正统女教的重视,始终伴随着对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重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明代中叶尤为突出。[24]
或许正是因为起于布衣,朱元璋的一应政策几乎都体现了务实的倾向,因此,我们还应看到,明初帝王在推广正统女教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了小说戏曲的教化作用。明初律令中,惟独不禁“义夫节妇、孝子贤孙”一类的杂剧戏文;[25]朱元璋十分赞赏《琵琶记》,其实也是看重了这部戏对家庭伦理的鼓吹,而这一直就是女教的重要内容。
正统女教熏陶下的女性,以家庭为核心,自下而上地维护着整个社会秩序;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一旦事易时移,女教的普及无疑也成了滋生女性“自我意识”的温床。
(二)嘉靖万历初,官方女教积衰下士大夫女教思潮的复兴与裂变
朱元璋在一开始重建传统女学与女官制时,就带有一种浓厚的复古情结;这样,当理想的色彩逐渐剥落,现实逐渐浮现时,一向苦心经营的女学与女官制,在洪熙、宣德后便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衰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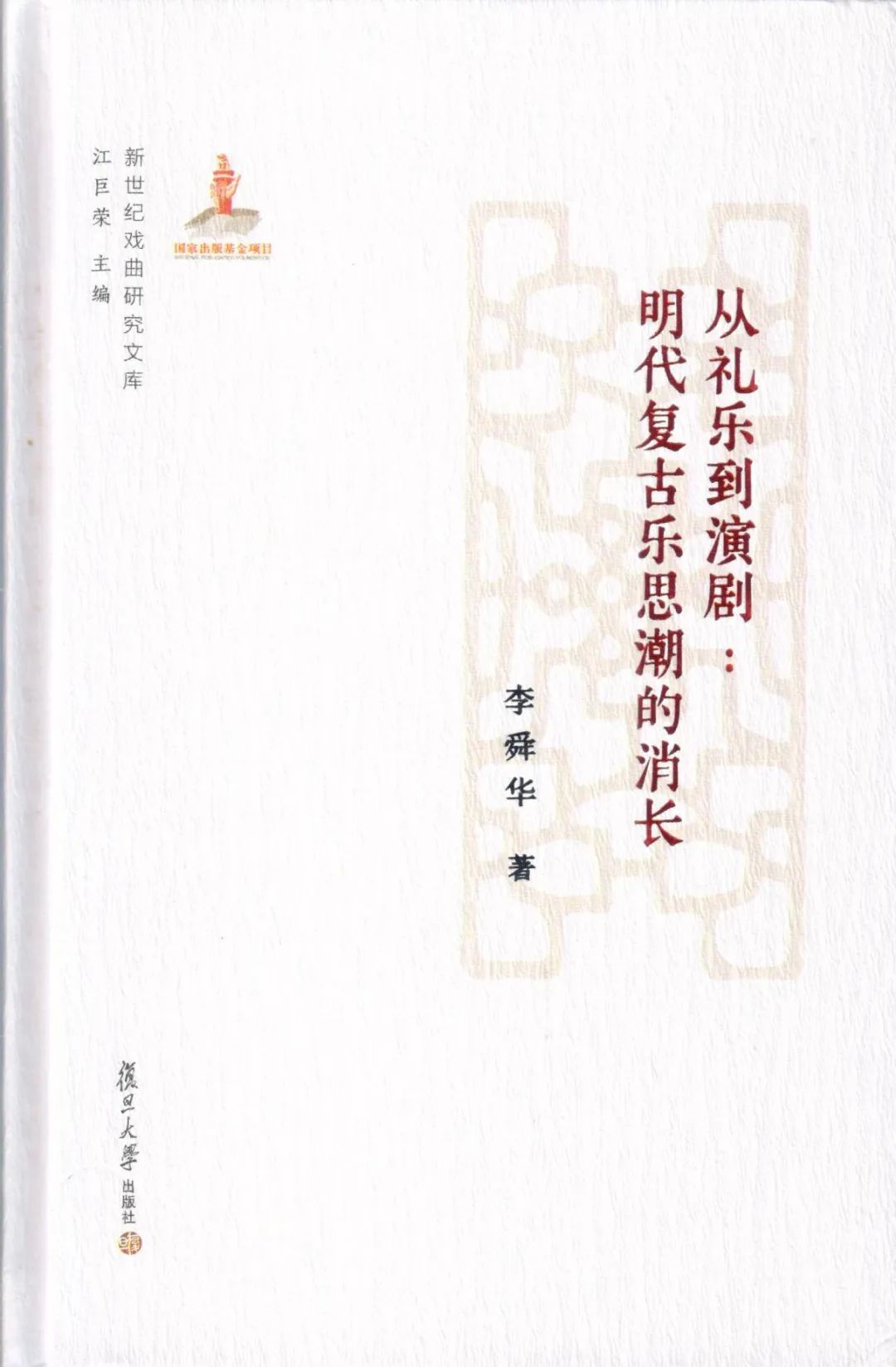
《从礼乐到演剧:明代复古乐思潮的消长》,李舜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版。
随着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解冻,小说戏曲渐次繁盛。明初朱元璋括天下乐籍入教坊,并特设官妓制度,后来宣德间榜禁官妓,于是缙绅间宴乐多用男优小唱,但正德以来,随着乐籍制度的衰落,原有禁令也在实际上流于空文,于是女乐与女伎日益繁兴,同时,勋贵、士绅、富商家庭还纷纷蓄养家乐,甚至调教婢妾,以为娱乐。
这一风尚同样波及了宫廷。与明初帝王积极控制小说戏曲不同,成化以来的各朝皇帝,大都沉湎于小说戏曲的娱戏之中,万历帝还特选近侍二百多人在玉熙宫学习弋阳、海盐、昆山诸腔戏文,又择《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词林摘艳》中词曲反复吟唱,等等。[26]可见,随着社会风尚的变迁,从宫廷到地方,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汇入小说戏曲的听说与表演之中。
官方女教久已式微,然而两百年来对女性教育的重视,却大大提高了女性的识字水平,并进一步为女性走向小说的阅读提供了一种可能;到嘉靖万历初,一方面是女性识字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社会风尚的变迁,这样,在女性教育中便逐渐出现一种与传统逆反的因素:
生闾阃内,惯听鄙俚之言;在富贵家,恣长骄奢之性。首满金珠,体遍縠罗,态学轻浮,语习儇巧,而口无良言,身无善行,舅姑妯娌不传贤孝之名,乡党亲戚但闻顽悍之恶,则不教之故。迺高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则邪教之流也。(《闺范》吕坤自序)




《闺范》
嘉靖万历年间的许多文人中,对当时的女性教育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焦虑。他们认为,这时女性的教育--无论是家学还是坊学,都偏离了儒家的伦理规范,以至于女性纷纷学诗、学唱,市场上充斥着说唱、词话,社会风气日益败坏。
马兰安在评述吕坤撰著《闺范》的动机时,就曾说道:“阅读能力的提高、书籍印刷的商业化、读者大众的扩大正威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权威性……也许这恰恰暗示了女性阅读已经扩展到令文人吃惊的程度,以至于他们试图扭转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 [27]
正是出于这种焦虑,嘉万间文人试图重建传统女教,引导妇女重返传统的女德。
嘉靖万历时的女教有两个特点,一是,鼓吹者主要为文人。明初以来的传统女教式微,由此也可以看出官方权力的失范。礼失而求诸野,明中叶文人,自觉担负起重建传统女教的责任,积极编撰女教读本,重新鼓吹传统女性教育,如王阳明、吕得胜、吕坤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二是,女教进一步走向通俗化。
例如,嘉靖时吕得胜《女小儿语》一书,专为女童作语,自然语言极为浅显;吕坤也是有感于“女训诸书,昔人备矣,多者难悉,晦者难明”,这才另撰《闺范》一书,并“绘之图像,其奇文奥义,则间为音释,又于每类之前,每传之后,各赞数言,以为激劝”[28]。

《女小儿语》
可见,二人都非常重视通俗读物的作用。实际上,不少文人,即使是正统文人,对女性介入通俗说唱都抱着许可甚至鼓励的态度。
例如,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主要考辨的是文言小说的源流与类别,对白话小说颇为冷淡;然而,同是此人,对其母嗜好话本小说不但没有异议,言语中还颇为欣赏,“宜人警颖殊绝,虽不谙笔砚,而诸史百家稗官小说下逮传奇词曲,属于耳,终身不忘”。[29]
原因是什么呢?对于文人自身,从儒家正统来说,重经史而轻小说;然而,对于女性,却以为小说正是教育女性、传播女德的最好工具。
由于话本小说文字粗浅,一般比较适合妇女儿童阅读;所以明中叶文人往往将种种通俗读物看作妇人女子的专有读物,一些好事者甚至把话本小说等看作“女通鉴”(叶盛语)。他们在不断地惊叹后,开始有意识地将小说戏曲纳入女性教育中,并加以引导。
从表面上来看,嘉靖万历间文人对女教的鼓吹与明初官方女教在观点上颇为相似,纳小说戏曲于女性教育之中也不过是官方女教通俗化的进一步发展而已;然而,文人自下而上,积极承担女教之责,这一行为本身即有着冲破原有官方女教桎梏的意义,于是在现实的影响下,有关女教的内涵遂迅速发生变化。
为什么如此说呢?不妨做进一步追溯。如前所述,明初官方女教正是当时官方(新)朱学的一环,后者的确立标志着明初君主集权的形成。
而官方女教在宣德以后的逐渐式微,原本就是士大夫地位上升的一种体现:一方面,帝王进一步放弃了礼乐天下的职责,小说戏曲在宫廷的大兴即是一个显证;另一方面,以王阳明为代表,文人士大夫的讲学运动遂在民间迅速开展,对女教的鼓吹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古代女教文献丛刊》
明世宗继位以后,为了重建君主权威及帝位继承的合法性,因此推行大礼议,更定祀典,于礼乐制度大肆更张。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女性地位的压制,其用意便是所谓重振夫纲。
譬如其生母蒋氏欲在宫中祭奠其父,世宗置儒家有关“夫妻齐体”的祖训于不顾,使其母尊奉丈夫为“尊辟”,而这也成了他欲更定祀典的第一个借口。[30]在这一背景下,作为议礼新贵的桂萼等人谄谀世宗、竞相推崇所谓女教便似乎不难索解了。
由此,因为议礼而引起的思想界的纷争也就自然在女教的问题上表现出来。嘉靖万历年间,关于女教发生了两起颇有意味的事件:
一是嘉靖九年明世宗颁章圣太后《女训》风波,一是万历二十六年郑贵妃序《闺范》风波。

《中国女性文学史》
这两起风波实质上是一场情理冲突在女教领域的展开。桂萼、郑氏等以复古守礼为标榜,极力鼓吹《女训》与《闺范》,这一行为无论就廷臣桂萼、还是宫廷后妃郑氏而言,其根本目的都不过沽名钓誉、以固帝宠而已,而因此掀起的种种争执都成了一场荒诞的戏剧,沈德潜便完全是用嘲讽的语气来评述这两件事情的。[31]由此可见,官方女教的光环至此已彻底被剥落。
而颇有影响力的《闺范》自身呢?它原本是吕坤民间实践的产物。这本书确实发挥了原有《女诫》、《女训》等的经典理论,但必须注意到这些原本也是朱熹女教的内容,因此,与其说《闺范》继承了官方女教的内核,毋宁说《闺范》试图重返久被遮蔽的朱学以规范日趋衰颓的世风,对官方女教的某种肯定亦不妨视为一种不得不如此的援引罢了。
实际上,较之于官方女教,吕坤的思想其实已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例如,同样以贤女贤妇贤母为闺范,吕氏在大谈“理”与“礼”时,却对女子应该守节、殉夫颇不以为然,认为“未嫁之女,死以殉夫,过矣”,过在“钟情过礼”。这恰恰说明,在吕氏心中,“情”与“礼”的概念已发生了变化。[32]
如果说吕氏还只是对“女德”有所突破;那么,另一些文人却开始对女德展开了强烈的攻击。
徐渭在《四声猿》中,分别书写了《雌木兰》、《女状元》两部短剧来称颂花木兰与黄春桃这一文一武两位女子的才能,这两部剧作都有明代实事为基础。
李贽在著作中,也一一列举过历朝历代有才有识之女,备加推崇,以为皆“男子不如也”。[33]这样一个异端之尤者李贽,万历初还有不少女弟子尊他为师,这也可以想见当时社会的风气。[34]

《李贽研究资料汇编》
谢肇淛更直接抨击了历代女教之书“只载早寡守志及临难捐躯者,其他一概不录”的作法,而主张“传列女者,节烈以外或以才智、或以文章稍足脍炙人口者咸著于篇,即鱼玄机、薛涛之徒也可传也,何况文姬乎”。[35]主张女性但有才学、虽身为妓人也可入“列女传”,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极具叛逆性的。
嘉靖元年到万历二十年间,一方面是,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女性介入说唱的阅读,而且出现了某种与传统相悖的趋势;另一方面,却是一些文人试图重新建构传统女教,但在现实的影响下,她们的女教实际上已逐渐突破传统的束缚,鼓吹性灵、崇尚才艺的思想日益发达。这时期的女教与女性阅读,同样呈现出一种复古蕴含着新变、新变蕴含着复古的光怪陆离的景象。
注释:
[1]《小说的兴起》,第42页。
[2] 例如,刘绍铭认为“在女读者的心目中,总希望看到一个男人除了侠骨以外,兼备柔肠”。《是侠客,还是瘟神--试论中国侠之形象》,收入联副三十年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典文学论》,台北:联合报社,1981年,第31页。
[3] Robert E. Hegel.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PP2-3. Anne E. Mclaren.Chinese Popular Culture and Ming Chantefables,PP67-72.
[4] 笔者暂且将市井中调教女儿书算琴棋歌舞等称作“坊学”,将宗教传播过程对女性的教育称为“寺庙之学”。
[5] 金易、沈义羚著《宫女谈往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6] Anne E Mclaren.,P68. 其实,我们不仅不能将女性识字率的增长视为直线型,还必需考虑到由于战乱等种种因素不同时期总人口数的波动;如此,用1930年的统计数字来推导明代前中期,无疑是不可行的。
[7] Robert E. Hegel,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P21.
[8] 早在宋代,女性所从事的行业,仅杂役一项,就有“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称”。[清]潘永因撰《宋稗类钞》卷
7“饮食·九”,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
[9] [明]海瑞《海瑞集》下篇四“书牍类”,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10] 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61-64、283-284页。
[11] 《东维子文集》卷6《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四部丛刊本。
[12] [元]王恽撰《秋涧集》卷76《鹧鸪引》十四《赠驭说髙季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郎瑛《七修类稿》卷22《辨证类·小说》。
[14]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5] 《明史》卷113《太祖孝慈高皇后传》。
[16] 洪武朝修书以戒天下,其例甚伙,可参明黄佐著《翰林记》卷一三“修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昭鉴录》、《相鉴贤臣传》与《相鉴奸臣传》,俱有洪武自序可考,收明姚士观等编校《明太祖文集》卷一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清]傅以渐等纂《御定内则衍义》卷1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据《明太宗实录》卷79载,永乐六年五月,日本遣使请赐仁孝皇后《劝善书》、《内训》二种,上命礼部各以百篇赐之。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19] [清]查继佐《罪惟录》《宦寺列传》,方福仁校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20]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 《宫闱》。
[21] 朱元璋制定选秀制度,从民间选取秀女,本来是为了杜绝女宠外戚之祸,但客观上应促进了民间的女性教育。参王云《明代女官制度探析》,《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
[22] 《内训·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详细论述并可参本书第六章第一、二节。
[24] 万历时谢肇淛在解释闽徽一带为何多妒妇时,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男子“赖妇操家秉也”。《五杂组》卷8《人部四》。
[25]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0《国初榜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26] 参见《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禁中演戏》条。
[27] Anne E. Mclaren,P72。
[28] 《闺范》吕坤庚寅(1590)自序,民国十八年己巳四月释印光石印本。
[29] 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91“先宜人状”,胡母死于万历十七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嘉靖更定祀典的根据在重振三纲,这一点邓志峰已经指出,参氏著《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第82-86页。
[31]《万历野获编》卷3“《颁行女训》。
[32] 参《闺范》卷2《烈女》之《前言》与《江文铸妻》、《杞梁之妻》诸条,其实,在吕氏对女性的评价上,更多地寄托了对自身(男性)的追求与感慨。
[33] 李贽《初潭集》卷2《才识》,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4] 李贽《焚书》卷4《杂述·观音问》中收有答复女弟子澹然、澄然、自信、明因的书札;并在卷4《杂述·豫约》中对女弟子梅澹然、善因深表推许。
[35]《五杂组》卷8《人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