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某一天,住在西安长乐西路安仁街21号楼里的邱会作,家里迎来了一位气色特别好的老爷子。
门一开,老头一眼瞅见邱会作,心里头立马热乎起来,激动得不行。
“咱俩以前见过没,你对我有没有印象啊?”

连着问了好几遍,把邱会作都给问懵了。
看到邱会作一脸困惑,来人又憋不住话,开始嘀咕起来:
你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但我是你在平津战役那会儿抓的俘虏。记得战役结束后,在咱们去收容所的路上,你跟我们说了句话,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它让我明白别灰心,只要肯努力,未来就有希望。
一说到这事儿,邱会作突然之间就明白了,心思又不由自主地跑老远去了。
老者悠悠讲述:他坐在那儿,慢慢地说着往事。从他口中流淌出的故事,就像陈年老酒,越品越有味。他的眼神里闪烁着回忆的光芒,每说一句话,都像是在打开一扇尘封的门,带我们走进那段遥远的时光。他说起年轻时的奋斗,脸上洋溢着自豪。那时候,日子虽然苦,但心中有梦,脚下有路,一股子拼劲让他走过了无数风风雨雨。讲到动情处,他的声音微微颤抖,仿佛在那一刻,他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老者还谈到了家庭的温馨,说到儿孙满堂的喜悦,他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那些平凡日子里的点点滴滴,在他看来,都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他说,家就是港湾,无论外面的世界多喧嚣,家里总有盏灯为他留着。就这样,他娓娓道来,我们静静地听。在他的讲述中,我们仿佛也经历了他的一生,感受到了那份岁月的沉淀和人生的智慧。老者的话语,就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我们的心房,也让我们对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我得知你现在处境挺不容易的,我这个人也没啥大道理,就想着把你以前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送给你。
两个老人家聊起了往昔的一大堆事情,让邱会作心里头感慨万千。要走的时候,老人家赠给他五盒蜂王浆。
邱会作心里头那个感激啊,除了说声谢谢,真不知道该咋表达了。
邱会作可能脑子里闪过好多以前的事儿,情绪一下子上头了,等心情平复点,却发现自个儿坐在椅子上,腿都使不上劲儿,站不起来了……
【一】
1981年9月12号,邱会作因为身体原因被允许外出看病,然后就被安排住到了西安长乐西路那边的安仁街,具体是21号楼。
在那个不一样的岁月里,邱会作犯下了不少错误,最后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等他到了晚年,生活安稳下来,经常会回想起以前革命打仗的那些日子。
肯定地说,在以前那些打仗的日子里,邱会作也是出过不少力的,他和身边的战友感情都很深厚。
邱会作在老年时候聊起过:
在长久的革命岁月里,我跟我的上司、同事、手下都建立了很铁的关系。被发配到西安后,来看望我的人络绎不绝。只要是以前的战友到西安,他们都会抽空到我住的地方来瞧瞧我。

1929年底,也就是12月份的时候,邱会作回到他的老家江西兴国县,加入了红军队伍。
江西兴国是个挺有名的革命地方,听说周总理以前说过这么一句话:
北京南京虽好,但比不上瑞金,说到国家,外国也比不上咱兴国的风采。
那时候,说起中央苏区在地方上的表现,兴国那是顶呱呱,排在最前头,瑞金紧跟其后,排在第二位。
邱会作跟林彪手下的黄永胜、李作鹏不一样,他的长处是在后勤方面。听说他在工农红军学校那会儿,就对数字和计算特别在行,中央军委觉得他这方面挺厉害,就专门让他去总供给部干活了。
遵义会议结束后,邱会作被调到了军委四局,担任三科的科长,那时候他还只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周恩来亲切地叫他“年轻科长”,在长征的路上,毛主席也曾和邱会作交谈过,跟他说过一些话。
我曾在你们家那个茶铺子里头喝过茶,晓得你爷爷、老爸、老妈都是村里管事的人,你和你哥俩都去当了红军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邱会作挑起了总后勤部的大梁,当上了部长。听说在六十年代那会儿,周总理在一次发言里还夸赞道:
邱会作是个铁了心跟党走的红军老将,他在后勤部长这个位置上干得相当漂亮,做得非常到位。要说起后勤工作,他算是历届里最顶尖的一个,这不光是我这么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也是这么评价的。
邱会作晚年时聊起周总理,感慨地说,就因为总理的一道指令,我才能多享70年的寿命。

1934年6月份,当时在军委管后勤的邱会作,收到了周恩来给他的任务:
你得去搞定一个超隐秘的任务。
就在第五次反围剿快顶不住的时候,邱会作突然接到个秘密指令,说让他去把几个兵工厂、做药的厂子和仓库给炸了。还有啊,那些搬不走的值钱东西,得赶紧就地卖了,反正就是不能留给敌人,宁愿毁掉也不能留。
这事儿得严格保密,万一传出去,很可能会影响到前线的军民,让他们的士气受到打击,对咱们的反围剿战斗非常不利。
周恩来还特地交代了一下:
处理兵工厂这事儿可能有点棘手,最好还是晚上动手。这是项绝密的行动,要是走漏了风声,军法严惩不贷。
那时候,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地调来了个警卫小组,跟我们一起干这活儿。在邱会作眼里,这些人说得好听点是来帮忙的,说得难听点就是来盯着我们的。在中央苏区,一提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大家都吓得脸色发白。为啥呢?因为那时候中央还是没能摆脱左倾那一套,长征前头还冤枉杀了不少好干部,像红五军团军团长季振同他们。
邱会作搞定任务大概一个月后,国家政治保卫局那边就开始琢磨了,说邱会作手里握着红军的好多重要秘密,怕他不老实,想把他给“永久封口”。

长征开始之前的那天傍晚,邱会作冷不丁就被抓了起来,紧接着就要被带去刑场。他当时拼命喊冤,但根本没人搭理。
好在关键时刻,周恩来、邓发还有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三个人骑着马赶了过来。他们瞅见被绑得结结实实的邱会作时,也都愣住了。
叶季壮是邱会作在物资部门的老大,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转头问站在旁边的周恩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周恩来没吭声,只是朝邓发使了个眼色。邓发也没开口,只是眨巴眨巴眼,意思是还照以前的规矩来。那会儿,周恩来瞅见邱会作眼里带着点祈求,想了想,转头对邓发说:
他年纪还小,就让叶季壮领他回去吧!
结果就是这样,邱会作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还好在半道上撞见了叶季壮,他拦了下来,周总理也亲自出面担保。要是事后才知道这事,再上报处理,那就全完了。后来,周恩来特地叮嘱邱会作,别把这次差点被处决的事情说出去,并且很有感触地告诉他:
你那时候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真的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多年过去后,邱会作心里始终对周总理充满深深的感谢。

以前打仗那会儿,邱会作也是出过不少力的,他的老领导、老战友们大多都对他评价挺好,尤其是东野那几位大头目,像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他们。
邱会作起初只是在后勤部门工作,后来到了东北,他就开始上前线了。
1947年夏天8月份,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摇身一变,成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八纵。那时候,黄永胜被提拔为司令员,邱会作呢,他既是副政委,还兼着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后来,他又接了刘道生的班,当上了政委。
八纵刚组建那会儿,新入伍的士兵占了大头,战斗力不算高。那时候,军事指挥上是由黄永胜挑大梁,他是个打仗的好手,经验丰富。至于政治思想工作,则是邱会作在把关。可没想到,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八纵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有了天翻地覆的进步。
有种说法是,邱会被任命为八纵政委那会儿,林彪特意点了他来主导军事方面的工作。
邱会作这人,勤奋肯干,又爱钻研学习,再加上他对人总是和和气气的,所以他能得到老领导、老朋友的认可,也就很正常了。
【二】
1992年,邱会作到了北京,他的老朋友段苏权不仅请他吃了顿饭,还多次开车到他家去看望他,问问他过得咋样,暖不暖和。
邱会作以前当过八纵的政委,那时候段苏权是八纵的司令员。他俩在那时候有过一些交往,关系挺不错的。
段苏权去八纵当上了司令员,他是接替了黄永胜的位置。这个安排是由冀察热辽分局的书记程子华提议的,背后还有段小故事呢。
到了1947年,华北的军队一直没能打开新局面。所以,中央在转移到陕北的时候,专门让朱老总和刘少奇组了个工作小组,他们得渡过黄河去华北帮忙指导。这样一来,华北的情况才慢慢稳定下来。但那时候,全国解放的大形势已经变得大不一样了。因为东北那边的情况,中央在战略上就想让华北的军队和东北那边配合起来一起打仗。

就这么个机会,原来晋察冀军区的冀热辽军区,就转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手里。等到八纵建起来以后,也是直接归东北民主联军管。
黄永胜当上八纵的司令后,作为带兵的将领,他的本事那是没话说的。不过呢,他身上也有不少毛病,这些事儿到现在也没谁能完全搞明白。有好多老战友都提到,黄永胜一门心思全在打仗上,别的事儿他都不插手。这事儿引起了冀察热辽分局的书记程子华的注意,后来他就让段苏权来接替黄永胜,当上了八纵的新司令。
这样一来,林彪又开始不高兴了。
段苏权当上八纵司令员没多久,就碰上了一连串突发情况,让他感觉束手束脚,挺为难的。
1948年9月份,东野那边定下了要打辽沈战役的主意。段苏权就接到了任务,带着八纵的3万多号人,往南直奔北宁线,打算把义县和锦州之间的路给断了。
9月16号晚上,段苏权接到了新任务,得去拿下锦州边上的机场。但奇怪的是,这道命令在参谋部那边耽误了整整四个小时,才辗转到了他手里。
接到任务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晚了,而且那时候段苏权还碰到个问题,锦州那附近有俩机场,近的那个已经没法用了,远的那个还得穿过9纵的地盘。因为要穿过自己人的部队,段苏权就发电报问该占哪个。结果这一问,可闹出笑话了,电话那边的刘亚楼一听就火了,直接训了他一句:
说起掌控机场,那肯定是得拿下能让飞机起飞的那种啊,要那些废弃的干啥用都没有!
段苏权这时恍然大悟,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战斗时机。

在辽沈战役那会儿,八纵可是立下了大功。他们不仅成功地把义县和锦州之间的联系给切断了,到了辽西会战的关键时刻,更是快马加鞭地奔到营口,把廖耀湘兵团想通过海上逃跑的路给堵得死死的。
后来论功行赏时,8纵的好多功绩都没被算上,反倒是他们的不足被过分强调了。
就拿攻打锦州那会儿来说,第八纵队比主力晚了6个小时才冲进城里。但其实呢,第八纵队战前的任务就是当配角,主要是给主力打掩护。他们战斗打得越激烈,主力部队的压力就越小。这样一来,第八纵队自然得比其他部队承受更多重担。
多年以后,到了2009年准备拍摄电影《建国大业》时,特地往里面加了两句新的对话。
毛主席询问:
十点半了,哪个部队还没攻进去呢?
周总理回应道:
“八纵这事儿,你都反复问了有五次了。”
1948年11月份,黄永胜被调回到了八纵,他当上了纵队的一把手,也就是司令员。
段苏权到这时候才明白,自己在部队里的名声已经不太好了,大家都说他“不擅长打仗,总是打败仗”。离开第八纵队后,他被调到东北军区,当上了作战处处长。没过多长时间,他的级别就恢复了,后来还当上了东北军区的副参谋长。
其实,段苏权在八纵那会儿,心里挺感谢和他一起搭档的邱会作。这事儿得从攻打锦州那会儿说起,小紫荆山那会儿没守住,多亏了邱会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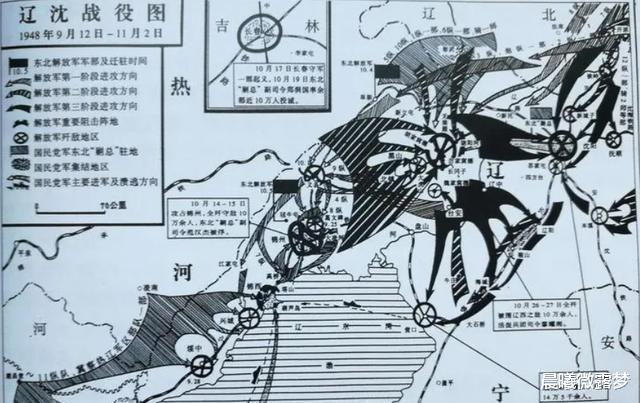
1948年10月份,八纵的23师68团打下了锦州边上的小紫荆山。这地方特别险峻,东总那边特别。可刚拿下没多久,在东总指挥的林彪就听到国民党在电台里使劲宣扬,说他们在小紫荆山那一带,给我军来了个重创。
林彪起初没当回事,以为国民党军在故弄玄虚,但后来他自个儿去查了查,发现这事儿还真不假。
那时候,东总直接给八纵打了个电话。段苏权和邱会作那会儿还对小紫荆山失守的事儿一无所知。后来好不容易跟68团联系上了,他们这才知道,原来事情是真的。68团的团长和政委也觉得这事儿挺严重,打算先把阵地夺回来,然后再往上报。
段苏权和邱会作到了68团后,这才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68团攻下小紫荆山阵地后,副团长韩枫看着大家又饿又累,就做了个决定,只留下于沛然的八连在阵地上守着,他自己则带着其他部队去吃饭了。可谁也没想到,韩枫他们刚下山,锦州的国民党军就杀了个回马枪,又是飞机又是大炮地猛攻。八连哪顶得住这样的火力,于沛然一看守不住了,也没跟上级请示,就自己下令撤了,结果整个阵地就这么丢了。
虽然那块地方已经收回来了,但事儿闹得挺大。邱会作一到部队,立马就把团长张峻岚、副团长韩枫、副政委杜绝、参谋长蒋勇,还有政治处副主任朱林尧给叫了过来,他们一起迅速处理了跟这事儿有关的那些人。
八纵成立这么久,从没碰上过这么丢脸的事儿,军纪得狠狠整顿!我这次是照着101的指示来的,就是来监督执行惩罚的。这回我先拿个人开刀,如果还有下次,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连马带人都得处理!

这件事邱会作记得特别清楚,以至于过了好多年,他跟小儿子聊起这事儿,还是忍不住感叹:
以前有个连长,跟了我快十年,结果因为一次搞砸了的事情,我一气之下就把他给处决了。
小儿子一听这话,立马眼睛睁得溜圆:
就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就要了命,这也太狠了点吧。
“战争真是太狠了!”邱会作不由得感叹起来。
段苏权和邱会作虽然一起共事不到一年,但合作得还算挺好。他们领导的8纵,进步真的是有目共睹,就连林彪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听说段苏权能从作战处处长重回原来的级别,不光是因为罗荣桓帮他说了好话,林彪也点头答应了。他还私下里跟一个很信任的手下说过这事儿:
苏权这人挺实在的,我并不是想惩罚他,我是想整顿冀察热辽这块地方。

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里,段苏权也碰到了麻烦,主要就是因为他接手了黄永胜八纵司令员的位子。不过还好,黄永胜在这事上帮段苏权说了好话,让他躲过了一劫。九大会议过后,又有人想对段苏权动手,这时候邱会作出面讲了句话:
在九大的时候,咱们八纵可是出了不少人才,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就有10个呢。
邱会作话里有话,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三】
邱会作1992年来到北京后,不少老朋友都来看望他。其中,老战友段苏权多次上门拜访,还拉着他一起去吃饭。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张震也特意在国防大学安排了一顿饭局招待他。

张震在1975年的时候,当上了总后勤部的副部长,后来又在1978年升为了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曾担任过这个部长职位。为了这次简单的聚餐,张震特意从自个儿家里带了一瓶茅台酒过来。
咱们年纪都不小了,喝一瓶酒就足够了。
挺有意思的是,张震跟管理人员讲了这样一句话:
我约了我的老同学出去搓了一顿。
简单来说,邱会作被一句话整懵了,心想他俩啥时候变成老同学了?后来张震特地来解释清楚这事儿。
原文大概说的是:“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但这些都是成长的机会。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失败就放弃尝试。面对问题,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积极寻找解决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进步,变得更加强大。记住,每一次的挫折都是一次宝贵的学习经历,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和智慧。”“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些坎儿,但这些其实都是让我们变得更厉害的好机会。别怕失败,一失败就退缩那可不行。碰到问题,咱们得挺身而出,想办法去解决它。只有这样,咱们才能一步步往前走,变得越来越牛。别忘了,每次栽跟头都是一次学习的好时机,它能让我们变得更坚强、更聪明。”
邱会作这时才突然明白过来。
说起来,张震和邱会作早就认识。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张震就成了新四军第四师的参谋长,同时还管着淮北军区的参谋长工作,邱会作则是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的政委,另外还负责豫皖苏边区的财政委员会。
吃饭时候,他俩边喝酒边聊天,说的都是以前打仗时候的那些事情。
邱会作记得很清楚,张震在饭桌上好几次提起了他老婆胡敏的政策是不是真的落到了实处。
胡敏也是个老资格的革命者,原本是名军医。在解放战争那会儿,她救过好多伤员,对我军的医疗卫生建设可是有大功劳的。但可惜啊,因为和叶群有点关系,胡敏也遭了殃,被发配到陕西农场去劳动改造了。

1981年,邱会作因为身体原因获准外出治疗,随后他就跟老婆胡敏一块儿搬到了陕西,在西安市郊的一栋普通房子里安顿下来。
张震很反感“一人有罪,全家遭殃”的做法,所以他特别留心胡敏那边政策执行得咋样。
有了好多老战友的鼎力支持,胡敏重新当上了军人,现在是师级干部。
1992年那会儿,邱会作搬进了省委的退休干部休养所,日子比起以前可是滋润了不少。
2001年快结束时,邱会作生了重病。在张震等几位老朋友的关心下,他被安排到北京协和医院去接受治疗。
2002年7月18号,邱会作老人在北京协和医院安静地离开了我们,那时候他89岁。
邱会作晚年过得挺平静舒坦。时不时就有以前的老战友,还有他们的孩子来找他聊聊天。有的是特意来看望他,有的则是工作出差顺道过来。就算有的人一开始不知道他家在哪儿,也会想法子打听清楚,一定要来见见他。
邱会作一直把这些老战友的情分深深记在心里头。

邱会作搬进了省委的干休所,所里还特地给他和老伴胡敏安排了个去延安的旅行。他们俩到了延安,在半山腰找到了以前住过的那个窑洞。窑洞里头的东西还是老样子,可他们俩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年轻人了。瞅瞅延安的风景,邱会作心里头一酸,眼泪就下来了。他跟胡敏说:
咱们投身革命这条路,走得没错。我来自江西,你来自陕西,要不是革命,咱俩哪有机会碰面呢?咱们一起闹革命,一起经历风风雨雨,这辈子都为这事儿豁出去了,有这份情谊就足够了。什么光荣啊耻辱啊,都别往心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