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即:不再仅仅从文本的角度来审视古代散文,而是将目光深入到文本生成所伴随的行为方式与所处的言说场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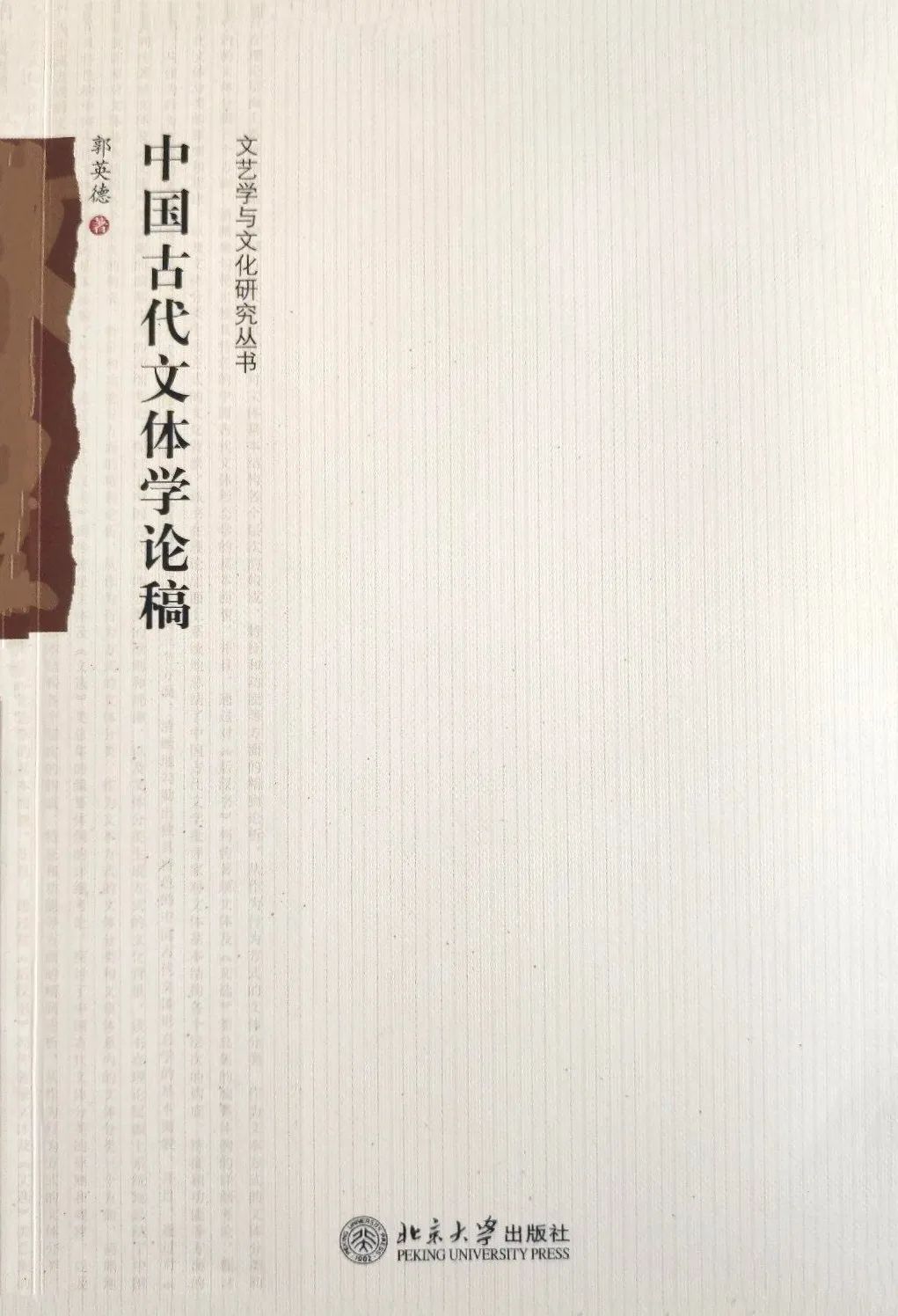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
郭英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就曾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1]29
这无疑为更加清晰深刻地研究散文文本的生成、文体的分类、文章的风格等问题开辟了一条新路。
事实上,在古代文言小说的研究中,论者已多多少少关注到了小说文本与言说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就认为征异话奇是唐代士大夫打发闲暇时光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征异话奇这一行为,也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传奇小说创作的根本动力。[2]151-152
陈才训也在《文人雅集与文言小说的创作及发展规律》一文中深入地探讨了文言小说与文人雅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认为文人雅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言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规律。[3]122
不仅文言小说的写作和文人雅集宴谈有关,中国古代的笔记也和古人的谈话有着密切的联系,严杰在《唐五代笔记考论》中就曾专设一节对士大夫相聚闲谈的场合和笔记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4]28-32
笔者在《明万历笔记与谈话之关系说略》一文中也曾将谈话与笔记之间的关系区分为以下四种:“谈话记录作为笔记成书的基本方式”“口述传闻作为笔记的一种信息来源”“作者在与友人谈话不得的情况下‘以笔代谈’”“笔记著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备谈或者助谈”[5]161。
但回顾以往的研究,仍有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得到学者的关注,比如说:既然笔记的生成和谈话密切相关,那么古人的谈话场合到底有哪几种?在这些谈话场合中,谈者的身份与相互关系是怎样的?谈话的形式、谈话的风格、谈话的特点又如何?这些谈话的行为到底怎样具体作用到笔记的文本,最终形成截然不同的文体风貌的?

《明代笔记小说大观》
本文拟以明万历时期的笔记著作为例,对“谈录类”笔记所诞生的谈话场合加以细致区分,以期对上述问题加以回应。[1]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笔者发现明万历笔记所涉及的谈话场合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家庭私谈、师友聚谈、客谈、社谈。

家庭私谈,是指谈话在家庭范围内进行,谈者与谈者之间以血缘或姻亲关系为纽带而产生的信息交流。谈者彼此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他们在谈话时的地位与身份。
在家庭私谈中,固然有诙谐嘲谑之情形,然而形诸记录的却以知识传授、道德训诫等内容居多。而谈者与谈者之间的关系,以父子为尤多,如陈第(1541—1617)的《谬言》、陈继儒(1558—1639)的《枕谭》,一般都采取父亲口授、儿子笔录的形式而写成。

陈第塑像
在父子谈话的过程中,由于二者本身具有着一定的伦理等级关系,父亲多采取一种讲授或者训诫的形式对其子进行教育,儿子虽然也有对于话题的引导,但更多仍停留在对其父所言内容的忠实记录上,由此形成的著作颇有古代语录箴言之风。
不妨以具体作品为例:署名陈第的《谬言》是一部典型的家庭私谈类笔记。该书虽题陈第之名,但在成书过程中,却有其子陈祖念的不少功劳。
此书著于陈第晚年抱病郊居之时,当时他的长子陈祖念日夜侍奉。在此期间,祖念读书凡有所疑问,则请其父“以意剖之”,为了备遗忘、资观省,他将父亲的回答与论说以片纸书之,历时两年,形成了《谬言》一书。[6]304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二人在成书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分工:陈第的作用主要在于答疑解惑,他的答语形成了《谬言》论说部分的主体;而陈祖念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发问——对回答的内容加以引导,另一方面则在于选择与记录,因为记什么、不记什么,事实上还是记录者根据自身的需要最终决定的。正因为这部笔记诞生在家庭私谈的场合中,《谬言》也打上了这一谈话场合的鲜明烙印:
首先,从记录内容上讲,书中大多数条目都带有着浓厚的学术色彩。
《谬言》一书共分八篇,分别为“论学”“论圣”“论经”“论性”“论政”“诗文”“诸子”“论兵”,可以说著作的重心仍是放在性理儒学上的,此外还涉及到兵学、诗文等内容。
这些分类立目其实和陈第本人的知识背景有关:陈第少时即博览群书,又颇喜谈兵;晚年更加潜心著述,学通五经,尤长《诗》《易》;而他与俞大猷(1503—1579)、戚继光(1528—1588)等名将也有着密切的交往,还有过出守边关的经历,因此“论兵”正是他长期用兵心得的口述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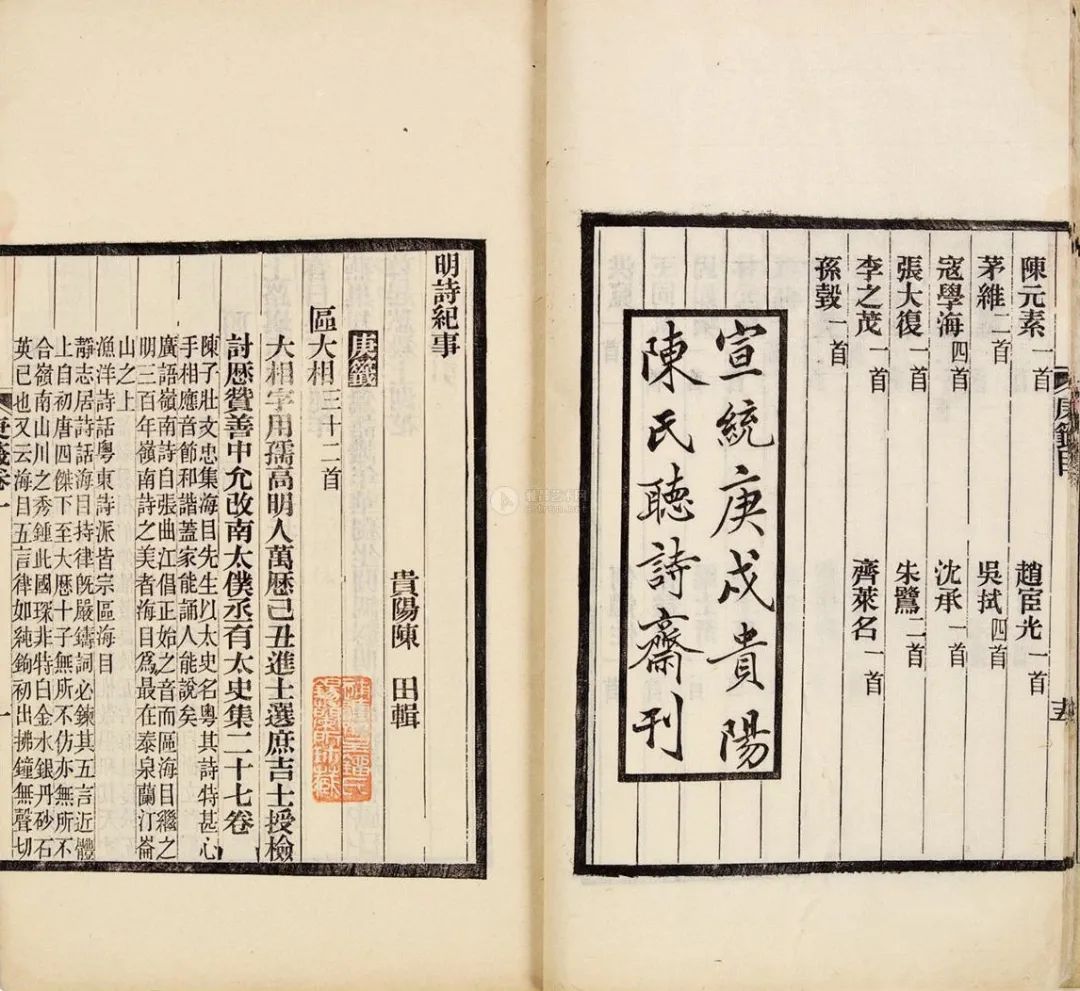
《明诗纪事》
除此之外,陈第的诗文也有一定影响:陈田(1850—1922)在《明诗纪事》中说:“季立诗,抒写性情,不拘一格,时有警动之作” [7]2069。而陈祖念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其父的学术传统,对于《易》经造诣尤深,其为学务崇实学,论文有“根极理要”的特点。
在了解二者生平的基础上,再来回顾《谬言》的分篇立目,不难发现,在《谬言》形诸记录前,父子二人的谈话内容,正是围绕他们的兴趣爱好与知识背景而展开的。
其次,二人的谈话形式也影响到了条目的书写形式。
陈第在《谬言》序中谈及二者的谈话形式:“每有疑问,则以意剖之。”[6]304可见,二者间主要是以一种问答的形式进行谈话的,而这一形式也有利于家庭私谈中答疑解惑目的的最终达成。通观《谬言》一书的记录格式,大多是以“问曰”“问”“或问”“或曰”等字起首,引出一个问题,然后再以“曰”字引出陈第对于此问题的见解与论说,这种文本形式不能不说与父子之间一问一答的谈话方式密切相关。

《屈宋古音义》
最后,由于在家庭私谈中,父亲往往是作为一个长辈对其子进行谆谆教诲的,因此谈话的口吻尤显语重心长。部分条目在行文之间,带有《论语》之风,如谈毁誉:“问曰:‘闻誉而不喜,闻谤而不怒,君子乎?’曰:‘我未之能行也,必也闻誉而惧,惧则副实;闻谤而思,思则寡过。’”[6]305-306更有一些条目本身就具备着较强的家训性质。如其言:
尝戒家人曰:“汝能卑人而使人尊己,轻人而使人重己,毁人而使人誉己乎?”曰:“不能。”“然则能尊人而使人尊己,重人而使人重己,誉人而使人誉己乎?”曰:“能。”曰:“然则卑人所以自卑也,轻人所以自轻也,毁人所以自毁也。汝戒之矣。”[6]306
在这段问答中,陈第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待人接物要多尊重、少轻慢,循循善诱,最终阐明了“卑人所以自卑也,轻人所以自轻也,毁人所以自毁也”的道理,并对家人进行训诫,这正体现出家庭私谈这一谈话场合赋予笔记文本的风格特征。

在这类谈话场合中,谈者与谈者之间或有师承关系,或因志于学问道德而形成一个群体,所谈多为儒家经典、子史杂学、嘉言懿行之类,其目的乃是通过聚谈取长补短,促成彼此学问道德的不断进益。谈学的形式既有讲论语录,也有对问辨难。风格较为正式严肃,没有太多谈笑之言。

《明代笔记小说》
明万历年间,对师友聚谈的内容加以记录最终形成的笔记有吴炯(1589进士)的《丛语》。吴炯自言垂髫时读宋代理学家的著作,就对孔孟圣学心向往焉,其后虽然饥寒奔走,但“一点初志未尝昧也”,唯独苦于没有师友同道相互发明。
直到万历庚寅(1590)之后,因为仕宦的缘故“浪游武林”,才与缙绅士大夫有较多的聚会讨论。[8]560
与会之人不乏当时晚明文坛、政坛的一些名流,如顾宪成(1550—1612)、邹元标(1551—1624)、钱大复(1579举人)、姜云龙(1597举人)等等,而顾宪成、邹元标正是后来东林讲学的中流砥柱。
吴炯在谈话时就已经有一定的著述意识,在和其他文人讨论时,他将自身所发表的见解加以札记整理,由此形成了《丛语》一书。
起初并无门类,后由其门人分为“理”“气”“性”“心”“道”“德”“仁”“学”“处世”“经世”“文章”诸门,其主要意图仍在阐发“洙泗伊洛”之旨,其门人何汝学就曾说此书“阐发幽微,剖析阃奥,洙泗伊洛之旨,昭如日星。” [8]561可见此书正是他“一点初志”的重新光明。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九〇册
书中许多条目,往往会点明聚会的时间、地点,与会者所提的问题,同道的反应与意见等,如该书卷3中就有这样一条内容:
庚戌三月会于阳羡明道书院,潘文学问:“夫子论仁,告子贡曰:事贤、友仁,曰:立人、达人,何其言之多歧也?”吴生曰:“事贤、友仁,收拾归来,立人、达人,推广出去。”又问:“事贤、友仁,则彼不事不友者俱立达之,念何在?”曰:“夫子有云:‘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不事不友者,因而感发,各事贤、友仁岂非立人、达人之意?”又问:“告樊迟曰:‘爱人’,又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何谓也?”曰:“天地之仁,不翕聚则不能发散;君子之仁,不忠敬则不能推爱,他日告仲弓,主敬行恕,其意亦如此。” [8]587-588
这则文本正展示出鲜明的谈学特征:师友谈学之时,一人提出疑问,另一人抒发己见作为回应,彼此探讨切磋;观点若有冲突时,亦可以彼此进行一定的争论与辨难,直到将疑问彻底探讨清楚。
这一形式的条目在《丛语》中并非孤例,卷7的“戊申正月前一日会于姜之北园”“泾阳先生问春王正月之义”、卷8的“钱肇阳讲食无求饱章”“周野人问博文约礼弗畔之义”等条目,都显示出几乎相同的文本模式,这一文本体制的形成不能不说和师友谈学这一谈话场合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在讨论的过程中,众人的目的在于探讨问题、阐发义理,所以仅仅将语言视作一种达意的工具,不甚讲究文采辞藻,因此谈学类笔记的语言大多较为质朴,并有着一定的口语化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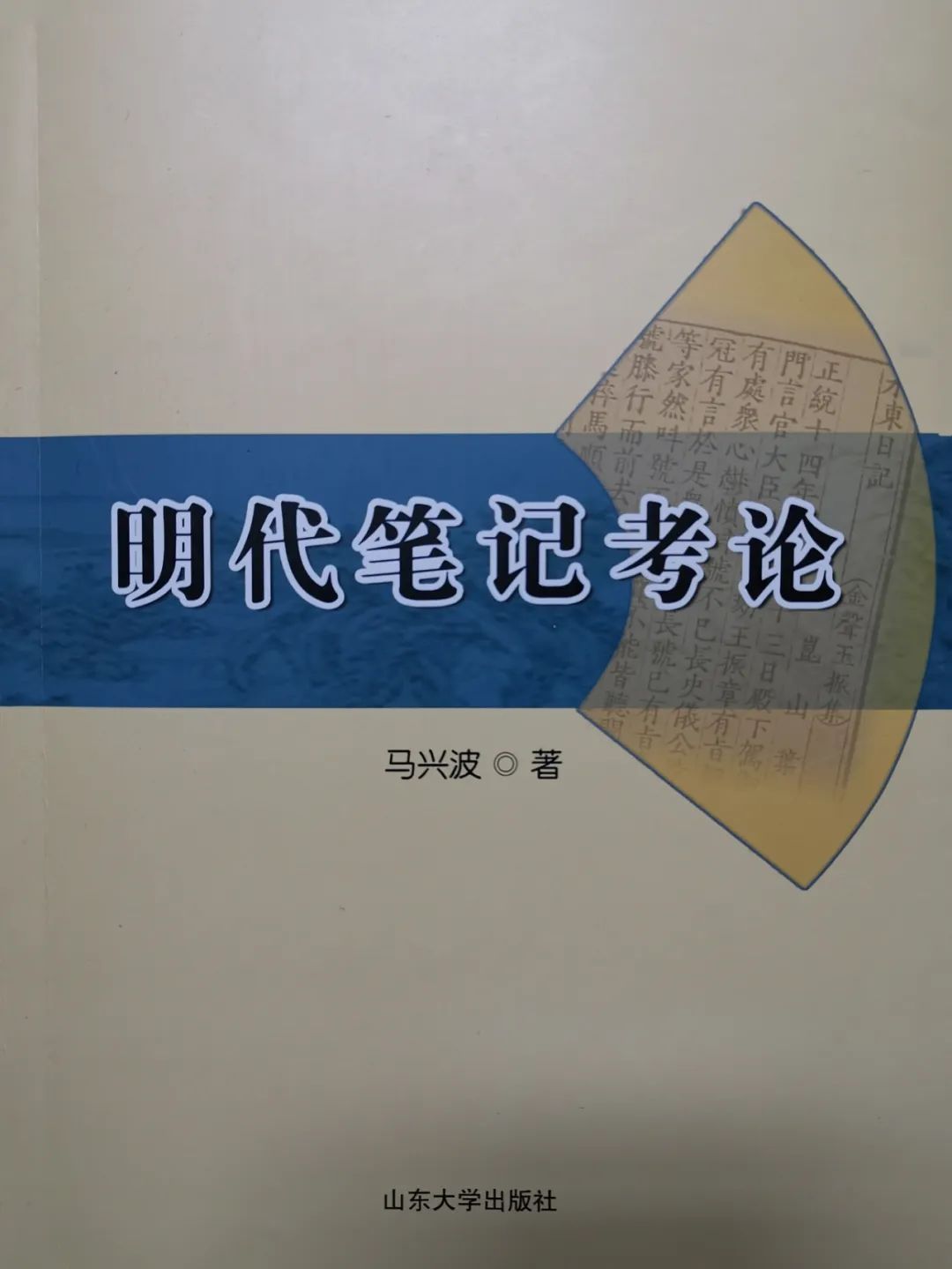
《明代笔记考论》,马兴波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
除了传统的儒学话题,晚明人治学亦有讲求博学兼通者,子史杂学、稗官杂说也常常成为师友谈学的重要内容。二者虽同为谈学,但所延续的文化传统却有很大差异:前者更多延续了古代的经学传统,而后者则更多具备着子部杂家的性质。
王肯堂(1549—1613)就曾提及他的师门之谈:他在作庶吉士时,馆师韩世能(1528—1598)常邀他入火房剧谈,谈论的内容“自世务外,于星历太乙壬遁之学无所不究”[9]45。
韩世能还叹惜王肯堂未能遇见赵文肃:“文肃公为馆师时,日孜孜为余辈苦口,如子所谈者无所不谈。”[9]45文肃公指曾做过明朝礼部尚书的“蜀中四大家”之一——赵贞吉(1507—1576)。
根据韩世能的回忆,赵甚至以《楞严经》课庶吉士,张居正(1525—1582)得知后摇头说:“也太奇。”而赵则言:“诸君少者几三十岁,长者逾四十矣。人寿几何?不以此时奇,更待何时耶?”[9]45从中不难看出其人无所不包的治学态度与时不我待的为学紧迫感。

《郁冈斋笔麈》
而师门之谈话,不仅有知识的传承,更有为学方法与治学态度的延续。王肯堂在《郁冈斋笔麈》中,天文历法、方舆形胜、训诂考据、巫医算术、三教九流,真可谓无所不究、无所不谈,这不能不说和韩世能的为学风格有着一定传承关系。
谈子史杂学而成书的笔记,还有江应晓的《对问编》一书。该书名为“对问”,正因为它是作者对客人疑难问题回答内容的一个记录汇编。作者在自序中开篇就说:“对问编何?对客问也。既答矣,编何为哉?志咎也。”[10]4所谓“志咎”,是指将往日的谈论记录下来,观其谬误以供日后反省反思。
“对问”的谈话方式在子史杂学类的谈话中较为常用,不仅是因为“对问”是一种有目的地摄取自身所需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因为“对问”也是古人检验一位学者是否博识的直接方式。
这种方式与六朝时征事、策事的文化活动有一定关联,故《对问编》之风格又与《谬言》《丛语》有别:《对问编》中的答客问往往并不局限于问题本身,而是旁征博引、触类旁通,凡与之相关的内容材料皆如江河流贯、喷涌而出,显得气势磅礴。
如江应晓形容自己的对问:“间一扣之辄聒聒不自休”,“若荆卿饮屠狗击筑辈于燕都中,歌哭自若,目无市人。”[10]4另一位序作者毕懋康(1589进士)也说他剖析疑义“驰辩如涛波,摛藻如春华”,令人“虩虩然惊,规规然自失也。”[10]3
这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谈话风格,也使得《对问编》中的文本带有一定策士论辩的色彩。

《对问编》

相较于以上两种场合,客谈的情形明显更为复杂。客谈是指古人以拜访作客为形式而进行的交流与谈话。“客”的身份往往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为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都可以以“客”的身份出现在与主人的交谈中。
客谈中谈者与谈者、谈者与记录者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多元:或为邻里、或为同僚、或为友人;谈话的时间与形式也往往自由不拘,十分灵活;谈话的氛围则比较轻松愉悦。可以说,客谈是“谈录类”笔记诞生过程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谈话场合。
客谈在万历时期的兴盛和当时文人丰富的家居生活不无关联。从相关文献来看,晚明文人士大夫对于居住环境的设计,常会将友人宾客的到访考量在内:茅坤在《皆可园记》中就曾谈及时人的居处设计:“左则宾客数过,或啸或歌,投壶博奕,饮酒无算,欢然适也,曰可游;右则客且忘归或枕石而卧,曰可休。” [11]727

《茅坤集》
对于居住空间的设计又蕴含着一种对于理想生活方式的预设,因此这种居住环境设计,实际上显示了晚明文人对于宴客活动的关注与用心。居住环境为文化生活的展开提供了空间,而文化生活又为文学、文献的产生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关于此,吴智和先生曾有过以下议论:
当低垣茅舍的住屋,被亭台楼阁的园林或园林格局的住屋所取代之后,首先,居住格局与空间的规划,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园林的格局为亲朋预留一个主客皆便的居住空间,以友朋为性命的时代生活文化得以浮现。[12]166
从笔记杂录中来看,晚明人的文化生活的确体现出“以友朋为性命”的特征:
周锡在《玄亭闲话》中说:“士大夫退居田里,一遵礼法,时与宾客欢叙丘壑,自是人生乐事,好结束处。”[13]4;费元禄(1575—1640)《转情集》中则有“清谈”“僧来”“酒熟客至”“谢客”“话旧”“宴客”等数条,皆与待客或客谈有关;高濂在《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中说饭后“或接客谈玄,说闲散话。”[14]216;冯梦龙《古今谭概》“癖嗜部”中亦言:“迨香水杂陈,内外毕具,而座客之谈谐,其可少乎!”[15]173黄景昉(1596—1662)在《屏居十二课》中罗列居家生活也有“朋来”一条;[16]4由这些材料不难看出,客谈在明代文人家居生活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而客谈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谈清事、谈神怪、谈地方掌故。
(一)谈清事
明季幽人韵士往往喜欢谈一些清雅之事,此类谈话也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元禄在《转情集》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良朋胜于佳节,清话可抵家书。韵士过从,朗朗玉山在侧;玄言满坐,霏霏木屑当前。谭空说有,间及鬼神;引古证今,不关朝市。奇文共赏,喜弹射为常;软语相遗,涉寒温而已。若乃益以奇香,资以苦茗,往来玄诣,虽达旦而未疲,宾主情深,每逢餐而必辍。[12]160-161
可见这里的谈话并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交流,更是一种带有着风雅意味的文化活动,清谈的过程还伴随着奇花异木、珍禽异鸟的同观共赏,主人预备的蔬果野味也常用来待客,从而使客谈变得更加富有情趣。
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就曾说过:“古人苹蘩可荐,蔬笋可羞,顾山肴野簌,须多预蓄,以供长日清谈,闲宵小饮。”[17]142
清谈的风格多偏于清雅,而规避俚俗。正因如此,奇文秘籍、诗词吟咏、书画赏鉴等便成为文人墨客谈论的主要内容,而赏鉴尤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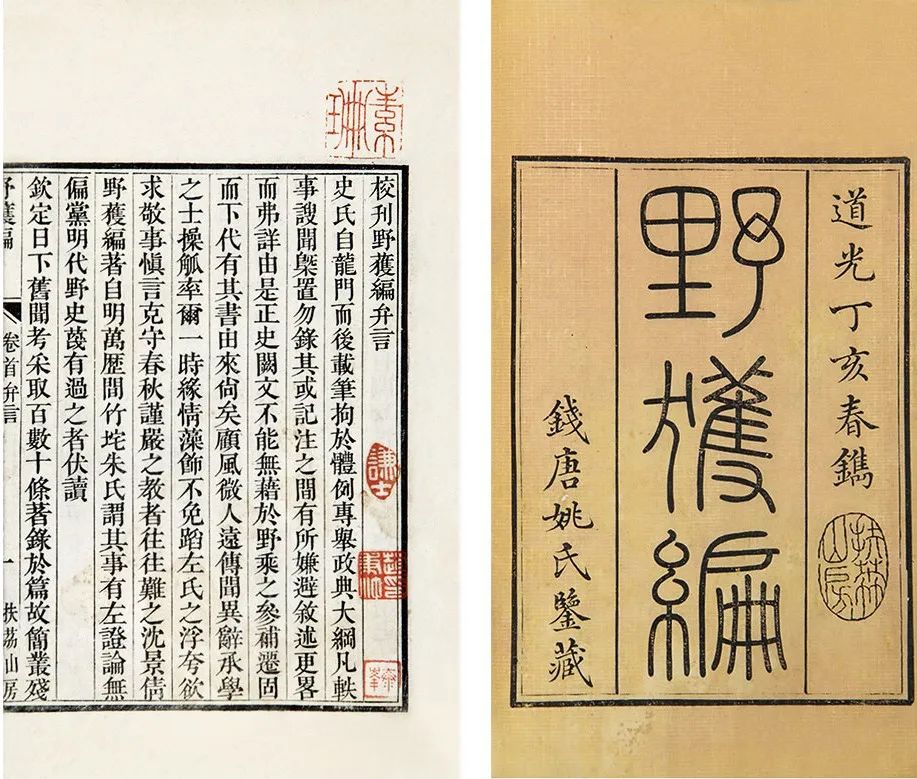
《万历野获编》
明中叶以后,赏鉴之风日趋流行: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中就曾说过:“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18]654
清人伍绍棠在为《长物志》作跋时也说:“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而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17]163这一风气直接影响到陈继儒(1558—1639)一些清事类笔记的产生。
陈继儒言自己因生在江南,又得以男子之身际遇清朝,因此得“读未见之书,眠渐高之日。”[19]244在此期间,门生故人多来走访,酒间常搜集一些古今文献、翰墨玄赏的掌故轶闻以资客谈。
其子听后,将相关内容手录投古盎中,积久成编。今观《太平清话》,保留了大量陈继儒及其友人对古玩、字画、器物的知见、收藏与赏鉴,又颇及山居清事,这正是当时晚明山人生活的重要写照。而此类书中所记录的谈话也多超尘脱俗,有着高度艺术化的清雅特征。《岩栖幽事》中就有一例,可作此类谈话风格之代表:
客过草堂,叩余岩栖之事,余倦于酬答,但拈古人诗句以应之。问:“是何感慨而甘栖遁?”曰:“得闲多事外,知足少年中。”问:“是何功课而能遣日?”曰:“种花春扫雪,看箓夜焚香。”问:“是何利养而获终老?”曰:“研田无恶岁,酒国有长春。”问:“是何往还而破寥寂?”曰:“有客来相访,通名是伏羲。”[20]695
在这段问答中,客人问及陈继儒隐居之后的生活,陈继儒以古人诗句分别描述了隐居的原因、隐居的功课、隐居的利养、隐居的消遣等等,从中不难看出其人悠闲平和的心态与自得其乐的心境。而在这一场合中诞生的谈话,也因此而带上了清雅恬淡的遁世色彩。

《明清文人清言集》
有此爱好的并非陈继儒一人:盛时泰(1529—1587)“喜宾客,四方客至者常满座,日与饮酒赋诗,闲举古玩书画赠,遗之不惜也。”[21]5079
焦竑(1540—1620)在为吴希元(1551-1606)所作的行状中也说他:“无他嗜好,独嗜古法书、名画、鼎彝、瑚簋之属,闭居扫地焚香,与客摩挲鉴赏以自适。”[22]11嘉兴文人李日华(1565—1635)也在退隐后优游田里,以法书名画自娱。这些文人的客谈应该都与陈继儒的谈话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
(二)谈神怪
谈神怪的笔记如黄奂(1596前后在世)的《黄玄龙小品·偶载》。黄奂自称喜听人说玄异之事,所结交多四方奇人,好为奇谈。后来一位客人征集土地公案,旁及神怪之事,作者将自己所听闻的新旧奇事以一日记之,由此便写成了《偶载》。[23]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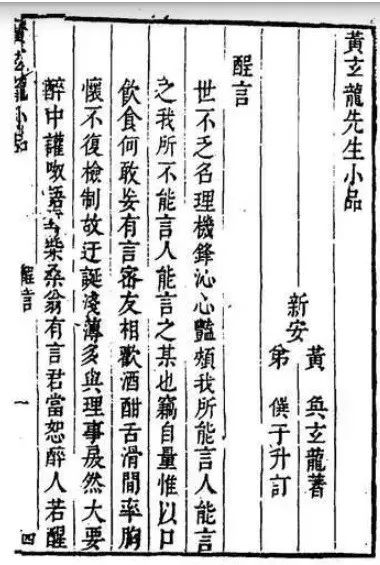
《黄玄龙先生小品》
因为此类客谈是以话题征集为形式的,故而谈话有着一定“主题先行”的特点,所谈之事都是向这一主题的靠拢与辐辏:书中前七条皆为何惟达被任命为土地神后游冥府的经历见闻;其余条目也多为土地城隍、神仙鬼怪、转世轮回之属。而讲述与主客交谈也成为此类谈话的主要方式。
由于谈神怪是抱着一种娱乐的心态而进行的,此时谈话的氛围较为宽松自由,讲述一个故事时,听者往往会随时加入一些插科打诨,从而使谈话的场面更加热闹。
在黄奂《偶载》的“城上覆釜”条中,作者讲述李惟达游冥府的情形,客人就发问:“四民之业,冥府何独缺一?”,黄奂则以一种调侃的口吻回答:“贾客善心计,较入锱铢,鬼不耐其计算,故不敢留之耳。”[23]326再比如在吴本如讲到关公、二郎神显灵的样貌时,黄奂就插话说:“关帝与二郎皆前代神,乃仪仗衣冠悉用本朝服色,岂神祇亦应尊奉大明官制耶?”,吴听后忍俊不禁。[23]331由此不难想见当时客谈的幽默情形。可以说,客谈轻松随意的谈话氛围,正是神怪、谐谑等内容诞生的温床,也决定了此类笔记条目的风格特色。
(三)谈地方掌故
客谈中,还有不少文人集中谈论当地地方掌故与人物轶事。这种风习在明代的金陵表现得尤为明显。金陵作为明代的陪都,虽然政治地位不如北京,但文化氛围却十分浓厚。关于这一点,焦竑曾有过这样的议论:
金陵六代旧都,文献之渊薮也。高皇帝奠鼎于斯,其显谟大烈,纪于石渠天禄,彬彬备矣。以故寰宇推为奥区,士林重其清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者,至今犹然。[24]4
一方面,金陵文人好谈议,另一方面,金陵文人又有着较为浓厚的宴客之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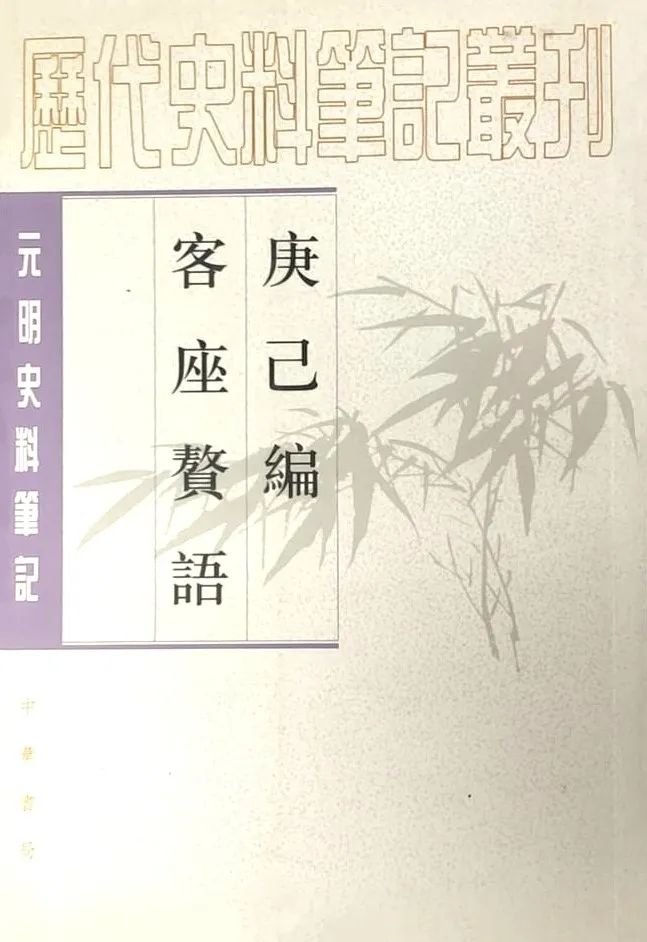
《客座赘语》
顾起元(1565—1628)《客座赘语》“南都旧日宴集”条载:“外舅少冶公尝言:南都正统中延客,止当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请吃饭’。至巳时,则客已毕集矣。”[25]225虽然后来宴客的方式有所改变,但这一习俗的本质依然保留了下来。
又说王少冶(1553进士)在晚年时,“每花发盆盎中,必招客饮,饮中好说古诗奇句,或古僻事奇人为令,嘲谑相错,风流文雅。”[25]224可以说,招客宴饮不仅可以拉近邻里之间的关系,也为客谈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与可能。
而隆万年间的一大批金陵文人,多有着非常浓厚的乡梓意识,着意于金陵一地乡邦掌故的搜求。
如《金陵琐事》的作者周晖(1546—1627)就曾提及孙光宪《北梦琐言》讥讽山人唐球诗思游历不能出二百里外,因为周晖所记也多为金陵之事,因此他“甚愧乎其言”;但又说:“嗟夫,余诚金陵之人而已矣。”[24]3可见他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地域归属。顾起元“生平好访求桑梓间故事。”[25]1焦竑在谪归以后,也专事著述,讲求留都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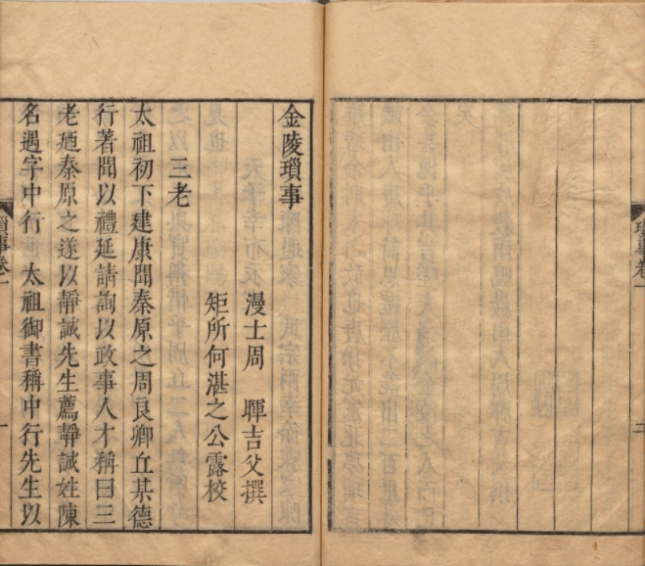
《金陵琐事》
尚谈议、好宴客的风气与乡邦意识相交融,导致了一大批金陵方志类笔记的产生,当时顾起元有《客座赘语》,周晖有《金陵琐事》系列,焦竑有《金陵旧事》,王兆云(约1601前后在世)则有《乌衣佳话》,从这类著作的大量涌现中正可以看出金陵一地客谈活动中谈乡邦掌故风气之盛。
总而言之,与家居生活相结合的客谈,谈话形式较为自由,谈话氛围较为轻松,因此形成的文本风格也多偏于清雅、闲适和幽默。谈话的主题往往和谈者的兴趣爱好有着密切的联系:好清雅者多谈赏鉴,好神怪者多谈异闻,乡梓情节浓厚者多谈乡邦掌故、人物轶事等。
当然,客谈话题的集中只是相对的,更多情况下,客谈会因为缺乏限制而旁及其他一些话题,这也成为客谈类笔记内容较为芜杂的一个根源。

晚明文人颇好结社,前人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都对这一现象做过有力的探讨。形形色色的“社”与“会”不仅将兴趣相同或相近的文人凝聚在一起,也为文人扩大自身的交际圈提供了重要的方式和途径。
而在结社活动中,文人之间常有谈议,这也成为“谈录类”笔记信息的另一个生长点。由于结社往往有着较强的目的性,活动也常在一定的主题下展开,故而社谈的内容相对来说较为集中;加上社规、社约对于结社活动时间、地点、内容、主题的规定与限制,社谈较之客谈更具有组织性和规律性。

《快雪堂漫录》
万历笔记中与社谈关系最密切的当属冯梦祯(1548—1605)的《快雪堂漫录》。冯梦祯的思想一直有着较为浓厚的佛教色彩,而归隐之后更与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祩宏(1536—1615)往来密切。在此期间,他还协助祩宏创办了旨在发扬净土宗“戒杀生”教义的社团——“放生社”。
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中,曾对冯梦祯有过如下记载:
公精心内教,弘护法门。性喜延接僧伽,无贤不肖率欣然引见。尝至净慈与寺僧大壑辈登慧日峰,憇莲花洞,语话终日。亦时与云栖老人、虞长孺、僧孺兄弟、黄贞父、葛水鉴诸公结放生社,流风余韵,照映千载。……是时司理:徐桂,字茂吴,余杭人,博雅工诗,尤长咏物,喜畜樽彝书画,称赏鉴家。祠部屠隆,字长卿,四明人,岁岁来湖上入放生社,赋咏甚富,皆梦祯同年。[26]321
可见当时“放生社”之活动盛况。“放生社”固然有促进文人吟咏、赏鉴的作用,但其本质依然是宗教性质的。“放生社”的成员不仅要捐出一定的钱财、贡品供养佛祖,也要常常携带被人抓捕的鱼鸟到寺中放生。

《快雪堂日记》
云栖大师祩宏还常集中社里成员进行经文讨论,要求他们早到迟退,不谈论俗事,多谈佛经与教化之事,冯梦祯正是这些社约社规的身体力行者。
从他的《快雪堂日记》中来看,他晚年参加“放生社”的聚会可谓十分频繁,而《快雪堂漫录》中的四位重要谈者,虞长孺、陈季象、徐茂吴、乐子晋正是通过放生社的相关活动凝聚在一起,并为冯梦祯讲述一些神佛灵迹的。
《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快雪堂漫录》时说它“语怪者十之三”“语因果者十之六”[27]1912,这当然并没有错。
但如果深入到谈话所诞生的场合就会发现,书中的“怪”与“因果”其实大多都与“杀生报”有关:如“永富化犬”“尼化猪”“杀生报”“屠牛恶报”之类的条目,可谓不胜枚举。在冯梦祯点明地点的条目里,有十条左右都是在云栖寺中进行谈话并记录的,而云栖寺正是“放生社”活动的主要场所。
由此可以得知:《快雪堂漫录》“放生”“戒杀”“斋戒”等思想基调的奠定其实与作者虔诚的佛教信仰以及放生社的社谈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文人结社谈话中,谐谑的地位也不可低估。晚明是一个幽默意识极为浓厚的时代,文人雅士好谑且善谑。而吴中一带,此风尤盛:《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在“苏州谑语”中就曾说过:“吴郡人口吻尤儇薄,歌谣对偶不绝于时。” [18]668江盈科《雪涛小说·谐史》里也说“吴中好相讥谑,不避贵贱。”[28]250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
张岱(1597—1679)在《陶庵梦忆》中就曾记载过一个专门谈论诙谐之事的社团——“噱社”:“仲叔善诙谐,在京师与漏仲容、沈虎臣、韩求仲辈结‘噱社’,唼喋数言,必绝缨喷饭。”[29]58“仲叔”指张岱的二叔张联芳,而虎臣正是沈德符的字。
在此条中,作者记载了帖括名士漏仲容对比少年与老年读书作文时的不同情形,以及韩求仲、张联芳的宴客谑语,皆具有浓重的戏谑成分,“绝缨喷饭”四字可谓恰如其分。试看下例:
仲叔候座师收一帽套,此日严寒,沈虎臣嘲之曰:“座主已收帽套去,此地空余帽套头。帽套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冷悠悠。”[29]58
沈德符化用崔颢《黄鹤楼》的前四句,将当时的场景形象、诙谐地描摹出来,千古名句由此也变成了一首诙谐幽默的打油诗。而这首“帽套诗”,在晚明通过笔记传抄的方式广泛流传开来,成为晚明谐谑的一个典范。而究其始,正与噱社成员之间的相互调侃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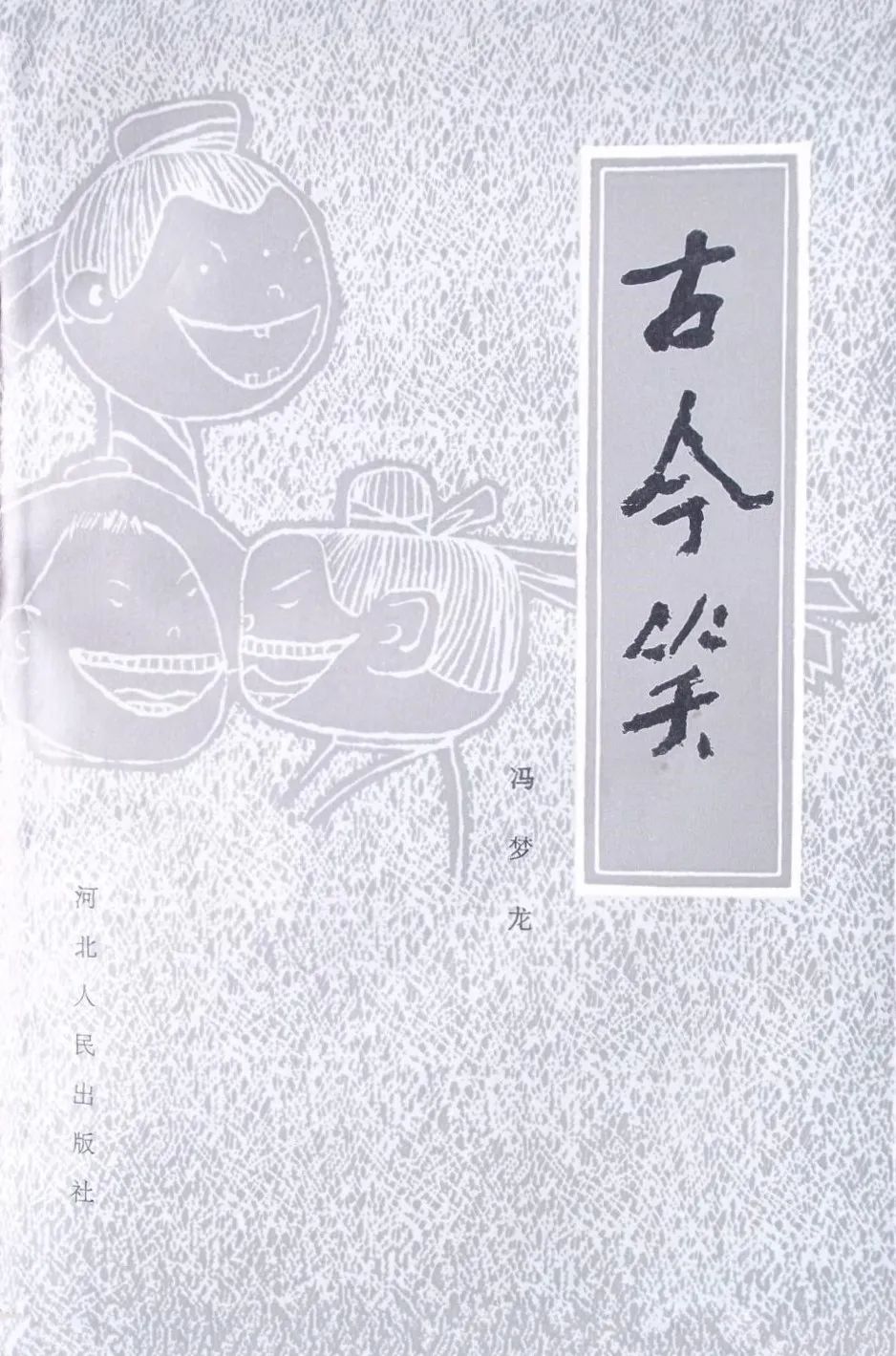
《古今笑》
此外,谈论谐谑之事的社团还有冯梦龙的“韵社”:
韵社诸兄弟抑郁无聊,不堪复读《离骚》,计惟一笑足以自娱,于是争以笑尚,推社长子犹为笑宗焉。子犹固博物者,至稗编丛说,流览无不遍。凡挥麈而谈,杂以近闻,诸兄弟辄放声狂笑。粲风起而郁云开,夕鸟惊而寒鳞跃,山花为之遍放,林叶为之振落。日夕相聚,抚掌掀髯,不复知有南面王乐矣。[15]1-2
由这段文字,不难想见韵社诸人当时戏谑欢笑的情形。后有社员建议冯梦龙不要以笑为社中私,而应该辑一部鼓吹以开当世之眉宇。冯梦龙正是听取了这一意见,方才在茶余饭罢辑录古今可笑之事成《古今笑》一书。可见:由谈话到纸上,由一社之笑到举世之笑,都是与“韵社”平时谈笑取乐的活动密不可分的。
明代诸多的“社”与“会”不仅为文人的凝聚提供了一种组织的形式,也成为规模性、群聚式谈话产生的最佳土壤。结社的缘由往往会对社谈的宗旨、谈话的主题构成影响,而社规、社约等也对诸人的谈话有着一定的限制作用,这也为谈话在固定范围内展开提供了一定的可能。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谈话场合作为一种言说活动展开的场域,虽然由谈者而构建,但长期以来,又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些与特定场合相应的主题、形式、特点与风格。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到进入这一场域的谈者的言说内容与言说方式,也会通过文人的记录,或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笔记的内容、体制、语体、体式、体性,最终孕育出截然不同的笔记风貌。

《中国笔记文史》
这也对目前的笔记研究构成一种启发,即研究笔记不能仅仅将目光集中在笔记作者写了一些什么内容,笔记当中具有哪些有价值的史料,更要关注:笔记是在一种怎样的文化场合中诞生的?笔记形成的过程伴随着怎样的文化活动?又有着怎样的文化传统?等等。
只有将笔记背后的文化行为加以复原,才能更加深刻地窥探笔记生成的整个过程,也才能更加深入地探讨笔记和相关文化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在笔者看来,也正是笔记本体研究走向深入的一条必由之路。
本文的写作曾受到香港研究资助局“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HKPFS)的大力资助,特此致谢。
上下滑动查看参考文献和注释
参考文献:
[1]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 陈才训.文人雅集与文言小说的创作及发展规律[J].求是学刊,2012(06).
[4] 严杰:唐五代笔记考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 陈刚:明万历笔记与谈话之关系说略[J].大学海(香港),2015(1).
[6] 陈第:一斋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7] 陈田,辑.明诗纪事: 己签卷18[M],民国25年版.
[8] 吴炯.丛语[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90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9] 王肯堂.郁冈斋笔麈[M].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0] 江应晓.对问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4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11]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2] 吴智和:明人文集中的生活史料——以居家休闲生活为例[J].明人文集与明代研究(台湾)[C].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2001年.
[13] 周锡:玄亭闲话:卷5[M].张振之隆庆元年序刻本.
[14] 高濂.遵生八笺[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子部第6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15] 冯梦龙:古今谭概[M].冯梦龙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16] 黄景昉.屏居十二课[M].丛书集成初编.哲学类第68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7] 文震亨.长物志[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18]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9] 陈继儒.太平清话[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4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20] 陈继儒.岩栖幽事[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8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21] 焦竑.国朝献征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7.
[22] 焦竑.焦氏澹园续集:卷16[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3] 黄奂.黄玄龙小品·偶载[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1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24] 周晖.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二续金陵琐事[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
[25] 顾起元.客座赘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6] 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43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
[27] 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1912。
[28] 江盈科.雪涛小说(外四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9] 张岱.陶庵梦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注释:[1] 关于为何要选择万历笔记作为研究样本,笔者在《明万历笔记著述方式初探》一文中曾予以说明,可参考:陈刚:《明万历笔记著述方式初探》,《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