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学科之间常有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而使美术的内容得以提升。苏轼对王维的诗歌和绘画的评价是:“尝莫诘词,其意在其意,其意在其意;“观其图,其图其词”,揭示了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

鲁迅的长篇小说的宏远、深邃,是世界上人们所承认的,他的长篇小说的成功,是因为他的“拿来主义”,他的创作视野是开阔的,他的创作思路是贯通了古代和现代,吸收了西方和西方的精华,而这个时代的新潮流,也是他创作的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鲁迅放弃医学而投身文学事业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日求学期间,在课堂中看到了一些幻灯,而那些与记录片相似的内容给了鲁迅很大的触动,而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影片的直观与煽动,也给了他很大的心灵震撼。
鲁迅归国之后,曾在各地的学校担任过教师,又到了教育部门,他十分重视影片的重要性,曾几次建议影片与投影相结合的方法:使用影片给人看,必胜过教师的教材。

“五四”以后,鲁迅以启蒙主义的身份走上了文学的舞台,把文学当作一把斩破日社会阴暗的利刃,提升文学的感染力,无疑是他思考的焦点之一,同时,由于他意识到“影片的巨大威力”,他把影片的一些表达方式,有意识地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从而拓展了近代小说的创作空间。
表达梦的艺术“因为它是图像的艺术,所以它的直观可以消除成人与儿童,有文化的人与不识字的人之间的区别。”正是由于它是一种图景,所以鲁迅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理智地认为:“而我,不愿意把我所认为的孤独,感染到和我年轻一样,正在做梦的年轻人身上。”这本书,实际上也是一种表达梦的艺术,它也是一种图景。

影片中的场景与颜色是一种特殊的结合,特殊的结构会有特殊的艺术性,流动的图像就会形成一个“镜头”。鲁迅的作品中,到处都有这样的“清晰”的图像。在夏瑜遇刺后,他的遗孀来悼念,鲁迅用一组图片表达了自己的悲痛和怜悯:“另一位女子,也是满头银发,衣衫褴褛,拎着一个红色的圆篮子,外面挂着一大把的纸钱,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前走。”
这是一幅客观的画面,我们能够感受到摄像机处于一种停顿状态,一位悲痛的妈妈慢慢地进入到了画面当中,而观众则是“单独的观影者”来观察这一惨烈的场面,影片中所拍摄的镜头与观众所观察的视角是相吻合的,所以会立即把观众带到这一惨烈场面当中。

在《毒方》的最后,我们发现了数个直接触及灵魂的空白场景:“墓碑上的青草尚未完全长好,一片片的泥土暴露出来,十分丑陋。”这些都是空白场景,隐含着当时阴郁黑暗的社会氛围;当他抬起头来,惊讶地发现,在那个圆形的墓穴顶部,竟然长着一朵红色和白色的花朵。
在这段空白的画面中,蕴含着情感的成分,震惊的不止是两位妈妈,更震惊的是所有的观众,缓慢的画面,在一片漆黑和绝望之中,给我们带来了一线生机和一丝希望,空白画面的精准使用,胜过了所有的讨论。“风已经停止了,干草像一根铜线一样竖着。

一声轻微的颤动,在空中变得越来越微弱,微弱到几乎听不见,四周一片死寂。“它就像一只铁打的石头,躲在一根又一根的树干里。”这一串空的镜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一种浓郁的气氛。在这一系列的场景中,可以看到无声中的群体力量,可以看到在这个铁板上存在着的不稳定的元素,也可以看到在英雄们的血液洒下后,在这一系列的场景中,人们看到了一种既有希望,也有希望的气氛。
而在这首歌的最后,“我看到了一只乌鸦,它扇动翅膀,身体一沉,朝着远方的天空,像是一支利剑,射向了远方。”特别是相似的几幅图,更是让人感受到了几分浓烈

要使作品能够更好地表现出创作主体的需求,就一定要有适当的构成手法。“图像的加工本质上就是一个单独的构思和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他就可以把他所忽视的一些细节,也就是那些细节。”
纵观鲁迅的长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优秀的创作高手,他用一种独特而又深邃的手法,把深沉的思绪和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鲁迅曾经说:“不知是何人所言,简而言之,要极省俭地把人物特征描绘出来,以其双眼为佳。”如果你把整个人的头发都给我,哪怕它看起来很精致,那也是没用的。我一直想用这个办法,可是没有成功。”

在《祥林嫂》的《福报》里,有很多有关她的镜头,让我们来看看:“她的头发五年前就变得灰蒙蒙的,现在又变得灰蒙蒙的,跟四十岁的人完全不同,她的脸又瘦又黑,再也没有了那种悲伤的表情,只有从她的眼睛里才能看出她是个活生生的人。她一只手拿着一只篮子,篮子里放着一只破碎的大盆。这一幕的特色在于,镜头跟随着创建者的双眼,通过特写和特写,镜头从上方往下,先是拍摄到了他的长发,然后慢慢往下,慢慢地拍摄到了他的面孔,而他的双眼,也被镜头放大,展现了他彻底的无助”。

其次,她拿着一个大特写,“她拿着一个篮子,里面有一个破碎的碗,里面是一个空荡荡的盘子,然后,她拿着一根比她还高的棍子,下面有一道裂缝,她拿着一根棍子,棍子断了。”
通过一组视角和结构的改变,突出了“祥林嫂”的“眼睛”和“竹杖断裂”等人物的生命形态,并用“大镜头”突出了“破的空碗”和“竹杖断裂”等人物形象,同时用“小镜头”对人物形象进行了描述,这样一幅象征图像,传递出了极为深刻的讯息。

“有年纪大的,有年纪大的,正坐在一张矮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把蒲团,跟他们聊天,有小孩在奔跑,有小孩在树上玩耍,有小孩在树上玩耍。妇女们给我们盛了一碗白白胖胖的白饭,还冒着蓬蓬的热气腾腾。”这是一系列的近景,这个画面在上一个画面的基础上,再往前移动,将故事中的角色一一呈现出来,让整个故事呈现出一副江南田园风光,闲适惬意的田园风光。

因为这一组的结构太好了,太形象了,以致于有可能淡化了文章中批评的主旨,因此,在文章的结尾,作家们就有了作家们的言辞和作家们的刻意回击。
除了构形以外,颜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鲁迅的创作中,他用黑白灰三种深沉的色调,来表达那些年迈的中国孩子们的悲伤和沉重,来表达他们心中的绝望和悲伤,他的创作风格,就像王国维对李白的评价:“太白是一种纯粹的意境,而鲁迅的小说,就是这样的意境。
在人物结构方面,他的画往往都是黑与白,特别是那些对理想的、对理想的、对理想的人的描述:“仔细观他的面容,仍是胡须、头发;一张国字脸,面色惨白,但却消瘦了许多。

在鲁迅的故事里,有时会出现一些生活的光鲜,这些光鲜的颜色可能是鲁迅内心最温柔的地方,例如著名的“童年知己”:“暗蓝色的天上,一弯满是金色的月亮,底下是沙滩,沙滩上长满了绿色的瓜子,中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脖子上戴着一串银戒指,”
在这个结构里,作家毫不吝惜他的优美的想象力,使整个沉闷的气氛里,一下子出现了蓝色,黄色,绿色,银等一系列鲜艳的颜色,以表示记忆的温暖,但是记忆成为了真实,作家却成为了对真实的冷漠的评论家:“原来的青白相间,现在却发黄了,还多了许多细细的褶子;他的眼睛和他的爸爸一模一样,红肿一片。”
影片对时空进行造型的艺术影片是一种对时空进行造型的艺术,为了使影片得以维持其精致性,去除无谓的时间和空间是必需的,这就是剪切。

这和鲁迅的文艺原则是一样的,他说:“选择材料要严格,挖掘要深入,不要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写在一本书上。”在鲁迅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有意地把时间和空间进行再排列,以下就以《疯子》为例证,来剖析其中的一些神秘之处。
在他的小说中,因为疯子的心理处于一种病态的状况,所以真实的时间和空间不再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一个持续的状况,在他的被害狂的病情下,他的思维所能认识到的只有他身边的人和事情,以及他身边的人和事情,鲁迅对这种支离破碎的“被害狂的错觉”的掌握,在文学上很难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前车之鉴,但是,它也是用了影片的蒙太奇方法的一个重要优势。

而影片的存在方式正是因为能够将真实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分割,只有蒙太奇特立独行的组合作用,才能够将其重构为影片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将“中断”和“持续”两种形态融合为一。
从表面上来看,这十三篇语颇为错综复杂的日志,很难进行一般的理解,但在引入了蒙太奇的理念后,理解就变得容易了,因为影片中的时空,本来就是分镜头的时空,每一个场景之间并没有一定的时间或空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发现因为“剪辑”而形成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断裂和新的延续。“今夜,月色不错。”在一片空白的背景下,一轮皎洁的明月,象征着疯子的灵感,透过这一幕,疯子就会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境界。
再接第二条:“今日皆无月亮”,一个黑夜的空镜头,进入了另外一个时间和空间,他们彼此无关,但是他们的心灵和性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上一个场景所提示的思想的醒悟,在下一个场景中立刻出现了不好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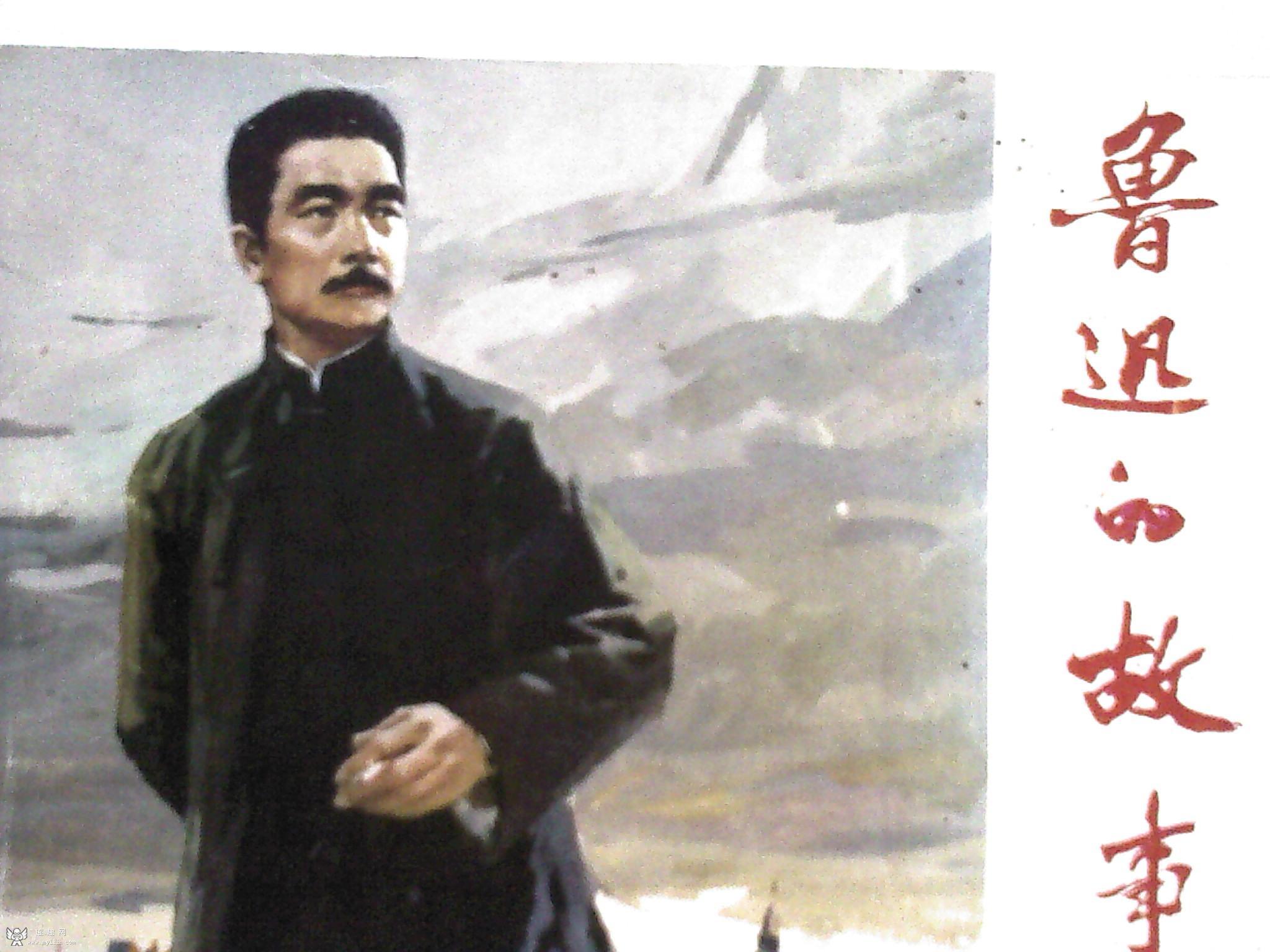
其次,在故事的后半部分,出现了一系列的记忆,这就是“叠印”的方法:《赵贵翁的眼神》、《七八个人的窃窃私语》、《一个人对我微笑》、《一群孩子的表情》,每一个场景都是独立的,但又联系在了一起,“《蒙太奇》并不只是一个场景,而是一个与真实不同的时空,在这个场景的后面,还有一种假设的时空结构。”
鲁迅以“疯子”的主观想像,呈现的并非是“实际”的情景,而只是一个假设的空间,一个“疯子”被众人憎恨的空间,这种“虚幻”与“实际”迥异,却正是这种“虚幻”在心理上的“实在”。

第三,它不但能将真实的空间和时间串联起来,而且还能将空间和时间串联起来,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疯子》中“吃人”形象的演化,正是一次跨时间和空间的跨越。
首先是在真实世界里食人,狼子村里的农夫口中的“食人”,这个真实世界里的时间和疯子的心态重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意义:“他们能食人,并不代表他们不能食我”。
然后,他又回到了那个虚幻的世界,“古代经常有人食人,我也想起了”,然后,他又联想到了另一个更悲凉、更深刻的含义:“这段历史,没有具体的时间,我失眠了,研究了大半夜,终于在文字的缝隙中,看到了一个词:食人!
结语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领域,作者必须从广义上“拿来”,这样他的创作就会变得更为自由。鲁迅曾经对中国文明的开放性赞不绝口:“想象一下,汉民族的胸襟是多么的宽广,外来的动物和动物,都是无拘无束的,用来做装饰品。
唐人的实力也不差,比如汉人的坟头上,雕刻着羊群、虎群、驱邪群,长安昭陵的坟头上,刻著一种骑着弓弩的马群和一只骆驼的飞禽,这是前所未有的。”鲁迅以其无拘无束的创作精神,以其“海容百川”的胸襟,为其“大家风范”作了最佳的注释。

参考文献:
【1】《南方方言》
【2】《连续图片的防卫》
【3】《鲁迅小说选编》
【4】《电影和电视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