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20日,位于澳大利亚南部海岸的阿得雷德港,展现出一座典型欧式城市的风貌。
相较于纽约的繁忙与纷扰,此地居民的生活节奏显得轻快而安逸。城市四周被茂密的森林环绕,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自然的宁静。在这片绿意盎然之中,珠光宝气的女性身着各式华美的帽子,如蔷薇花瓣帽、粉红网罩帽及头巾式无边帽等,五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港口的宾馆内人声鼎沸,来自澳大利亚各地及美洲的记者们纷纷聚集,渴望借助这一历史性时刻,通过采访名人以提升自身知名度。

随着一列火车缓缓驶入站台,人群开始涌动。火车尚未停稳,记者们便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去。治安警察迅速排成两队,维护秩序,将部分试图强行上车的记者拦下。随后,麦克阿瑟与琼相继出现在车门口,瞬间成为所有目光与镜头的焦点。麦克阿瑟对于此类场面早已习以为常,他摆出惯用的姿态,以胜利者的形象展现在公众面前。此时的他尚不知晓,意大利媒体正用“懦夫”一词形容他,日本人称其为“逃兵”,而德国画报则讽刺他为“脚底抹油的将军”。他挥动着手臂,大声宣告:“我出来了,但我还会回去。”这句话,尽管朴实无华,却成为广为流传的名言。细心的记者注意到,麦克阿瑟在讲话中使用了“我”而非“我们”,这一表述引发了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一句充满信念的鼓舞之词;而反对者则指责其在此等场合过于突出个人,显得傲慢、狂妄,甚至虚伪、好大喜功。对于这一争议,或许麦克阿瑟的部下们的解释最具权威性:将军口中的“我”,实则代表着“我们”。麦克阿瑟满怀激情,眼中闪烁着希望之光,他郑重宣布:“自今日起,即1942年3月20日星期五,我们将……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连续挫败已接近尾声,强大的盟军力量势必跨越太平洋,最终战胜敌人,彻底终结日本帝国的霸权。”这一宣告激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人群激动不已。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语穿透时空,自澳大利亚广袤的沙漠林屋至纽约繁华大街的贫民窟,无处不在。尽管麦克阿瑟在巴丹曾经历挫败,但在国内,他被视为能够扭转乾坤的英雄。民众并未过分苛责其在菲律宾的失利,而是更侧重于颂扬他率先向日军发起反击的壮举。正是这一“英勇无畏”的举动,为美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重塑了信心。因此,一股强劲的“麦克阿瑟风潮”迅速席卷了整个英语国家。美国参议员们提议将6月13日设为“麦克阿瑟日”,以纪念他于1899年这一天成功考入西点军校。

国会以253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授予麦克阿瑟荣誉勋章的决议,这一票数甚至超越了历届美国总统所获得的记录。当罗斯福总统选择威廉•李海上将作为其首席军事顾问时,《时代》周刊表达了不满,指出若由民众投票决定,麦克阿瑟无疑是不二人选。一向保持客观理性的《纽约时报》也破例以生动的笔触,将麦克阿瑟比作好莱坞塑造的理想士兵理查德•戴维斯,赋予了他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民族》杂志同样不甘示弱,在扉页显著位置写道:“国民对领袖最为钦佩的品质,便是‘将军’那般坚韧不拔的斗士精神。”新闻界对麦克阿瑟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纷纷惊叹于他在复杂环境中的“深远洞察力”以及“激励并领导士兵前行的卓越能力”。澳大利亚本地媒体也积极响应,纷纷在头版大篇幅刊登麦克阿瑟的肖像。在伦农旅馆,麦克阿瑟将军的办公室电话号码B-3211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任何有兴趣的公民拨打此号码,接线员都会礼貌地回应:“您好,这里是巴丹精神的象征。”《纽约太阳报》驻伦敦记者发来的专访报道指出:“自电影明星瓦伦丁诺之后,麦克阿瑟将军无疑成为了又一全民瞩目的焦点。”麦克阿瑟,一位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极高知名度的军事人物,其名声之盛,以至于伦敦的各大报纸频繁将他与历史上的军事英杰纳尔逊和德雷克相提并论。甚至苏联的《真理报》与《消息报》也在其头版显著位置发表评论,赞誉麦克阿瑟展现了与苏联士兵同等的英勇品质。麦克阿瑟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直至战争落幕,一个未曾预料的效应逐渐显现。美国商界敏锐地捕捉到,众多家长倾向于以“麦克阿瑟”为孩子命名,视其为勇敢与胜利的象征。借此契机,商家们创新推出了“麦克阿瑟系列”商品,涵盖服装、蜡像、甜豌豆乃至铁锁等多样产品。同时,该名字也被建筑师与经纪人广泛采用,诸如“麦克阿瑟大桥”、“麦克阿瑟水坝”、“麦克阿瑟大厦”以及“麦克阿瑟歌舞晚会”等命名层出不穷。连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在公开演讲中,对麦克阿瑟的胜利突围与新任职务表示祝贺,认为这标志着美国反攻的序幕即将拉开。面对如此高的期待,麦克阿瑟能否兑现其反攻菲律宾的宏伟誓言,却成为了悬而未决的问题。

战争中的荣耀与希望虽真实存在,但麦克阿瑟很快意识到,现实远比预期复杂。当他抵达澳大利亚,期望能够组建起一支强大的陆空联军,以解救被困于巴丹与科雷吉多尔的盟军时,却遭遇了严峻的现实。澳大利亚的精锐青年已奔赴北非战场,仅余3万民兵可供调配,且其中许多人缺乏实战经验。至于空军,仅有150架老旧的飞机,其状态之差,连升空作战都显得力不从心。海军方面,虽有6艘巡洋舰,但多为从菲律宾撤退时的残兵败将。面对如此困境,麦克阿瑟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夜晚难以入眠,即便入睡,也仅维持片刻便醒来。作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官,他肩负着指挥该区域盟军的重任,却缺乏必要的海空支援。战争该如何继续,连他自己也心中无底。面对公众许下的壮志豪言,如何兑现成为关键问题。实践往往比言语更为艰难。麦克阿瑟一向自信其口才足以媲美五个师的战斗力,但此次能否成功收尾,唯有天意可决。当麦克阿瑟抵达时,澳大利亚的防御体系已近乎崩溃。先前,澳大利亚构建了两层防御屏障,首要者乃“布里斯班防线”。此防线位于墨尔本东北方向约1100公里的海岸线,其布局实则等于将澳大利亚北部区域暴露于日军威胁之下。更令人诧异的是,整个澳大利亚居然未配备一辆坦克,即便是此防线亦未能幸免于装备匮乏之困。此情此景,不禁令麦克阿瑟回想起巴丹战役,回想起他的部队,以及昔日那得心应手的指挥体系与精良装备。这一切皆已遗失于菲律宾战场,如今正被日军转移至伊里安岛,炮火直指澳大利亚。他在地图上定位巴丹,仿佛能看见通往马尼拉之路上,美军战俘在日本刺刀下,垂头丧气,双手抱头,向战俘营行进。面对敌人的残暴,他的部下面临失败的屈辱与恐惧的绝望。麦克阿瑟深感痛楚,星条旗与美国陆军的荣耀何在?这是自1776年以来未尝败绩的军队,而今失败的阴影却笼罩在他身上。内心的痛苦与无力感侵蚀着他的心灵,他前所未有的感到软弱。经历数日失眠后,麦克阿瑟决定将其司令部由墨尔本迁移至布里斯班。布里斯班的伦农旅馆成为他的居所与西南太平洋总司令部的所在地。伦农旅馆为布里斯班之豪华地标,临近群山、荒漠与大海。入驻首日夜晚,麦克阿瑟沐浴后,以一条印有南极山毛榉图案的毛巾裹身,躺于柔软的床垫之上。宽敞的大厅内,他难以掩饰对室内布置的不满。如此优雅的房间,竟缺乏精致家具的点缀,仅充斥着笨重粗犷之物。在专业鉴赏家麦克阿瑟的锐利目光下,那些色彩搭配失当、尺寸比例失衡的二手物品与缺乏珍稀价值的装饰品无所遁形。尽管他的主要身份是军人,但其在收藏领域的洞察力堪称卓越。遗憾的是,因日本侵略者的战火肆虐,他珍藏的宝物尽数遗落于马尼拉,未能为他提供一个静谧的自我欣赏空间。

约莫一小时后,麦克阿瑟已从厅中央的藤椅中起身,借助落地灯的柔和光芒,审阅着案头堆积如山的文件与报纸。他迅速处理了数项紧急军务,随后挑选了一份报纸,全神贯注地阅读起来。他对政治的深切关注广为人知,甚至有言论认为,若他涉足总统竞选,亦非毫无胜算。正是这份卓越才华,让他在美国政坛遭遇了诸多非议与排挤。对此,麦克阿瑟始终保持淡然态度,不为所动。他起身走向窗边,轻轻拉开厚重的天鹅绒窗帘,凭栏眺望布里斯班那璀璨夺目的灯火海洋。黄、白、彩三色霓虹交织于墨黑的海湾之上,与繁星交相辉映,美不胜收。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布里斯班被赋予了“小迈阿密海滩”的美誉,但实际上,它与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大相径庭。这里空旷宁静,地域辽阔却略显单调,拥有纽约般广阔的地域,却只居住了四五十万人口。一条曲折蜿蜒的小河穿城而过,宛如蚯蚓般匍匐于城市之中。城市布局缺乏规划,道路狭窄且维护不善,宛如随意搭建的格子状迷宫。老房子错落有致地高耸于各处,建筑风格多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遗迹,屋顶覆盖着波纹铁皮,窗前挂着格子帘。此外,四分之一的本地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高耸的教堂中,时常传来管风琴演奏的圣歌,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神圣的气息。如此种种,使得布里斯班宛如人间仙境。当欧亚大陆被黑暗笼罩之时,这里的灯火却如此迷人。酒吧中啤酒爱好者的喧嚣、市政厅附属音乐厅内悠扬的管风琴声以及别墅内本地居民无忧无虑的彻夜欢歌与舞蹈,共同铸就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使其在全球众多名城如伦敦、巴黎、柏林、莫斯科、重庆、罗马、华沙、奥斯陆、哥本哈根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相较于其他城市,布里斯班免受灯火管制的限制,亦未遭受邓尼茨潜艇的海上侵袭。在战争的阴霾之下,此地宛如一片独特的避风港,象征着和平的绿洲。在和平缺失的年代,和平的价值愈发显得弥足珍贵,成为世人心中最向往的瑰宝。和平的取得,往往以鲜血为代价,这使得麦克阿瑟对和平抱有深刻的职业感悟。他忆起往昔在菲律宾的时光,与父亲、妻子及儿子在明媚的天空下,于美丽的马尼拉共度的美好时光,那种幸福难以言表,只留下片刻的温馨记忆。而今,当这些记忆渐行渐远,他才愈发怀念那段时光。与那段短暂的美好相比,占据他思绪的更多是巴丹战场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景象。每当思及此景,麦克阿瑟仿佛触及了内心最敏感的神经,双眼肿痛,内心激荡,喉咙哽咽,昔日的狂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悲伤。菲律宾不仅塑造了他,也彻底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个体。这种变化同样波及了他的部下,从参谋长至副官,皆变得异常严苛,有时甚至显得不近人情。最坚强的人往往也最为脆弱,麦克阿瑟便是如此。在他威严的外表之下,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孤独、幻灭、自责且痛苦的影子。他时常感叹命运的不公,即便逃离了菲律宾,仍需承受无尽的苦难。他的荣辱、成败、兴衰,似乎都寄托在这片420年前由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发现的海岛上,而何时方能彻底摆脱这困顿的境地,仍是未知数。当前,他手中毫无力量可言,既无步兵,亦无舰队与飞机。他凭何跨越从布里斯班至马尼拉这长达8000公里的广阔天空、浩瀚海洋与众多岛屿?若不能重返菲律宾,他恐将沦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可怜、可笑且可悲的小丑。与此同时,在北非战场,一位曾在麦克阿瑟麾下效力的年轻军官——小乔治·巴顿,这位比他晚五年进入西点军校、拥有英国血统的校官,正率领大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在北非战场的战略行动中,盟军采取了一项出人意料的举措,迫使德军向加贝斯湾方向撤退。与此同时,美军协同蒙哥马利指挥的第8集团军,成功地将“沙漠之狐”隆美尔率领的非洲军团围困于突尼斯与比塞大之间的一片广袤平原上,此役一举歼灭了德意联军共计25万人。这一辉煌战果迅速吸引了美国和盟国各大报纸、电台及杂志的广泛关注。公众舆论中,巴顿将军被塑造成为一位现代版的古罗马角斗士,其英勇威猛与卓越战功足以媲美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与神话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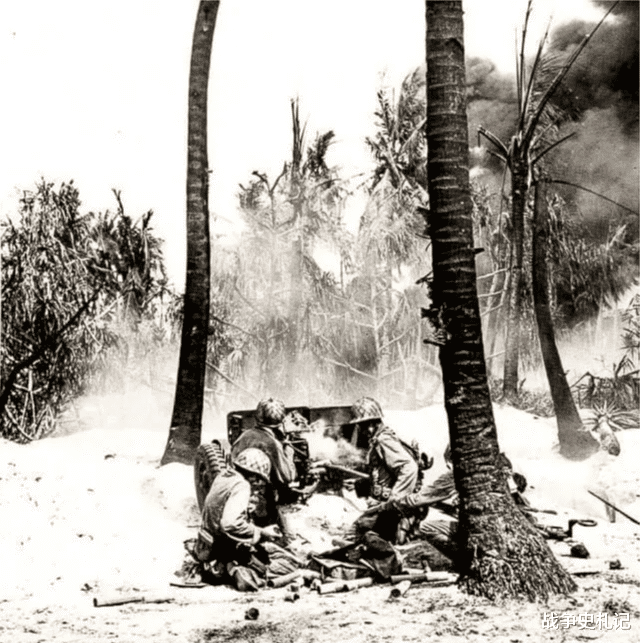
巴顿将军的照片频繁见诸报端,其言论被广泛传播与颂扬。部分女性追随者甚至佩戴起他偏爱的皮带与皮鞭作为时尚符号,而一些年轻人则竞相模仿他的语调、神态乃至细微举止,包括他特有的眨眼频次,这些特征也被媒体细致描绘,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面对这一态势,麦克阿瑟将军深知,若自己在澳大利亚战区无法迅速取得显著成就,恐将面临公众关注的流失。因此,他深感有必要积极寻求新的作战机遇,以期在战场上重新占据公众视野的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