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典籍的校勘整理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书籍的出现而产生,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成规模、有意识的校书始于刘向、刘歆父子,其后从事校勘者代有其人,至清代,经许多学者的大量运用而得以光大,成为整理文化典籍的一种有效方法,显示了乾嘉之学的不俗实绩。至现代,经叶德辉、陈垣等著名学者在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终于成为一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独立学科。

《校勘学释例》
但是,这些校勘学的理论和方法多是建立在对经史类典籍校勘整理的基础上,对古代小说的整理虽然也有一定的指导和启发意义,但并不十分贴切。因为古代小说的创作、刊刻及流传同经史类著作乃至诗文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具有许多自身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因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低贱社会地位,很少有学者愿意下工夫去进行认真的校勘整理。至20世纪,当小说的地位大大提升,对其进行的整理研究成为一门与经史并列的专门之学时,探讨和总结符合古代小说自身特点的校勘整理方法,就成为小说史研究者要迫切解决的一个新的学术课题。
对古代小说的校勘整理,鲁迅、汪辟疆、汪原放、孙楷第等研究者都曾进行过可贵的尝试,他们将先前学者治经史的功夫用在古代小说的研究整理上,开学界之新风,并皆有相当丰硕的收获。
相比之下,以孙楷第对古代小说的整理研究用力最勤,成果最丰,其研究也最具典范意义。孙楷第曾师从著名学者陈垣,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以毕生精力研治小说、戏曲,成就卓著。就治学方法而言,他从版本目录、训诂校勘入手,将乾嘉学风应用于通俗文学的研究,并根据实际情况加以灵活变通,摸索出了一套符合小说实际的整理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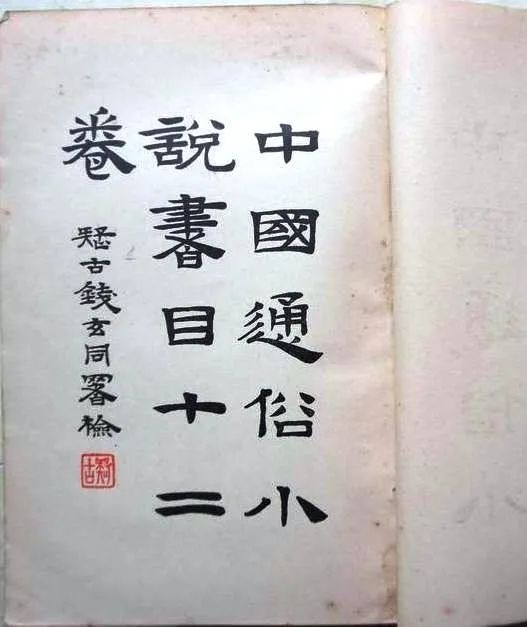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等著述都显示了他在小说目录学方面的成就,这些书籍至今仍是研治小说史的必备参考书。
其小说整理校勘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新近出版的《小说旁证》一书中。
《小说旁证》是孙楷第先生用毕生心血写成的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初创于20世纪30年代,此后几十年间一直在修订补充,其间曾在《文献》、《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刊出数则。由于各种因素造成的延搁,直到20世纪的最后一年才得以出版。
该书共收录160多篇话本小说的本事材料,以“三言”、“二拍”为主,“征其故实,考其原委”[1],主要目的在钩稽古代话本小说的本事素材,探讨古代小说的渊源流变之迹。作者的态度极为严谨审慎,不仅对书中所收各篇小说的本事渊源进行细致的梳理辨析,而且对作为本事素材收入书中的有关资料也大多进行了精细的校勘。
由于这些话本小说取材大多源自历代笔记野史,自身亦属小说作品,其中不乏名篇佳作,故该书也可当作一部校勘精良的专题小说选集来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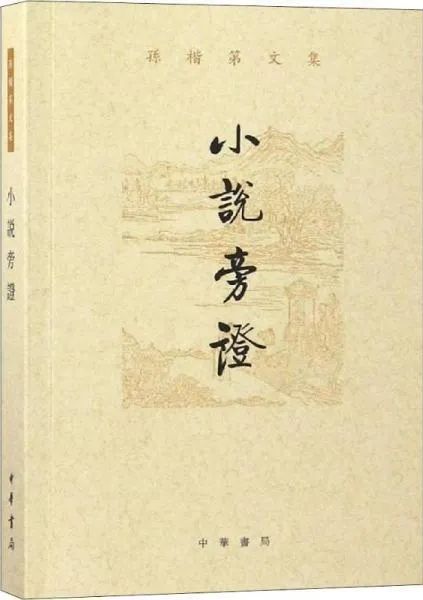
《小说旁证》
《小说旁证》一书所收材料采自诸书,其版本文字精疏优劣自然各不相同,情况较为复杂,孙楷第先生根据各篇作品的具体情况,采用了多种有效的校勘方式,可以说校勘古代小说所遇到的各类情况在该书中皆有涉及,加之作者随文出校,从中可以探其校改原由。
因此,该书也可以看作是古代小说校勘整理的一个范本,该书所采用的诸多有效的符合小说实际的校勘方法,对今天古代小说的校勘整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典范和指导意义。
对古代典籍的校勘,著名学者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一书中以校勘《元典章》所精选的一千多条校例为例,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和归纳,使校勘学提升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特点的专学,胡适称之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认为该书“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2]。
在《校勘学释例》一书中,陈垣先生归纳出4种有效的校勘方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这些方法早已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和采用,奉为古籍校勘所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陈垣全集》
孙楷第先生终生仰慕陈垣的道德学问,其学术研究受陈垣的影响较深。因此,笔者在本文中有意将孙楷第先生校勘小说的诸种方法与陈垣所总结的四校法进行对比,以见古代小说校勘与其它文类典籍校勘的相通之处,以见古代小说校勘整理自身所独有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可见出孙楷第先生在校勘小说方面对陈垣四校法的继承和变通,由此可以明了其治学的渊源与创新之迹。
总的来看,《小说旁证》一书主要采用了如下一些校勘方法:
其一是不同版本间的校勘,即选用一种较好的版本作底本,再用其它不同的版本参校,这和陈垣所说的对校法基本相同,但具体处理方式又有所不同。
陈垣认为对校法的“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3],孙楷第先生则更进一步,既校异同,又辨是非,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取舍,进行增补删改,并随文注出异文以明示校改的依据。
再如底本的选择,陈垣校勘《元典章》时,弃更好的元刻本不用,而以错误较多的沈家本刻本为底本,尽管其大量的校例可为后学者示范,但就一般典籍的校勘来讲,这种底本选择的方法显然不可取,既费时又费力[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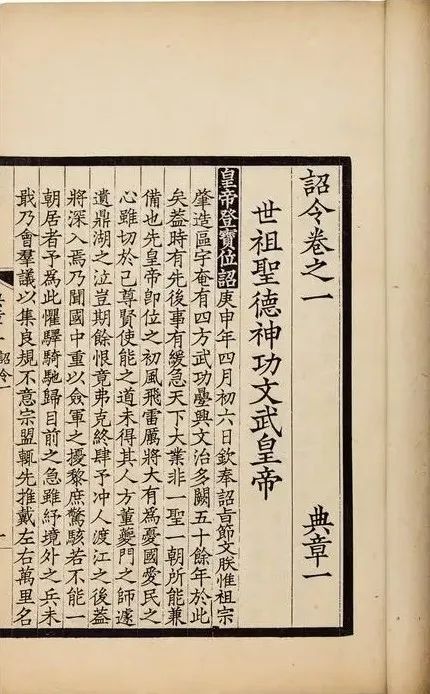
《元典章》
《小说旁证》一书没有固守这一做法,对底本的选择还是十分慎重的。比如全书本事资料采自《齐东野语》的部分,选用涵芬楼印本为底本,这个本子系夏敬观据现存最早的元刻明补本整理而成,校本则采用据明正德刊本重刻的汲古阁刊本,这是目前所见到的《齐东野语》最好的两个版本。选定质量较好的底本、校本后,再根据文句的异同情况酌情校改,经过这样校勘的文字无疑是十分可信的。
其它如该书采自《效颦集》者据日本旧抄本为底本,以明刊本参校;采自《灯下闲谈》者据涵芬楼校印本为底本,以《适园丛书》本、原本《说郛》卷十一参校等皆是如此。
不同版本间的校勘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校勘,如上述所举诸例;一是同一作品不同书籍间的校勘。古代小说作品,特别是文言小说,篇幅较短,难以单独成书,经常被各种书籍选收,因此,需要进行不同选本间同一作品的校勘。
孙楷第先生在处理这一情况时,往往以最先收录该作品的书籍为底本,以后出的各类选本做校本。比如作为《灯花婆婆》本事的《诺皋记》,就以原载该作品的《酉阳杂俎》明刻本为底本,以后来选收该作品的《太平广记》为校本。应该说这种处理方式是十分妥当的。

明汲古阁刊本《酉阳杂俎》
其二是同一题材不同作品间的校勘,这是《小说旁证》一书采用最多的一种校勘方式,与陈垣所说的“以他书校本书”的他校法虽有些相似,但又有诸多不同,应该说是古代小说所具有的特例,在其它文类中较为少见。笔者姑且仿陈垣命名方式称其为旁校法。
古代诗文在作者完成作品后,只有流传过程中因版本不同造成的文字上的差异,很少有人去进行改写修订,但古代小说则不然,不少作品在题材、情节上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往往是一篇内容新奇的作品产生后,被其它人略加改写修订,又变成另外一篇作品,收入各自所撰的笔记野史中,结果就出现了一篇作品衍生出人物、情节大体相同的一类作品的现象。
这些作品不仅人物、情节、结构基本相同,甚至在文句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因此,可以利用这种相似性进行小说作品的校勘,即将同一作品所衍生的一类作品放在一起校勘,不仅可以比较人物、情节间的异同,探究小说人物故事的渊源流变,也可以借此订正一些文字上的讹误。
《小说旁证》也正是利用中国古代小说的这一特点进行了校勘学上的尝试和创新。比如《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楷第先生收录较早的《九龠别集》卷四《负情侬传》为本事来源,同时以《删补文苑楂橘》、《情史》、《亘史》所收同一题材的作品进行参校。

《警世通言》
虽是同一篇作品,人物、情节基本相同,但四种版本之间文句差别较大,孙楷第先生经过仔细的比勘,“梳其异同”,整理出一个较为可信的读本。全书类似情况很多,这里不再一一举例。
其三是依据小说之外的其它文类的一些典籍记载来校正小说作品中一些人名、官职、地名、数字的讹误,这基本上与陈垣所归纳的“他校法”相同,但具体到小说的校勘上,两者又有一定的差异。
陈垣认为采用“他校法”,“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5]。
但这种方法并不太适合古代小说的校勘,因为诗文类的写作不管如何讲究文采,如何夸饰,其内容基本上是真实的,可以利用其它书籍的记载来校正其中的一些事实、名物上的错误,但古代小说则不然,其情况较为复杂,就笔记野史的写作而言,其中固然有不少作品是据实而作,但更多的作品则是真伪杂糅,有的系虚构之作,有的属道听途说。

《沧州集》
内容的真实性尚不能确定,用其它书籍径直进行校勘显然不妥,因为这样就抹杀了小说的虚构和想象,将小说等同于实录了。况且古代小说的实际写作及文化地位与诗文也不相同,既较少引用他书,也较少被他书所引用,因此用“前人之书”、“后人之书”和“同时之书”进行小说的校勘有很多操作上的困难。
但难操作并不是不能操作,《小说旁证》一书根据小说作品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灵活处理,大胆尝试,使他校法也得以为小说的校勘整理服务。
这可以说是孙楷第先生在小说校勘上的一个创新,从治学方法上讲,它同现代著名史家陈寅恪所创的以诗证史之法在思路上正好相反,但殊途同归,都是将文史打通、融会贯通的高明之举。
中国古代的笔记野史固然虚构者较多,但采用真人真事的作品也为数不少,因此,在叙述一些真实的人物事件时,往往合乎史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为史学家所取资。在这种情况下,就也可以利用史书及其它书籍的记载来校正小说作品中的一些史实、名物,并进行一些文字上的比勘。

《古今小说》总目
比如《古今小说》卷五《穷马周遭际卖 追媪》,孙先生选用谈恺刊本《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四《卖追媪》为本事来源,同时用《新唐书》、《旧唐书》来校正其中人名、数字以及字句上的一些讹误,并在文后的按语中进行说明。
同样,《古今小说》卷三十《明悟禅师赶五戒》一篇,选用《津逮秘书》本《甘泽谣》中的圆观篇为本事来源,同时用《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七、《高僧传》卷二十、《冷斋夜话》卷十相关记载进行参校。
因古代内容的真伪杂糅,因此这种以史证稗的校勘方式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运用不好,会造成将小说等同史书的弊端,这种校勘方式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
从《小说考证》一书来看,孙楷第先生将这种校勘方式只是运用在具体名物以及字句的辩正上,分寸的把握还是比较恰当的,并没有泛用滥用的现象。总的来看,这种新的校勘尝试是有益的,可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对今天的古籍校勘整理仍有一定启发。
其四是根据小说作品的前后文校正其中的一些错误,这和陈垣先生所总结的“本校法”基本相同,即“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沧州后集》
这种方法多系在“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采用,因其直接取证于作品本身,可信度往往很高。《小说旁证》一书也采用了这种校勘方式。
比如《古今小说》卷三十《明悟禅师赶五戒》,孙先生引《冷斋夜话》卷七一段文字为本事材料,其中一句为“二人大喜”,在“二人”后有校记:“‘二人’疑当作‘三人’。”之所以当改作“三人”,是根据上下文推知的,因为上文说的是云庵梦见自己同子由、聪禅师三人去拜访五祖戒禅师,醒来后又和子由、聪禅师讲述,这时接到东坡的书信,三人都在场,显然大笑的应该是“三人”而不是“二人”。
再如《醒世恒言》卷五《大树坡义虎送亲》,孙先生选录《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八《勤自励》条为本事材料,在“我即自励”一句有校记:“原脱‘励’字,今径补也。”之所以要“径补”这一“励”字,是因为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勤自励”,而且这句话就是他所说,自我介绍,显然,“我即自励”后缺一“励”字。

金阊叶敬池刊本《醒世恒言》
不过,本校法在古代小说校勘中应用的空间不大,这是因为古代小说特别是文言小说作品往往篇幅很短,根据上下文进行校勘的余地较小,不象经史著作那样,篇幅较大,有很多可供发挥的余地。但总的来看,这也不失为古代小说校勘整理的一种有效方法,可根据具体作品的实际情况而灵活采用。
最后一种是没有其它版本可资参校,或几种版本的文字虽然相同,但其字句颇为可疑,难以读通,则依据上下文语气或一定的语言文化规则如文字、音韵、训诂、语法、历史文化制度等知识来定夺文句的正误,这就是陈垣所说的理校法,即“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6]。
校勘时有善本可依固然很好,但没有善本可依并不能就此放弃校勘,不过就像陈垣所说的,这种校勘方法有一定的风险,对校勘者的素质功力有很高的要求。
也正是为此,有些学者对理校法持保留态度,比如胡适就反对这种校勘方式,他认为“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是校勘学的唯一途径”,而理校则“不是校勘的正规”,“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7]。

《胡适全集》
利用善本对校是校勘的有效途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并不是唯一的途径,这也是明显的,因为校勘不一定总是能找到善本,况且善本也并不是没有讹误的地方。
因此,理校法还是可以有其发挥功能的空间,只是要求校勘者态度更为审慎严谨而已,就像陈垣先生所说的:“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8]。
古代小说特别是白话通俗小说在中国古代因不受重视,不象别的文类作品那样有较多的善本可依,缺乏善本的情况较为严重,因此,理校法对小说的校勘来讲更为必需,否则一味依赖善本,校勘工作就无法进行。
孙楷第先生长期师从陈垣,曾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治学态度极为严谨,他自然深知古籍校勘中善本的重要作用。但是从《小说旁证》一书来看,孙楷第先生在其他校勘法之外,仍然大量使用了理校法这种校勘方式,显然这是孙先生根据古代小说版本具体情况而进行的灵活变通。

《孙楷第集》
不过,他并没有滥用这种校勘方式,其态度极为审慎,改必有理有据,处理方式得当。总的来看,其意断大多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由此显示出其扎实、过人的学术功力。
首先,他的校改建立在对文句的仔细推敲及对作品文化背景的深刻理解基础上,并点出校改之由。
全书例证甚多,这里仅举两例,如《初刻拍案惊奇》卷27《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孙先生选取《剪灯新话》卷4的《芙蓉屏记》为本事材料,其中“偶外间忽有人买草书四幅”一句中的“买”字孙先生认为有问题,“‘买’,当作‘卖’”,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上下文可知,当时御史大夫高纳麟“多慕书画”,而崔俊臣正值落难,“惟卖字以度日”,因此,其买卖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同一文中,孙先生认为进士“薛理溥化”之名当作“燮理溥化”,因为“薛里溥化”史书无载而“燮理溥化”则是实有其人,《揭文安公集》中有载,两个名字的字音大致相同,发生混淆是很有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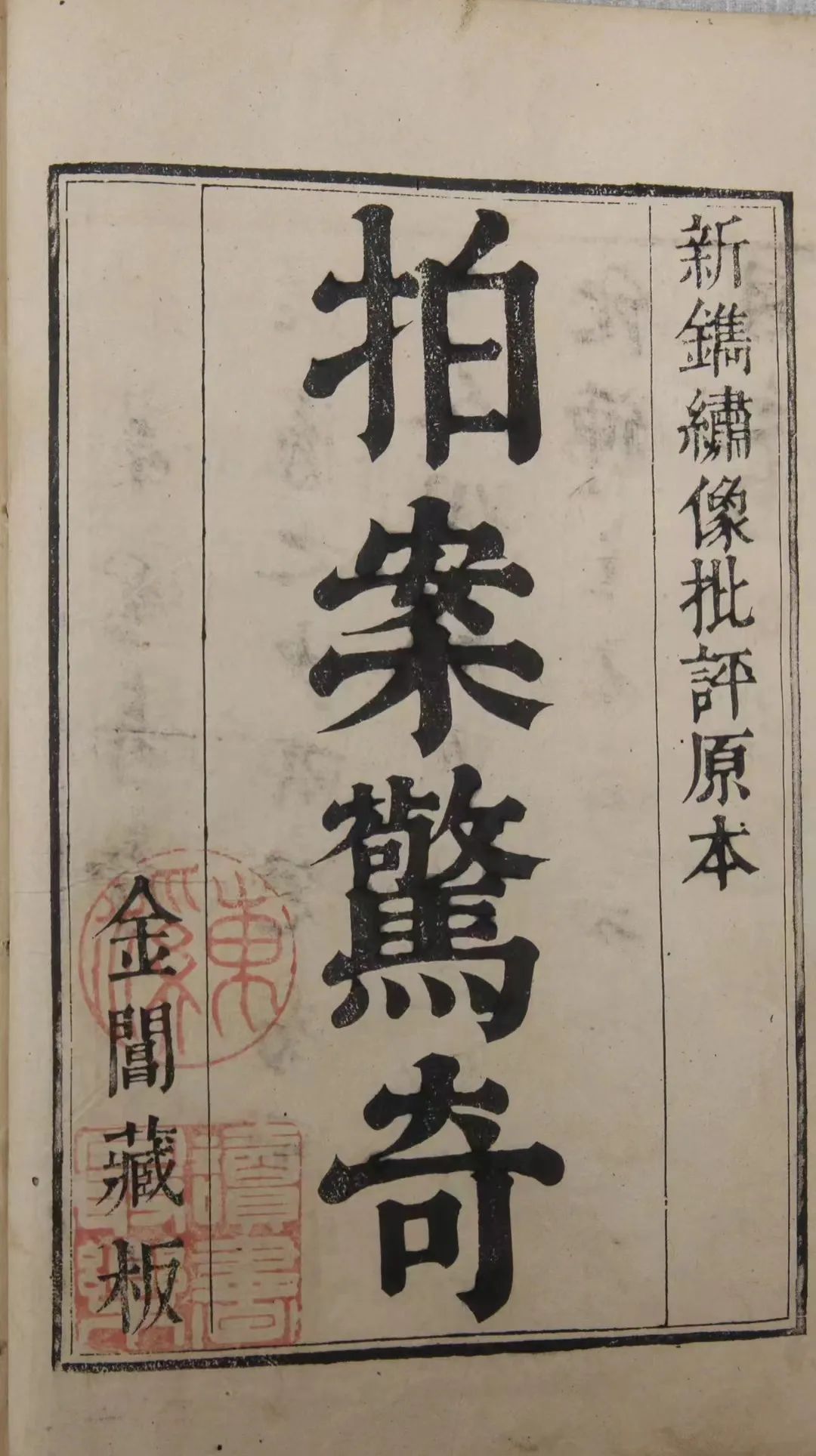
金阊藏板《拍案惊奇》
其次,文句可疑的情况不同,孙先生的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
像前面所举的前一个例子,“买”字的错误是很明显的,因此使用十分肯定的语气,“‘买’,当作‘卖’”。而后一个例子中,“薛理溥化”当为“燮理溥化”,虽然有一定的文献根据,但没有完全的把握,所以孙先生使用了存疑的口气:“‘薛理溥化’,疑当作‘燮理溥化’。”一个“疑”字,显示了孙先生极为审慎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
全书使用理校法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处理方式。同时,尽管怀疑文字有问题,有不少很有十分充足的证据和把握,但孙先生还是没有据此改动原文,而是保留原文,把自己的看法附在有问题的文字后,为读者提供参考。应该说这种处理方式还是十分妥帖的,既表达了个人的见解,同时又使原文得以完整保留,为读者的阅读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既继承和遵循校勘学的一般原则和规范,又根据古代小说的具体而加以灵活变通和创新;既表达了个人对文句正误的一些见解,有理有据,又不妄改字句,注意保留原文的完整性。

《孙楷第文集》
孙先生经过对古代小说校勘的具体实践,探索出了一套符合古代小说自身特点的科学校勘方法。这对古代小说的校勘整理无疑具有典范意义,因此将《小说旁证》视作古代小说校勘领域的《校勘学释例》,当不会是过誉之词。
注释:
[1] 孙楷第《小说旁证》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2]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陈垣《校勘学释例》,载刘乃和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 对采用对校法时是否需要用善本做底本的问题,黄永年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论》一书中辨之甚详,可参看。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 陈垣《校勘学释例》,载刘乃和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6] 陈垣《校勘学释例》,载刘乃和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陈垣《校勘学释例》,载刘乃和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