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学术领域,学术界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估一直都是偏向于批判的一面,很难注意到鲁迅与传统的联系。

产生这一视域偏移的根源,是因为许多学者始终把鲁迅与新文化运动以及它的特殊本质相结合,因而设定了一个起点,把鲁迅置于当时被定义为“彻底颠覆”的文化大革命的主将和旗帜,但就中国近代文化背景而言,不管是极端派或保守派,都默许了“断裂”的文化活动,并把“传统”与“现代”分开,虽然两派观点迥异。
在这样一种强有力的语言指导下,鲁迅的个人性格在某种意义上归于幕后,被世人所忽视。

在时间的流逝中,在那些伟大的叙述逐渐消失和褪色之后,在我们的反思那些被强大的语言所掩盖的现实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到,将一个特定的时间和一个特定的个体,特别是鲁迅这样的一个拥有超自然思维能力的人,并不能用一种理性的眼光去看待。
就鲁迅和“传统”的关系来说,它具有尖锐、深邃的批判精神,同时又与扎根于本土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不仅具有其特有的民间思想,而且在其创作的各种作品中都体现出了这样的特点。

鲁迅早期在日本留读期间所写的《破恶声论》一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假文人应走,迷信尚存”,从民间的视角来看,鲁迅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迷信”(也就是民间传说)的认同,并通过对“伪士”的批评,对当代中国民间习俗的合理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破恶声论》于1908年完成,于同年十二月在东京发行的《河南》期刊上刊载。鲁迅当时还未当过“新文学”的旗帜人物,他仅仅作为一名学生,到日本东京从事文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在这段时间里,他发表了大量的古文文章,《破恶声论》就是他的代表作。

鲁迅与民间的联系,在其后的文献中并未着重论述,而《破恶声论》则充分展现了其特有的民间观念。
本文所说的“伪士”,即是以“科学”为名“破迷信”的“志士”。“崇科学”、“破迷信”是二十世纪早期西方文化传播的一种口号和一种思想。
五四启蒙时期,这种思潮成为中国一面旗帜,继而席卷了二十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在鲁迅早年的作品里,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并引起了各种的质疑与批判。

鲁迅主张,不能以科学自身作为摧毁宗教的借口,因为“志士”高呼“科学”的名号,非但没有把宗教的正义感带到民众身上,反倒用它作为压抑和掠夺民族的精神生活的方法。
鲁迅再进一步说,这些“志士”本身,也不一定具备什么科学学问或智力,只是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借着这个幌子,为了谋取私利,一切“破迷信”,都是他们致富的一条捷径。所以鲁迅把这些人叫做“伪士”,也就是那些虚伪的“志士”。

鲁迅则积极地承认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生存的合理性和价值。鲁迅认为,赛会、祭神等民俗,尽管是封建社会的一种迷信,但也是一种虔诚的信仰,是一种真正的、令人愉快的心灵生命。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行动,是人的心灵发展的历史结果,是祖先对物质生命的超脱。
与宣扬“以提倡科学为借口”来压制、消解传统民间习俗的思想不同,鲁迅更重视人的心灵,而这是一种非物欲的精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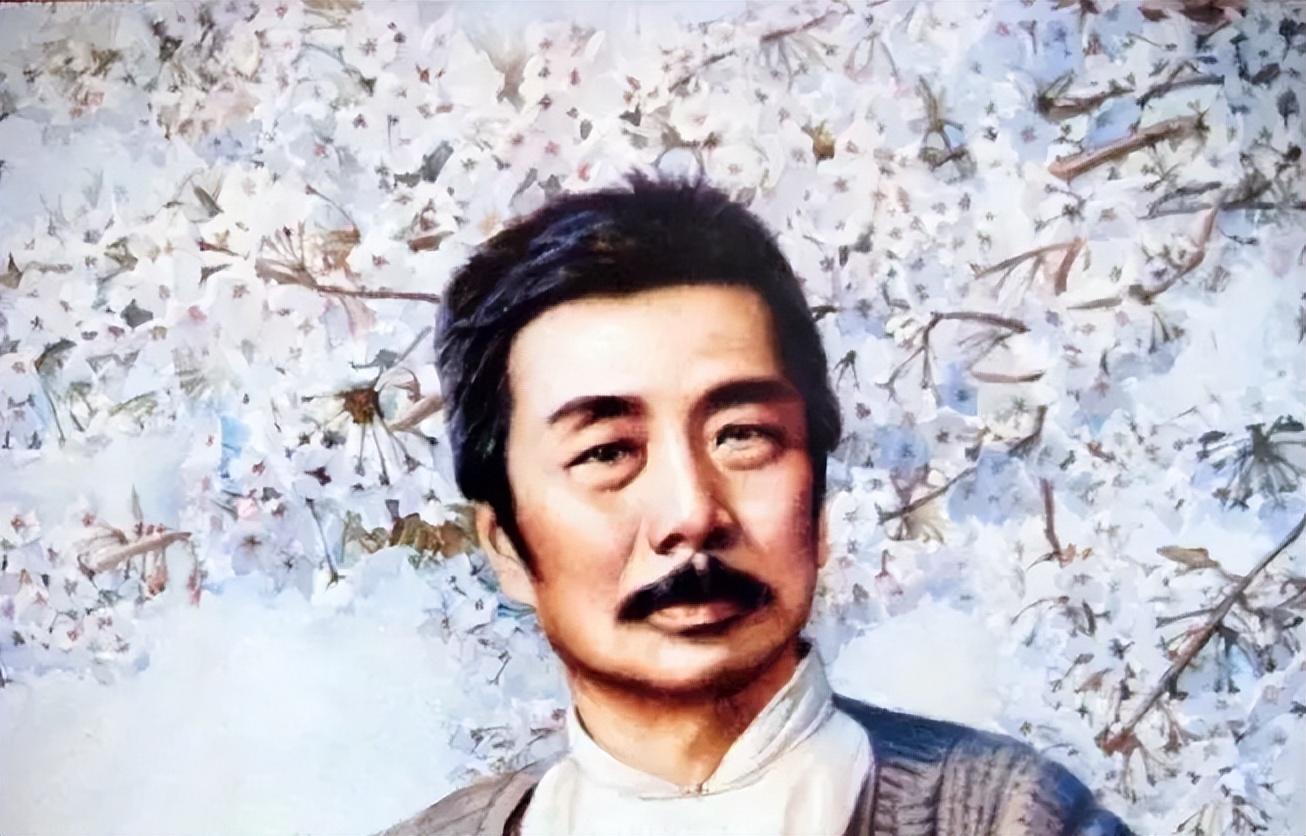
在“伪士”的眼里,“迷信”看似简单,其实是一种上进的精神。与当时的特定时期相结合,寻求民族救亡、民族的发展,首先不在于物质,而在于心灵。
鲁迅并非完全的反科学,他自己也是自然科学家,早期在中国的矿山学校学矿物,后来在日本仙台进修了医药,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所以,对于那些以科学为名破坏民族传统的做法,他是非常愤怒的。

鲁迅自己在学习之途上的转型,亦是其价值定位的一个重要体现,由《破恶声论》所建立的民间观念,在鲁迅整个人生中都是根深蒂固的,甚至连五四新文化高擎“科学”大旗的五四新文化也没有因此而有所变化。
温暖记忆与幽暗意识——童年经验中民俗因素的双重影响既然如此,鲁迅为何对这个象征着灵性的民间传说这么重视?鲁迅的很多追忆散文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探寻其原因的蛛丝马迹:他的幼时生命常常与各种乡村民间的文化事件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回忆中,既有温馨光明的一面,又有阴郁的一面,回环交错纠缠,构成了鲁迅独特的儿童体验,并对其个性的塑造产生了直接的作用。

鲁迅的童年快乐,在他的记忆里,往往和乡村的运动会联系在一起。
鲁迅的儿时参加过“目连戏”的《社戏》、《五猖会》、《无常》等回忆文章。正因为这样的对比,鲁迅对戏剧这个民间的行为有了更深的印象,因此他对民间故事始终抱有一丝温暖,并抱以积极的心态。
但是,鲁迅的儿时回忆里却有着另外一种体验,这种体验与《社戏》中所描绘的清新温暖截然相反,充满了一种沉闷和迷茫。虽然与传统的民俗文化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所传递的影响却是消极的。
最好的例证是叙述性的《五猖会》。本文所描写的“父亲”,只不过是受传统伦理观念影响下的许多父辈的典型,其消极影响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广义地说,民间的概念,既包括像马会社等乡村社会的民间文化,也包括在传统思想引导下的日常生活和习惯,后者尤其会带有某种规范性、训诫性的价值观,并以此来约束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
鲁迅的童年回忆中,由于民族民间文化的双重属性,产生了极端强烈的反差情绪,其回忆式的文章常常将二者的鲜明冲突凸显出来,构成了一种经典的反差。
一是色彩鲜明、朝气蓬勃的“看戏”;二是严肃冷酷、深沉压抑的“背书”,民间文化在正面和负面的双重作用下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不但参加了比赛等民间的活动对鲁迅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在他的记忆中,这是也最温暖的一面,而实际上,目连戏中的戏剧意象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并在他的心灵世界中逐步成长升华,成为一种自我言说的符号意象。其中包括了“无常”和“女吊”两个戏剧人物。

在鲁迅的作品里,《无常》是对目连剧表演的最积极的描述和观众的情感的描述,而“无常”这个人物的表现尤为突出。
“无常”就是“死”,也就是“最后的审判”,但鲁迅认为,它不只是“死”,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要不断地去应对。
我们一定要说鲁迅的深邃,但是,他的深层根源,就在于“向死而生”,面对凄凉的生活,他的胆识和力量,所以,“无常”的形象,在鲁迅的生命中,一直徘徊着,挥之不去。

《目连戏》中的另外一个角色叫“女吊”。“女吊”和“无常”不一样,是复仇女神的化身,是一种行动的标志。
鲁迅的“女上吊”就是这样一个受了屈辱和伤害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得到公平的待遇,哪怕他们已经堕入了地狱,他们也会继续报仇。
“无常”和“女吊”都是鲁迅童年时代印刻在戏剧里的经历,他们和戏剧里的回忆不一样,既不像戏剧里的回忆那样温润,也不像礼仪的回忆那样厌恶和困惑。

但他们结合在一起,在鲁迅的心灵发展中不断生长、升华,温存和困境、承认和质疑,都变成了一种令人兴奋和悲伤的黑暗意识,但这都是鲁迅从民间文化中获得的一种精神营养。
启蒙理想与时代境遇——表现于文学创作中民俗传统的冲突与困境鲁迅的童年体验中的民间色彩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冲击,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的作品选择。鲁迅的现实题材作品大多以家乡为题材,还特地取了一个虚拟的名字“鲁镇”,各种乡村风俗习惯都是它的特点,体现了江南的风土人情。

作为一个作者,鲁迅最熟悉的还是童年时代,家乡给他留下了深刻而丰富的回忆,因此在他的笔下,最能打动他的,就是家乡的风景。
家乡的民间故事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鲁迅在多年以后,受到了西方的教育,他已经萌发了一种新的思想,他的信仰和理想,就是要改变中国。

从启蒙的观点来看,对古老的、愚蠢的东西进行批评,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文艺作品中,它必须转换成一种特定的意象。《狂人日记》一书中,鲁迅将“狂人”视为启蒙者和觉醒者的代表人物,对“吃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批评。
我们可以看到,民间传统的正面与负面的对立面,内部的矛盾,都是从儿童时代的无意识中产生的,形成了一种内部的原型。

鲁迅虽主张“启迪”,但与一般的启蒙家不同,他并不以“新人”自居,反而将自己置于一个老时代的“老手”地位,这是因为他自己的诚意。
《在酒楼上》描写了吕纬甫这个昔日启蒙的人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吕纬甫就是鲁迅自己,在经历了一场辛亥革命的狂热之后,传统的社会并未发生什么改变,自己已丧失了童年的乐趣,却要背负着生活的沉重负担,鲁迅虽然是开创者,但他并没有完全信任这些鼓吹的人,也从未认为这种厌倦和孤独正是五四时期的一名普通员工鲁迅的人生境遇。
中国会因为一个梦想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鲁迅所关心的,却是社会中最低级的民众,在这一次的革命中,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虽然鲁迅从来没有抛弃自己的启蒙思想,但他又是一位坚持的写实主义作家,他的洞察力和洞察力远超常人。
正是因为他来自旧的年代,烙印着古老的风俗习惯,所以他对那些还活着的人很熟悉,对他们的“魂灵”了如指掌。他并没有为这个时期的思想灌输任何的思想,而是在启迪的思想的映衬下,将这一矛盾的思想和现实的矛盾展现在他的作品里,并表现了他的内在矛盾。
结语竹内好曾经用“挣扎”来描述鲁迅的人生境遇,鲁迅一直在新旧、欢愉与冷峻的民间生活中苦苦抗争,时而批评,时而扞卫,但他所关心的焦点却永远都是人的存在与精神的解放。

时代的风土人情、物象的变化是无法阻挡的,鲁迅对这一问题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在早期的时候,他主张“取今旧制,另立新派”,而在他的晚年,则主张“拿来主义”,要“取其精髓,除其渣滓”,凡是符合人性、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东西,都要敢于拿出来创新。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种正确的民间观念。
参考文献:
鲁迅:《无常》,《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鲁迅:《无常》,《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日]竹内好:《鲁迅》,《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鲁迅:《女吊》,《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鲁迅:《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鲁迅:《五猖会》,《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