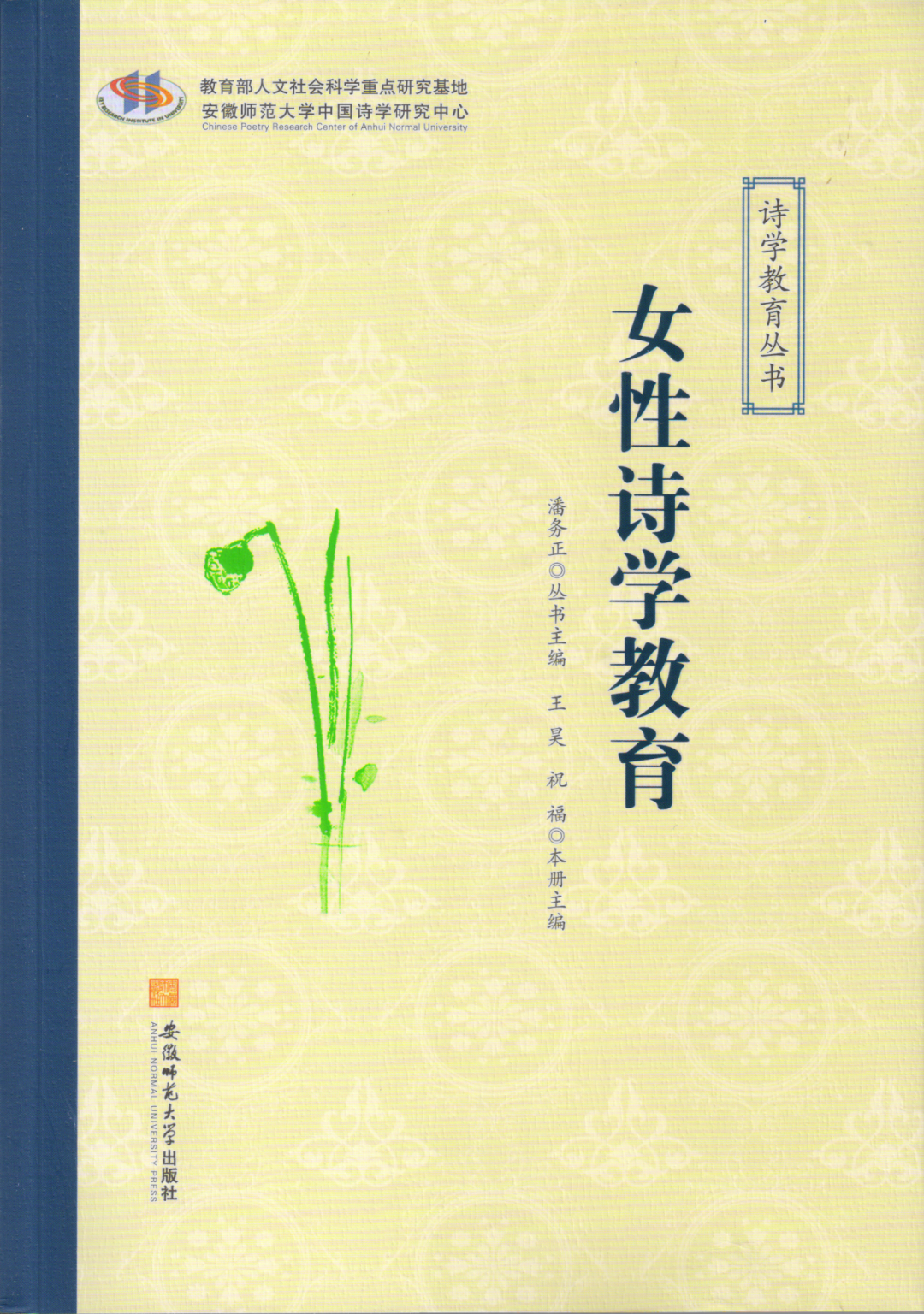
《女性诗学教育》,王昊、祝福主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

该书以“女性诗学教育”为主题,关注女性作为诗学教育接受者与传播者的重要角色,选取学界优秀学术论文15篇。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梳理先秦至当代女性诗学教育的发展历程;中编以传统诗学教育观念之间的对立、转化、融合为重点,聚焦女性诗学教育在思想上的艰辛开拓;下编以女性诗学教育的场域为核心,呈现女性由家庭、家族内部空间进入公共空间,通过拜师、游学、结社等途径接受诗学教育,并产生“闺塾师”这一特殊教育职业的变化过程。

前言:女子学诗,庸何伤乎?
——百年中国古代女性诗学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女性诗学教育历程
春秋时期女性赋诗、引诗析论 胡宁
论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诗歌创作 郭丽
明清女子文学启蒙教育述论 郭英德
“诗”“歌”传统的消长与晚清新女性的诞生 曹晓华
吴梅词学教育新范式与潜社女词人的词学活动 徐燕婷
千春犹待发华滋
——略论叶嘉莹先生的诗教传承 陆有富
女性诗学教育观念
清代闺秀诗学观念论析 宋清秀
清代女性诗歌创作论争的诗教依据及深层动因 朱君毅
“花间”与“诗教”之间:清前期女性写作传统的构建 黄晓丹
“诗穷而后工”说的拓展与“诗福”说的产生 蔡德龙
女性诗学教育场域
清代女诗人的成长与家庭教育 郭蓁
清代女性戒子诗的母教特征与文学意义 曾礼军
论清代常熟屈氏家族女性的文学活动与传播 梅新林 娄欣星
从闺内吟咏到闺外结社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突围之路 袁志成
游学与明清闺塾师的文化身份认同 赵崔莉

女子学诗,庸何伤乎?
——百年中国古代女性诗学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诗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占据显耀位置,汉学家孙康宜对比中西方女性文学之后发现,与西方女诗人的边缘化不同,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女作家几乎都是诗人[1]。张秀玉亦指出女性作家创作存在“诗多文少,或有诗无文”[2]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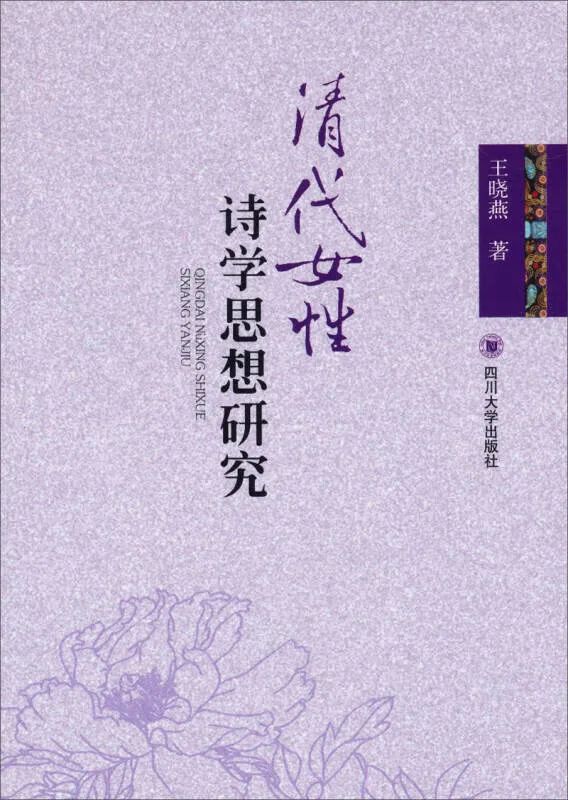
《清代女性诗学思想研究》
这表明诗与女性在历史中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诗的写作与诗的教育同在,“诗学”与“学诗”,对于中国古代女性来说实际上是一体之两面。但女性诗人在创作之前的准备因文献之阙如而不为人所知,女诗人往往被冠以“才女”头衔,似乎其写诗是生而知之,这使我们忽视了女性真实的诗学历程,忽略了其所受的诗学教育。
诗学教育是社会文化教育的组成部分,当诗学教育与道德教育联结,女教和诗教融合,它就成为反映古代女子生活状况、文学观念、写作境遇的一面镜子。
一、女子学诗的艰难历程
古代女子接受诗学教育、进行诗学教育的方式是多样的。早期接受诗学教育的女子多在贵族之家,或经由父兄在家庭中完成,如汉之兄妹诗人班固与班昭,父女诗人蔡邕与蔡琰。也有夫妻唱和,互相学习的,如李清照在南渡逃亡中,仍留有“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3],可见她早年与赵明诚的夫妇吟咏之乐。
但这种情形毕竟罕见。宋代以降,出版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得诗集的编选、刊刻、传抄更为便利,女性诗学教育的途径得以开拓。
明清两代女性教育状况更是大为改善,许多女子在闺阁时不但得到父母兄长的教育,而且可以接受家庭塾师的指导,就像《牡丹亭》中杜宝聘请陈最良教育杜丽娘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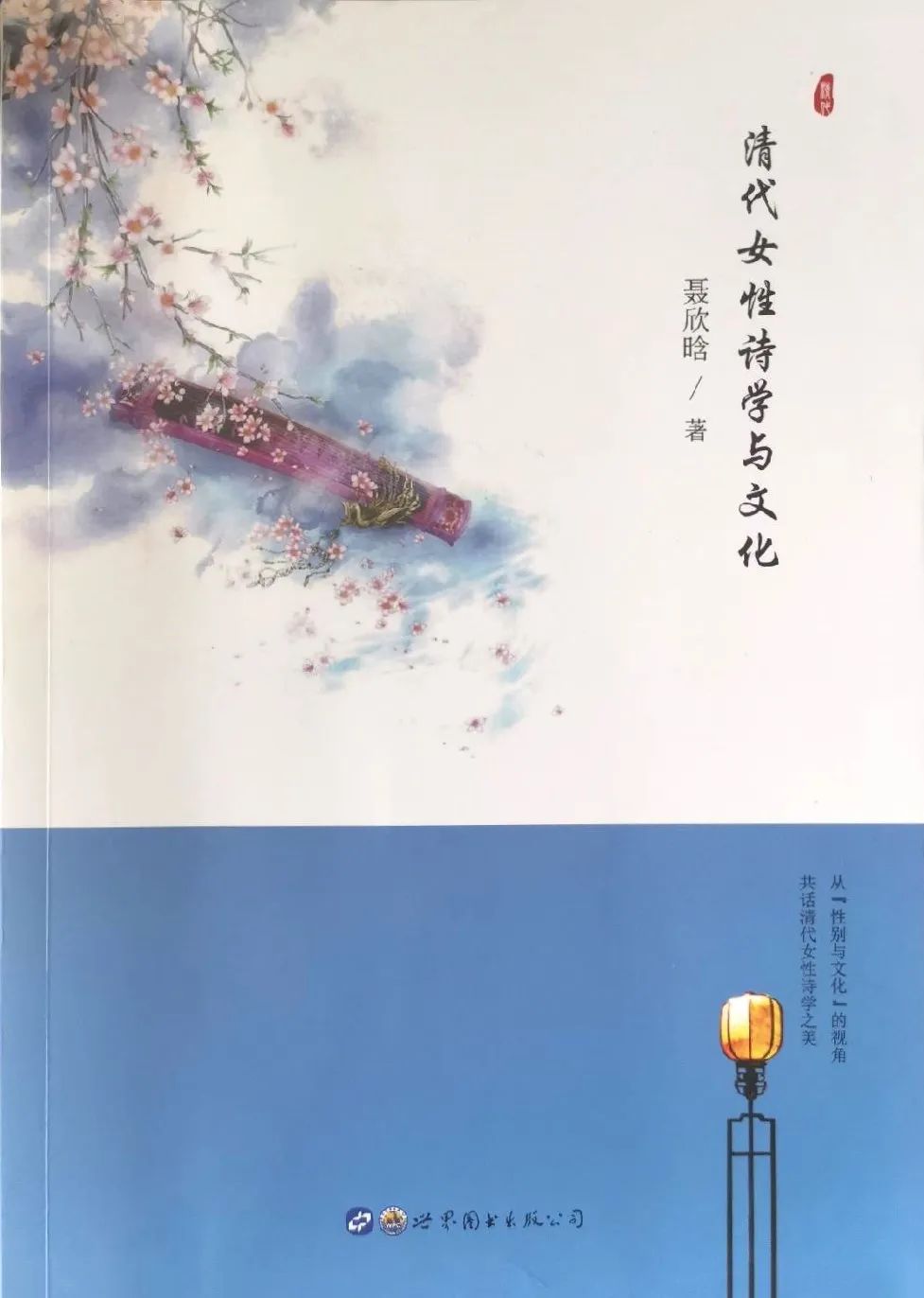
《清代女性诗学与文化》
女性如果嫁到书香家庭,婆媳、姑姊、女眷甚至可以结诗社、吟咏性情,就像《红楼梦》中对海棠社、菊花社的描述。
女性的生存空间大大拓宽,逐渐挣脱闺阃之束缚,在风气开放的江南地区,女子甚至可以拜师求学,在湖畔水滨结社联吟,如“蕉园七子”“清溪吟社”“随园女弟子”等。
幸运的才媛如沈善宝常常随宦游历大江南北,开阔眼界,拓展怀抱,使其诗作得江山之助而提升境界。引人注目的是闺塾师群体的产生,明清之际女诗人黄媛介是闺塾师的杰出代表,她们应运而生,适应需求,不但自己受过良好的诗学教育,而且成为女性诗学教育的传薪者。
尽管中国诗学史上涌现过不少杰出女诗人,但受传统妇学观念的影响,女性的诗学教育异常艰难,它始终面临道德的压力与合法性的困扰。诸多才女事迹与诗学批评经由男性的记载而在文学史上留下印痕,这更加突显女诗人的孤独与沉默。明清时期情况有所改观,女诗人们通过建构诗学理论而寻求话语突破。

《历代妇女著作考》
明清之际的女诗人顾若璞曾感叹:
诗难言哉!女子言诗,抑又不易也。自诗谨非仪,礼严梱外,一语之发,人咸刺讥。既苦无师承,又不能穷山川草木以发其奇宕之思。[4]
女性作诗本受礼教约束,谈诗也不容易,时刻面临闲言碎语的讥讽。女子学诗、言诗之难不但在于缺乏名师的传授,而且在于无法得到山川之盛、草木之荣的兴发感动。乾嘉时期的女诗人恽珠曾为女性诗学正名:
昔孔子删诗,不废闺房之作,后世乡先生每谓“妇人女子职司酒浆缝纫而已”,不知《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妇德之下继以妇言。言固非辞章之谓,要不离乎辞章者近是,则女子学诗,庸何伤乎?[5]
她将辞章置于妇言之中,从孔子删诗中寻求诗学合法性,认为女子学诗无伤大雅。虽然恽珠的诗学思想仍有着鲜明的诗教色彩,但为清代闺秀诗歌的流播拓宽了原本逼仄的舆论空间。道咸时期,女性诗坛领袖沈善宝仍未摆脱女性诗学教育的困扰:
窃思闺秀之学,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盖文士自幼即肄习经史,旁及诗赋,有父兄教诲,师友讨论。闺秀则既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6]

《清代闺秀诗话丛刊》
沈善宝将“女子之学”与“女子之传”相联系,与文士相比,女子学诗境遇艰难,既无父兄的指导,也没有师友的切磋,因此不是绝顶聪慧之人难以写出好诗,更难以流传后世。
女性的境遇因近代女性教育的变革而转变。1884年,英国的爱尔德赛(Marry Ann Aldersey)女士在宁波创办第一所女塾;1898年,第一所自办的中国女学堂开设于上海;1907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更是标志着女性教育的合法性。
此后,女性杂志的创办、女性专栏的开设、女性文学的研究愈来愈盛。在此背景下,谢无量于1916年首次提出“妇女文学史”的概念,他说:
夫男女先天之地位,既无有不同。心智之本体,亦无有不同。则凡百事之才能,女子何遽不若男子。即以文学而论,女子固亦可与男子争胜,然自来文章之盛,女子终不逮于男子者,莫不由境遇之差,有以致之。考诸吾国之历史,惟周代略有女学,则女子文学,较优于余代,此后女学衰废。惟荐绅有力者,或偶教其子女,使有文学之才。要之超奇不群者,盖亦仅矣。[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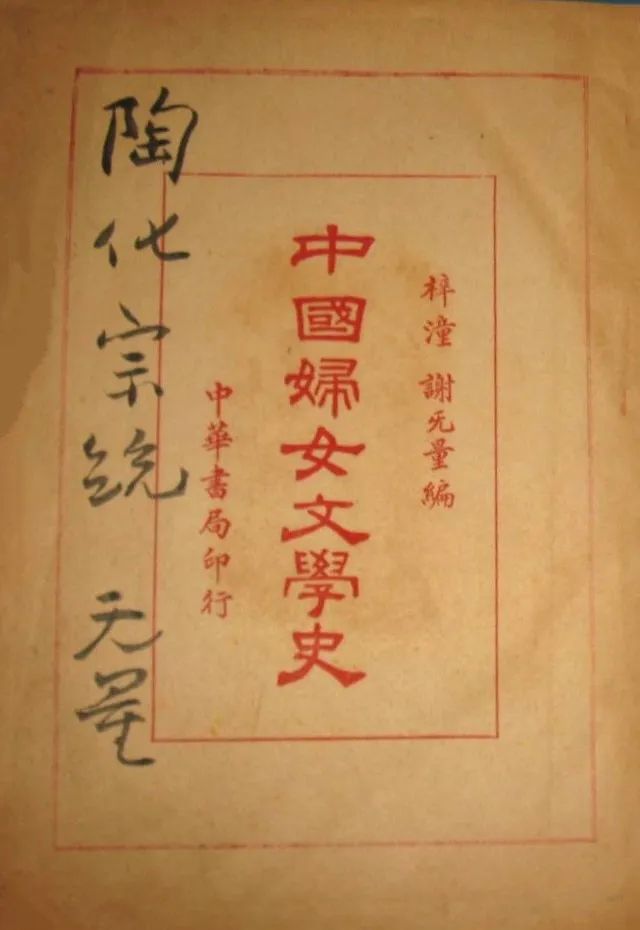
《中国妇女文学史》
此段论述虽于女性教育历史之考察有可议之处,然其拈出女学兴废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他认为男女在文学成就上的差距,均由男女受教育的“境遇之差”导致,确为卓见。自此之后,女性诗学教育的话题逐渐进入学术史的视野,从边缘趋向中心,不断呼应着久已存在的“女子学诗”之思。
二、进入研究的女性诗学教育
女性诗学教育长期以来所受重视程度不够,但其价值仍在部分学者的努力下逐步得以彰显,焕发出独特的光彩。这主要体现在文学史、教育史、妇女史的编纂,与女性文献的整理以及女性个案研究方面。
(一)史学视野下的女性诗学
首先是文学史的编写。
就专史而言,除了前文提及谢无量著作之外,尚有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1927年)《中国妇女文学史纲》(1932年)和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1930年)。
梁著具有鲜明的“影响”意识,注意女性受男性文学家之熏陶,以及女性之间以诗派相称或结社之现象。谭著虽强调女子的天生才华,但也关注到了家庭教育、文士交往等对女性文学的培育作用。这四部书奠定了早期女性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当前由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仍处于理论、方法不断建构的过程,兹待新的著作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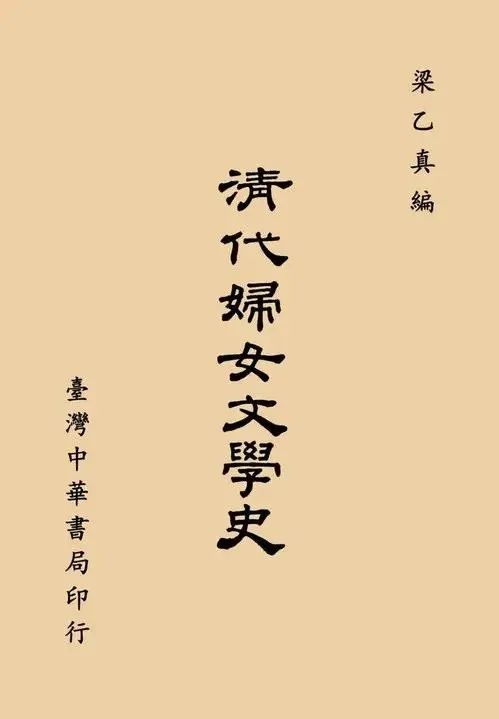
《清代妇女文学史》
就通史而言,早期的研究对李清照关注较多,如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1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年)、林庚《中国文学简史》(1954年)、游国恩《中国文学史》(1963年),唯有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1935)给予其他女性诗人较多篇幅,在两汉、魏晋、唐宋文学等章节后都有女诗人专论。
其后班昭、蔡琰、李冶、薛涛、鱼玄机、朱淑真等陆续进入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如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1998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1999年),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2007年),刘跃进、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2013年)等都曾论及。
但总体而言,由于受“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对女性诗学极盛的明清时期,文学史的编排往往将更多篇幅放在俗文学部分,造成了文学史著作与文学史实的“错位”。
其次是教育史、女性史的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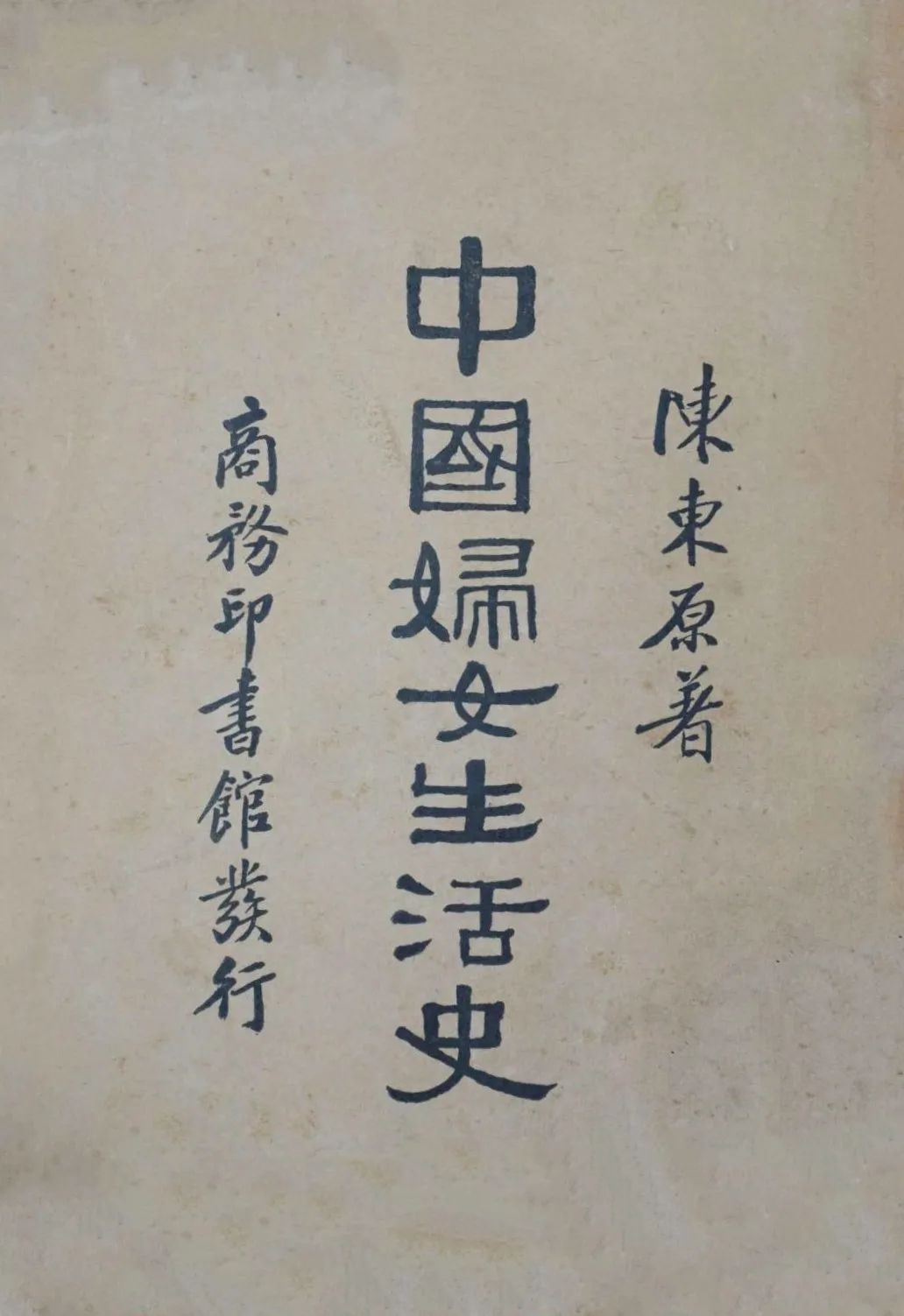
《中国妇女生活史》
陈东原于1928年撰写的《中国妇女生活史》,据其自叙是从女性教育史的研究扩展而来,故对古代女性文学与教育关注颇多[8];曹大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较早论述了诗教的特殊形式及对古代女子的深刻影响[9];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对先秦至20世纪中期的女性教育进行了细致梳理,在明代以前选取了蔡文姬、李清照两位女诗人进行个案研究,明代之后则尤为关注女性所接受的诗词教育[10];陈高华、童芍素主编的《中国妇女通史》关注到女性知识教育中的诗歌文本[11];周洪宇主编的《中国教育活动通史》详细梳理了中国教育发展历程,其中“私学教育”和“家庭教育”部分的论述与女性诗学关系密切[12]。这些史著,为古代女性诗学教育的研究开拓了一片园地。
(二)女性诗学文献的整理
近几十年来大量女性诗学文献的整理,推动女性诗学教育研究。胡文楷1953年初版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广收博采,保存汉魏至近代4000余名女性的文献资料,为女性诗学研究奠定基础。
近年来,大量女性别集、总集、汇编材料与大型丛书不断问世。在别集方面,李清照、朱淑真、柳如是、贺双卿、顾春、屈秉筠、施淑仪、秋瑾、徐自华、吕碧城等女性作者的诗文集得到整理。在总集方面,《唐女诗人集三种》《随园女弟子诗选》《湖南女士诗钞》《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等相继出版。
在汇编材料与大型丛书方面,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丛编》(2008-2022年),方秀洁(Grace Fong)、伊维德(Wilt L.Idema)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2009年),傅瑛主编《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2010年),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2010年),李雷主编《清代闺阁诗集萃编》(2015年),江庆柏、章艳超主编《中国古代女教文献丛刊》(2017年),孙克强、杨传庆主编《历代闺秀词话》(2019年),宋清秀著《清代女性别集叙录初编》(2020年)等出版,为女性诗学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就女性文献的总量而言,目前仍有大量明清女性文献没有进入学术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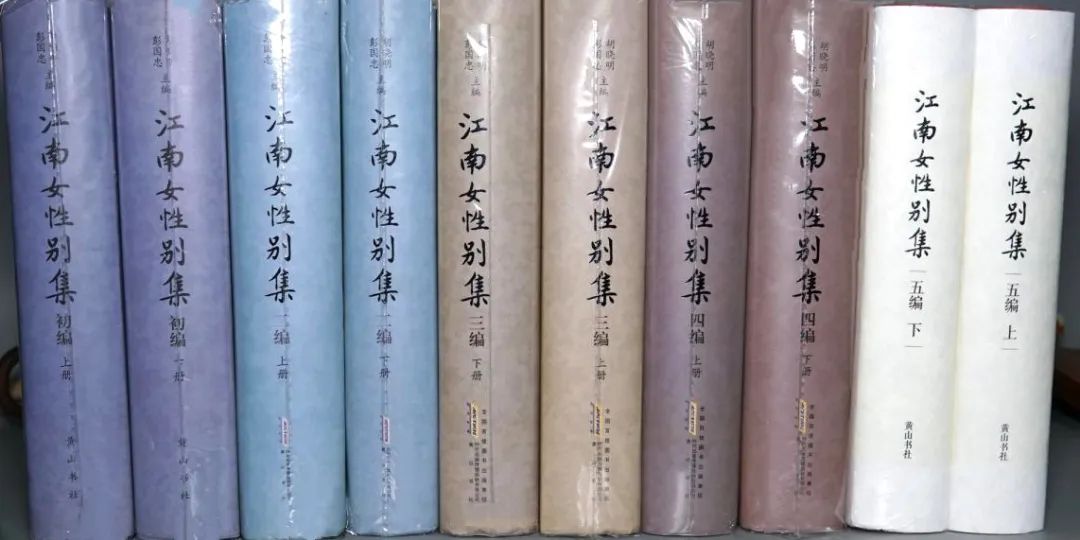
《江南女性别集》
(三)女性诗人的研究
较早对女性诗人进行个案研究的是陈寅恪,其晚年呕心沥血之作《柳如是别传》于1963年竣稿。书中三、四两章通过翔实考证,勾稽出柳如是早年受徐佛、周道登之诗歌教授,与陈子龙、宋征舆、李待问等松江文人交往,及与钱谦益之相伴吟咏的史实。还原出“诗人”柳如是的成长之路,实现陈寅恪自谓“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13]
近年来,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视野的开阔,海内外女性文学、女性教育的学术著作大量涌现。其中曼素恩(Susan Mann)《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2005年)《张门才女》(2015年)、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2005年)、艾朗诺(RonaldEgan)《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2017年)、孟留喜《诗歌之力:袁枚女弟子屈秉筠(1767-1810)》(2020年)等海外著作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呈现古代女性的文学与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是较早专论女性诗人群体的著作,在分析清代女诗人兴盛的原因时,关注到了家庭、师承及结社等方面的教育因素[14];王力坚《清代才媛文学与文化考察》着重从“诗话”与“书简”两个角度分析清代女性参与诗学教育的途径[15];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涵盖了女性诗学教育的制度、内容、活动与效果[16];蒋明宏《明清江南家族教育》着眼于教育的地域性特征,以苏南地区女性为例,探讨了女性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并指出了“文教联姻”在诗学教育中的意义[17];夏晓虹《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着眼于女性启蒙读物,关注到女性文学由“诗”到“歌”的转变。[18]
此外,孙康宜主编《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1998年),张宏生、张雁主编《古代女诗人研究》(2002年),张宏生主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2002年),方秀洁、魏爱莲(EllenWidmer)主编《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2014),张宏生、卓清芬主编《空间与视野: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的新进境》(2022)等论文集,收录大量中外学者关于古代女性研究相关论文,亦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诗学教育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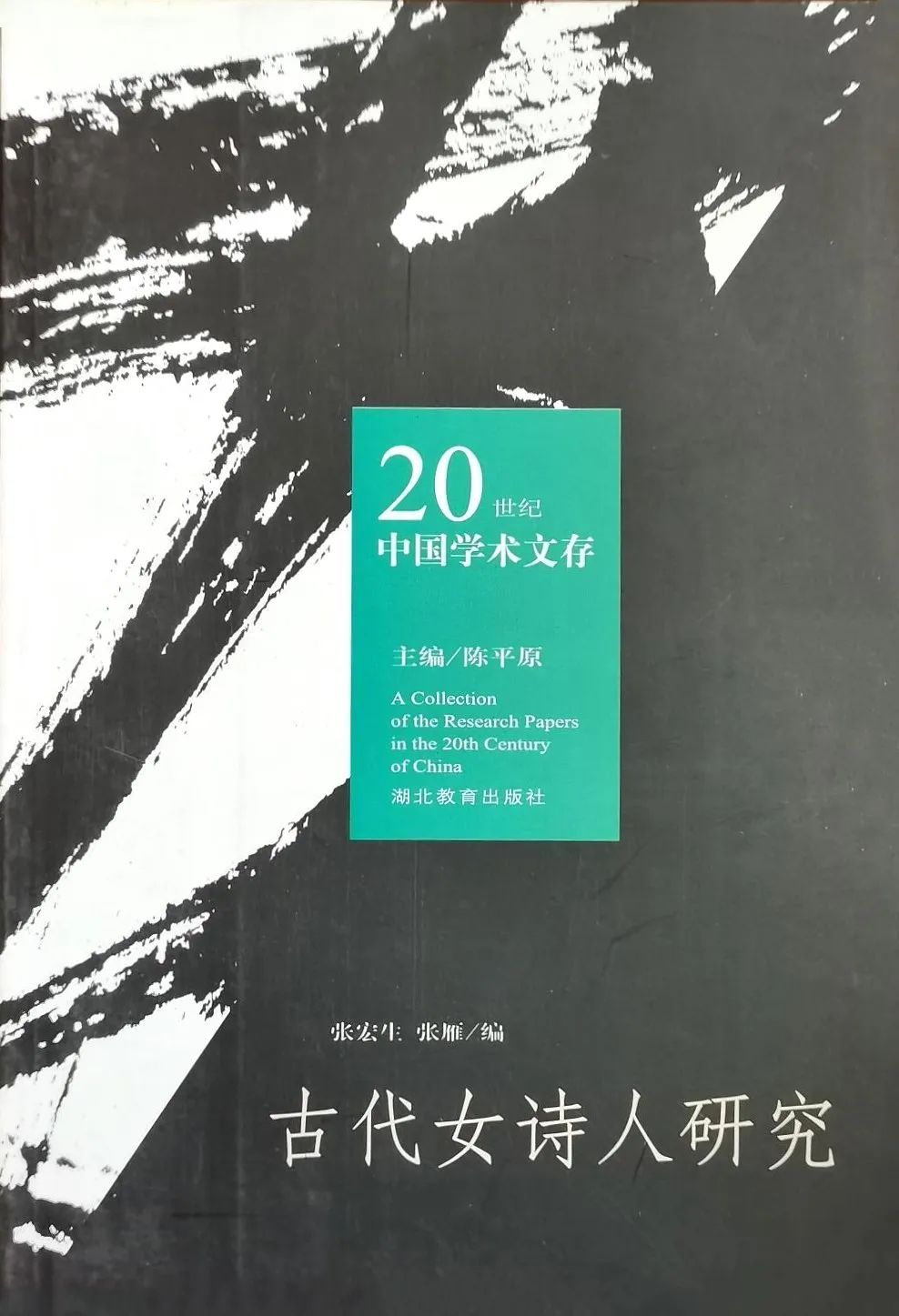
《古代女诗人研究》
总体而言,女性研究的深化不断推动着学界对诗学教育的关注。良好的研究基础与繁荣的研究态势,使得“女性诗学教育”的研究逐渐形成自身的特征与方向。
三、女性诗学教育研究的面向
新世纪以来,一大批学者的积极参与,推动女性诗学教育研究不断在深度和广度上延展。郭延礼、郭英德、王英志、张宏生等老一辈学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涉及到这一问题,宋清秀、郭丽、黄晓丹、娄欣星、聂欣晗等中青年学者专注于此。
就近二十多年来的学术成果来看,可以划分为几个主要议题,即古代女性诗学教育的发展脉络、教育观念的变迁及教育场域的突破。
(一)女性诗学教育的脉络
英国女权思想家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曾将妇女称为“最漫长的革命”[19],其着眼的是女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艰难处境。女性的诗学教育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对其发展历程进行不同阶段的研究,能够反映古代女性在生存境遇、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联系与嬗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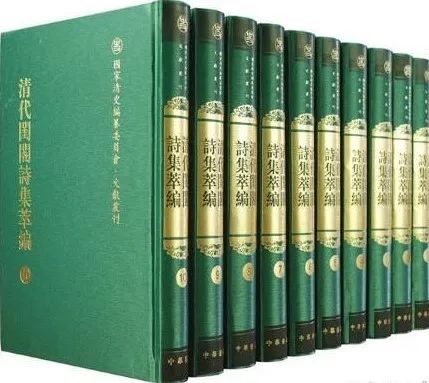
《清代闺阁诗集萃编》
明清学人常将女性诗学的历史追溯至《诗经》,如陶澍《绣余近草序》所言:“余惟妇德不出闺门,诗非所急,然古女子皆娴诗。如《关雎》《鸡鸣》等篇,皆出于宫人之手;而《葛覃》之章则后妃所自作,其诗曰‘言告师氏’,知古女子皆有师长,而犹敬礼焉。”[20]不但认为《诗经》中多有女子之作,而且推断女性亦有师长相教,这一观点也可从先秦两汉女性赋诗、引诗的传统中得到印证。
胡宁《春秋时期女性赋诗、引诗析论》一文,从用诗现象看春秋时期的女性教育,认为女性贵族用诗的前提即为接受诗学教育[21];成倩《汉代<诗经>与女教的互构:现实塑形与理想寄托》一文,注意到汉代贵族女性接受《诗经》教育,并实现女教塑形的情况。[22]
唐宋时期,是诗学史上的高潮,出现了许多备受关注的女诗人。郭丽著作《唐代教育与文学》列有专章对女性教育的内容、成效及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进行了分析[23];李光生《宋代女性的文学教育述论》一文,则对宋代女性接受的文学教育进行考察,提出“诗歌是女性文学教育的重要手段”[24]。
明清女性诗学发展极盛,教育环境也大为宽松,郭英德《明清女子文学启蒙教育述论》、沈沫《“国朝诗学迈前贤”:清代才媛诗歌繁荣的综合性考察》等文章[25],都指出明清女性诗学教育对创作的深刻影响。女子教育在清末的转型,使其教育内容、教学形式等产生剧烈变化,曹晓华《“诗”“歌”传统的消长与晚清新女性的诞生》一文即着眼于此,阐明女性诗学教育的通俗化倾向。[26]
(二)女性诗学教育的观念
著名史学家李伯重于2002年的一篇论文《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中,指出当时妇女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力图从某些外来的理念出发去重新构建历史,而未能从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妇女的过去”[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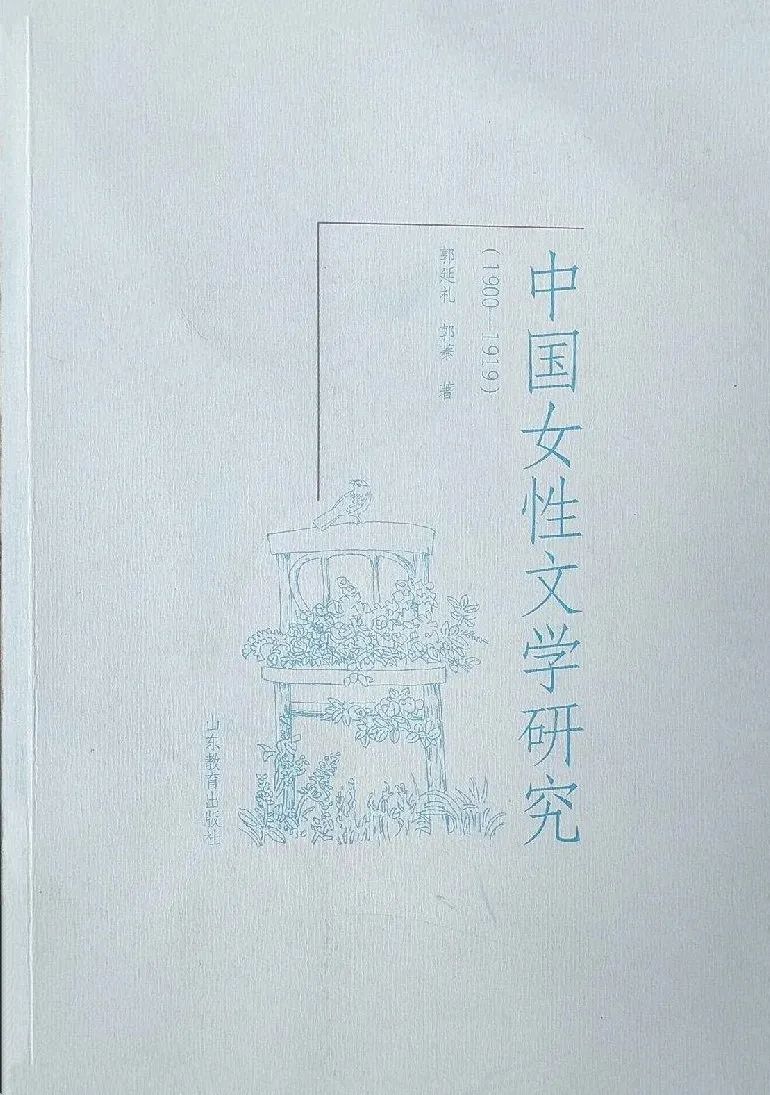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过去二十多年里,此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史料的运用对女性诗学教育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推动了对观念史研究的深入。
古代女子长期以来不但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不宜为诗”“唯酒食缝纫是务”“诗能穷人”等观念的约束,而且缺少如男性参加科举考试而学诗的现实动机。
尽管如此,从大量的诗文中,仍然可以看出女性诗学教育在观念上的变化。李志生指出唐代士人妻女在礼教的缝隙中,寻求更大的诗学空间[28];熊海英以元代女诗人郑允端《肃雝集》为中心,考察江南女性诗学的社会观念与环境[29];李国彤将女教与女学相联系,探讨文学教育尤其是诗词教育在提升女性表达与书写才能上的作用[30];管梓旭揭示了清代女性力图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诠释,突破“酒肉是议”“才德相妨”“内言不出”等观念的约束[31];朱君毅呈现清代女性以诗教为依据对抗“女子不宜为诗”的陈腐观念,为诗歌创作和学习寻求合法性的论争过程[32];蔡德龙关注“诗穷而后工”这一古老理论命题在内涵外延上的突破,并最终生成女子“诗福”说的新现象。[33]这些概念之间的对立、转化、融合,呈现出女性诗学教育在思想上的艰辛开拓。

《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
(三)女性诗学教育的场域
闺门,是古代女性始终面临的一重阻碍。它不仅在体现在空间概念上,也与文化概念绾结在一起,共同形成一个特殊的场域。从《诗经·鄘风·墙有茨》开始,就强调言不出阃,对于女性来说更是如此。
当下许多以闺阁为视角的著作,如李汇群《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伊沛霞(Patricia Ebrey)《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鲍家麟《走出闺阁:中国妇女史研究》等无不说明这一场域的重要性。女性的诗学教育,往往也正是从这里开始。
郭蓁着眼于家庭场域,讨论了母辈、父兄及丈夫在女诗人成长中的担任的角色[34];曾礼军以“戒子诗”为切入点,探讨了在男性角色缺失的情况下,女性作为家庭教育者的特征与意义[35];梅新林、娄欣星将视野从家庭扩展到家族,论及家族在内部联吟与外部交际中为女性诗人提供的教育空间[36];段继红、高剑华针对才女结社拜师的风气进行研究,并分析其背后女性意识的觉醒问题[37];高彦颐聚焦于女性突破场域限制后形成的特殊教育形式与教育身份[38],着重探讨了闺塾师的身份认同问题[39];宋清秀将女性文学空间聚焦于江南特有的“南楼”与“西湖”,讨论了闺秀的生存环境、创作空间、文学传统与传播途径[40]。
随着学界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诗集的阅读、流传、批评亦可被视为古代女子接受诗学的重要文化场域,张宏生、叶晔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41]由内而外的场域转换,不仅改变了教育的角色,也实现了古代女性对“内言不出阃”的突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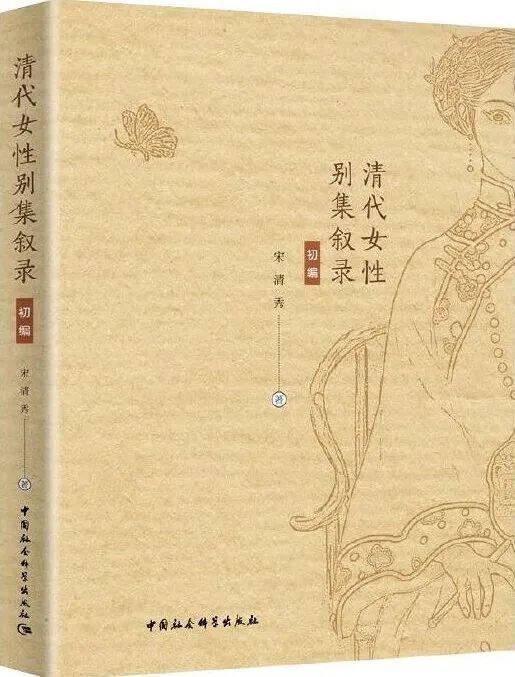
《清代女性别集叙录》
四、女性诗学教育研究的反思
当前的女性诗学教育研究具有多角度、跨学科的特征,不仅涉及文学层面的探讨,而且包含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性别研究等方面的阐述。尽管女性诗学教育研究不断走向成熟,却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其一,研究时段的不均衡。
古代女性诗学教育的研究总体来看较为繁荣,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这固然出于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与文献的充足,但也与学界对早期女性文学教育关注较少不无关系。以往的研究重视“诗学”的教育,强调对文本的考证与阐释,但对诗学的“教育”较为忽视,尤其是对明清以前女性诗人的研究更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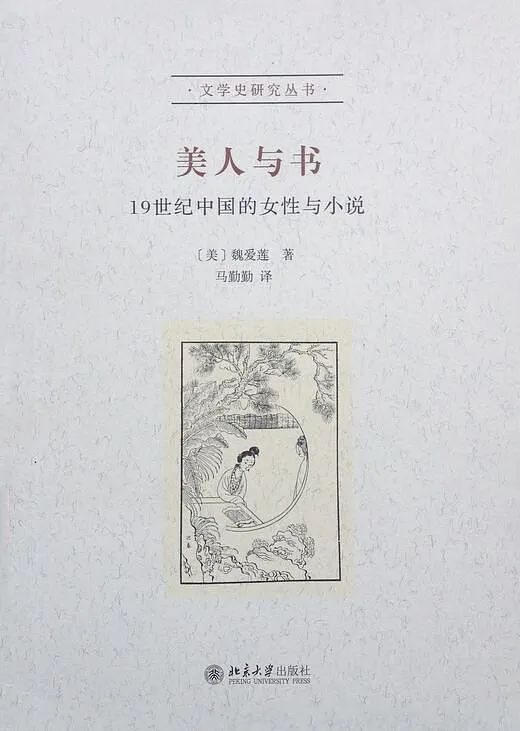
《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
事实上,对早期诗学教育的研究并非无法完成,上文提及的胡宁、郭丽等的研究,即突破以往对女性诗人创作与生平的研究,将其置身于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关注其生活的全过程。
此外,对诗学教育概念的传统理解也限制了学术研究的视野,除家庭教育、私人教育外,阅读、唱和、结社等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教育特征。如郭海文编著《从女性文献史观出发:<奁史>新解》,通过对女性生活类文献的细致爬疏,寻绎出女性所阅读的经部与集部诗学作品,就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42]。
其二,“现代性”的视角局限。
过去的学术研究,常将古代女性简单地置于“受害者”的立场,批判封建社会下女性教育的种种不公,以至于产生强烈的性别对立。
但女性诗学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征和规律,研究者应当用史料说话,置身于她们所处的情境,对其话语作出符合历史语境的解读。曼素恩曾提出应“跳出‘受害者的手稿’这一迫使学者回答妇女如何不受压迫的框架”,这是西方学者长期从事女性研究后的深刻体悟,极具启发意义。
就国内研究而言,尽管在上个世纪末叶舒宪等学者就已提出“性别诗学”[43]的概念,希望建立新的研究框架以取代过去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但传统的研究思维仍有很大的惯性。例如对女性与男性诗人的交往研究,学者大多着眼于袁枚、陈文述与女弟子之间符合“现代性”特征的行为与理论,过于强调其重要性,反而忽略了女性文学与传统诗教文化的共生性,遮蔽了女性对自身伦理困境的艰难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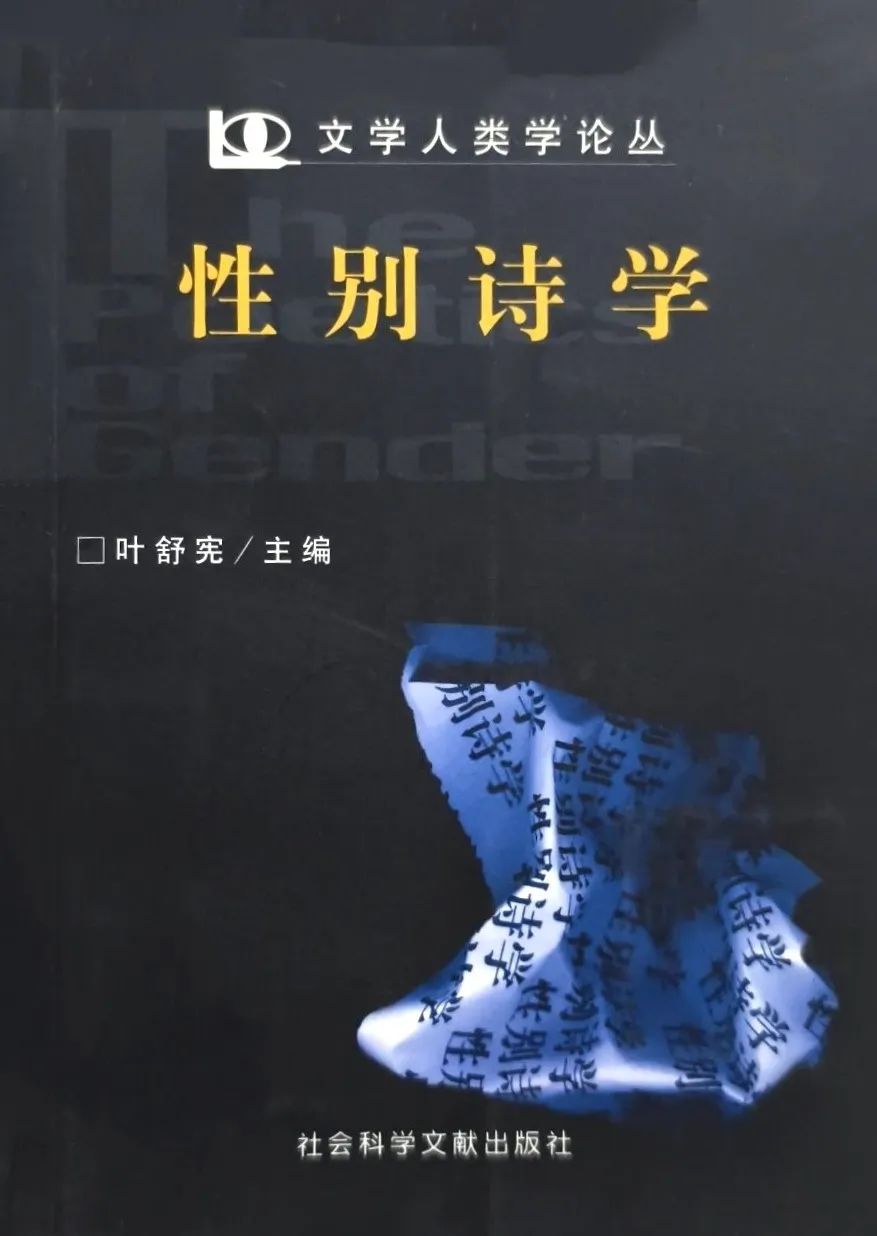
《性别诗学》
其三,“传统”与“当下”的割裂。
女性教育在晚清时期产生巨大转变,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女子教育,研究者多能注意到古代与现代的差异,而较少论及两者的联系。王德威等学者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44]的文学之思,就诗学教育而言,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过去在时代变革情况下出现的“原发性”问题应当得到重新审视。
直到现在,仍有不少研究在追溯女性文学教育传统时,将目光定格在晚清以后,而忽略古代女性这一群体。关景媛针对当下女性群体自我体认的困境,聚焦传统女性教育观的承袭、转向、迷失与复归,提醒我们现在与过去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45]
“女子学诗,庸何伤乎”,在现在看来似乎已经不成问题,如今,女性已不再独立于教育体系之外,而诗词也成为通识教育的必修内容。
但当下的研究还很难回答许多具体的问题,笼统地以群体的境遇去总结历史只会使我们离真相更远。除了被人们所熟知的闺秀诗人,古代社会大量没有条件接受系统诗学教育的女性能否学诗、作诗?男性视角主导下的女性诗学与实际上的女性创作有多远距离?传统的诗学教育在内容和方式上如何符合女性的心理特质,能为当下的性别研究和困境纾解带来怎样的启示?现代教育体系下“诗学教育”是否还应拥有特殊的定位?
博古毕竟为了通今,诸多问题仍然等待我们回答。

《明清女性戏曲作品集》


作者近照
王昊,男,1972年2月出生,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2005)、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2013)。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项,在研教育部项目1项。在《文学遗产》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2部。主持教育部首批“卓越中学语文教师培养改革项目”,完成省级教研项目1项。获“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安徽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一等奖等。
祝福,男,1995年5月出生,西北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在读。
注释:
[1] 孙康宜《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2] 张秀玉《中国古代女性有诗无文之异况及成因》,《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3] 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36页。
[4] 顾若璞《闺晚吟序》,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182页。
[5] 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卷首,清道光十一年(1831)红香馆刻本。
[6] 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一,见王英志《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一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349页。
[7] 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导读》,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0页。
[8]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4页。
[9] 曹大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1] 参见郭松义《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
[12] 周洪宇《中国教育活动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13]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14] 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0年版。
[15] 王力坚《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
[16]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7] 蒋明宏《明清江南家族教育》,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78-88页、203-243页。
[18] 夏晓虹《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190页。
[19] 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见李银河《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精选》,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20] 陶澍《印心石屋文钞》卷十,见陈蒲清《陶澍文集(增订版)》第六册,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121页。
[21] 胡宁《春秋时期女性赋诗、引诗析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22] 成倩《汉代<诗经>与女教的互构:现实塑形与理想寄托》,《唐都学刊》2019年第5期。
[23] 郭丽《唐代教育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5-364页。
[24] 李光生《宋代女性的文学教育述论》,《社会科学论坛》2022年第1期。
[25] 参见郭英德《明清女子文学启蒙教育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沈沫《“国朝诗学迈前贤”: 清代才媛诗歌繁荣的综合性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26] 曹晓华《“诗”“歌”传统的消长与晚清新女性的诞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
[27] 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见李小江主编《历史、史学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1页。
[28] 李志生《“妇人尤不可作诗”:质疑声下的唐代士人妻女作诗》,《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29] 熊海英《女性、市民与晚唐体:元代江南诗人社会之新变——以郑允端<肃雝集>为中心》,《江汉论坛》2021年第11期。
[30] 李国彤《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1] 管梓旭《经典重释:清代女性诗学合法性的理论倡导》,《文艺评论》2015年第2期。
[32] 朱君毅《清代女性诗歌创作论争的诗教依据及深层动因》,《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33] 蔡德龙《“诗穷而后工”说的拓展与“诗福”说的产生》,《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34] 郭蓁《清代女诗人的成长与家庭教育》,《东岳论丛》2008年第5期。
[35] 曾礼军《清代女性戒子诗的母教特征与文学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2期。
[36] 梅新林、娄欣星《论清代常熟屈氏家族女性的文学活动与传播》,《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37] 段继红、高剑华《清代才女结社拜师风气及女性意识的觉醒》,《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8] 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9] 赵崔莉《游学与明清闺塾师的文化身份认同》,《兰州学刊》2019年第12期。
[40] 宋清秀《南楼与西湖:清代闺秀诗栖居的文学空间》,《兰州学刊》2016年第6期。
[41] 参见张宏生《经典确立与创作建构——明清女词人与李清照》,《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期;叶晔《女性词的早期阅读及其历史认识的形成》,《文学遗产》2022年第1期。
[42] 陈丽媛《<文墨门>所见女性学术活动》,见郭海文《从女性文献史观出发:<奁史>新解》,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年版,第218-232页。
[43] 参见叶舒宪《性别诗学》导论部分“性别诗学及其意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44]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16页。
[45] 关景媛《淑女教育的昔与今——女性主义语境下中国传统女性教育合理性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