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来讲京官中的“贰”】
在古代中国官制体系中,“贰”这一称谓主要应用于文官系统。与之相对,于武职岗位而言,通常并无此称。这种文官、武职在称谓使用上的差异,是中国古代官制里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非清代所独有的情况。
在京都,衙署林立。于各类衙署之中,凡官居四品及以上且执掌衙署印信的正职官员,皆被统称为“京堂”或者“部院堂官”。毋庸置疑,能够跻身此列的文职官员,无疑是统治阶层的菁英人物。

据《大清会典》所载,于文官体系中,官阶达正四品及以上的衙门涵盖众多,诸如内阁、六部,此二者于清代行政架构中地位关键;都察院,肩负监察之责;翰林院,乃文化学术之所;詹事府,司职东宫事务;通政使司,承担内外章奏之传递;大理寺,主管刑狱复审;太常寺,掌管祭祀礼乐;光禄寺,负责宫廷膳食;太仆寺,司掌马政等。
在封建王朝的行政架构中,宗人府、内务府、理藩院分别司职皇室事务与少数民族事务,而翰林院、詹事府亦有其特定职能范畴。鉴于其职责属性与国家常规行政管理体系有所差异,故这几类衙门的最高行政长官,并不以“京堂”这一称谓相称。
需予以明确的是,于京城之中,各部院衙门的正职与副职官员,在组织架构及行政关系层面,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联。
以六部体制为例,“堂官”这一称谓涵盖尚书与侍郎。在政治地位及实际权力层面,二者差距并不显著。需指出的是,清代推行满汉官制,在特定情形下,汉尚书所握实权,或逊于满籍的左、右侍郎。基于此状况,皇帝于选拔军机大臣时,亦将侍郎纳入考量范围。

然而,尚书作为名义上的首要官员,自古代起便地位崇高,备受尊崇。明清时期,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与大理寺被纳入“九卿”之列。实际上,“九卿”这一概念较为宽泛,通常用以指代京城各中央部院的正职官员。
在清代诸多文献记载中,常见“交大学士九卿会议”之表述。从实质而言,此乃饬令各部院之堂官共同展开商议。
与之类似,在相关文献中,“卿贰”亦是频繁出现的术语。从概念范畴而言,“卿贰”所涵盖者颇为宽泛,绝非仅限定于六部侍郎、通政司副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及大理寺少卿等职位。实际上,其范畴还囊括了太常寺、鸿胪寺、太仆寺与光禄寺少卿。
卿贰这一称谓,虽表面观之,似未具崇高之气象,然实则与卿并无显著差异。于各衙署体系内,二者皆居堂官之位,分别执掌特定领域之事务。不仅具备径直向君主奏报之权力,且在朝班序列中,亦有各自明确之位次。
由于“卿贰”这一称谓所涵盖范畴较为宽泛,故而仅依据字面意义,难以确切判定其具体品秩。然而,在清代官场语境中,通常惯于将六部侍郎视作正统意义上的“卿贰”。

【再来讲地方官系统中的“贰”】
在各直省官制架构下,总督、巡抚、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以及各道,均施行长官全权负责之制度,并未设置佐贰官员。需说明的是,清初虽曾设有参议、参政、副使等佐贰官职,然其后已予以裁撤。与之不同的是,唯有府、州、县层级设有佐贰官,而厅这一层级同样未设佐贰。
在地方官制体系中,佐贰与属官概念迥异。于明代,佐贰官权势颇重。以知县一职为例,县丞、主簿乃其佐贰官。于地方行政事务之运转进程里,佐贰官作用显著,在诸多层面,知县亦受其掣肘。具体而言,凡遇重大政务,唯有正印官与佐贰官共同签署,相关政令方可生效。
清代时期,佐贰官的地位呈显著下滑态势。在此期间,朝廷从法律维度颁布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限制举措,致使佐贰官逐渐沦为政务清闲、无所事事的虚职部门。

在行政架构中,属官处于正印官的从属层级,作为具体事务的践行者,二者呈现明确的上下级统属关系。从权力架构角度而言,属官并不具备对正印官进行制衡的权力。
依据清代官制体系,知府之佐贰官员分别为同知与通判;知州的佐贰则是州同及州判;至于知县,其佐贰官员乃是县丞与主簿。
与明代相比,清代佐贰官在诸多方面呈现差异,尤以数量设置的变化最为显著。就行政层级而言,府级佐贰官的设置数量虽有变动,但整体幅度相对较小,通常仍会配置佐贰官。具体来说,对于政务繁杂的府,同知与通判均会设置,甚至部分府的此类官职不止一位;而事务较为简易的府,或仅设同知、通判中的一员,或干脆不设。
在全国范围内,州县佐贰官员的配置数量颇为稀少。于一千数百个州县之中,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佐贰官员,其总数仅约三四百人,尚不及正印官数量的五分之一。而且,在同一州县,同时设置两名佐贰官员的情形极为罕见,大多仅设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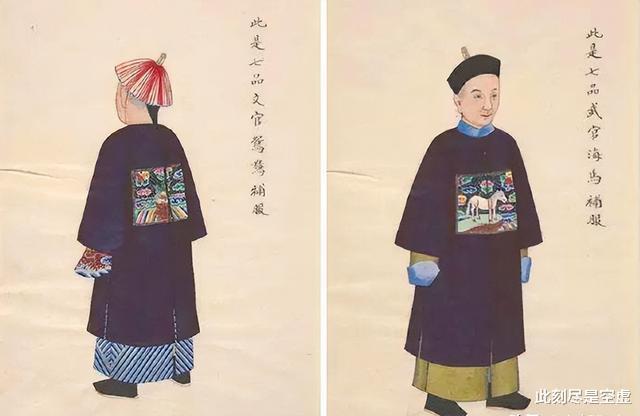
其次,府州县佐贰官的职能出现显著转变。最初,佐贰官主要承担辅佐正印官处理地方各项政务之责。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其职能逐渐细化,转变为分管辖区内特定领域事务,诸如钱粮赋税管理、治安捕盗工作、河工驿站运维以及水利盐政相关事宜等。
从现代行政架构视角类比,清代佐贰官的职权地位发生显著变迁。在过往,其职能近似于当下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副市长、副县长;然而,随着时代演变,其职掌范围逐渐收缩,职能定位亦随之转变,最终与分管特定事务的各局局长相当。
在官场的职官体系中,佐贰官员依据其品级的差异,有着各自特定的别称。具体而言,凡在称谓中含有“贰”字者,所指即为品级仅次正印官的佐贰官员。
在古代行政架构中,府的行政级别相对较高。彼时,知府常被尊称为“府尹”。在此体系下,“贰尹”这一称谓所指的是各府的同知,而通判在府级官员序列中位居第三,故被称作“三尹” 。
在古代行政架构中,州县官员作为直接亲民的基层职官,虽品级相对较低,但因其于地方治理至关重要,故常以特定称谓指代。其中,“堂”为对州县正职官员的一种传统称呼。在此基础上,州同与县丞作为辅助正职的重要佐贰官,被习惯性称作“二堂”;而州判与主簿,因其在政务体系中的层级与职责定位,亦有“三堂”之谓。

开篇提及的墓碑刻有“贰尹”字样,此“贰尹”实则指代某府同知一职。然而,在清代,官员逝后墓碑的镌刻习惯并非如此。同知,于清代官制中属正五品,依散官分类,其对应“奉正大夫”。相较之下,“奉正大夫”在称谓上所体现的品级格调,远高于“贰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