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在公园,看见一个孩子飞奔向前,不出意外的被脚下的什么绊了个狗啃屎,后面的姥姥追了上来,连忙拉起孩子,拍打着灰尘,孩子同样不出意外的大哭起来,姥姥为了平复这场“灾难”,用手用力的打了一下那个绊倒孩子的东西,对着孩子说,这东西太坏了,把宝宝弄疼了。

在《阿Q》正传里面,有两处有趣的段落——
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
在阿Q那颗自负却又幼小天真的心里,凡不和他心意的,就是傻的、没见过世面的,凡女人与男人接触,就是坏的。

美国社会学家约翰·李维·马丁在《领悟方法》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对自己喜欢的人,我们用他们自己找的那些理由来解释其信念;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我们对他们的信念的解释则是“他们不是傻就是坏”。他们的信念需要解释,因为这些人的信念不合情理;我们的信念不需要解释,因为这些人的信念合乎情理。
像“他们不是傻就是坏”这样的论断,在生活中简直多到会让人一度以为这是种有着坚实理论基础的判断方式。

人们常常会说,明明有更好的路,他为什么不走,他是不是傻?显而易见的东西为什么他就是看不到?为什么他这么对我,一定是不怀好意;美帝为什么这样,他们就是太坏了。
如果我们抛开这种表面化的、带有情绪化的论断,深入其后,这些情境究竟表现的是什么内涵呢?
简单来说,就是在两种观点或两种行为(我的和他的)发生冲突,或者可比较的时候,人们如何维护自己的观点,或如何打击对方的观点。
如果说对方傻,潜台词就是,我的观点或我的行为要明显优于你的,但至于说你为什么没选择我这一边,根本的原因就是你傻,你看不出来而已。
说对方坏,潜台词就是,虽然你不傻,你能看出你跟我的观点或行为的对立,但你选择在那边,是因为你的意图就是要跟我作对,哪怕是我的观点或行为是绝对正确的,你都非要站在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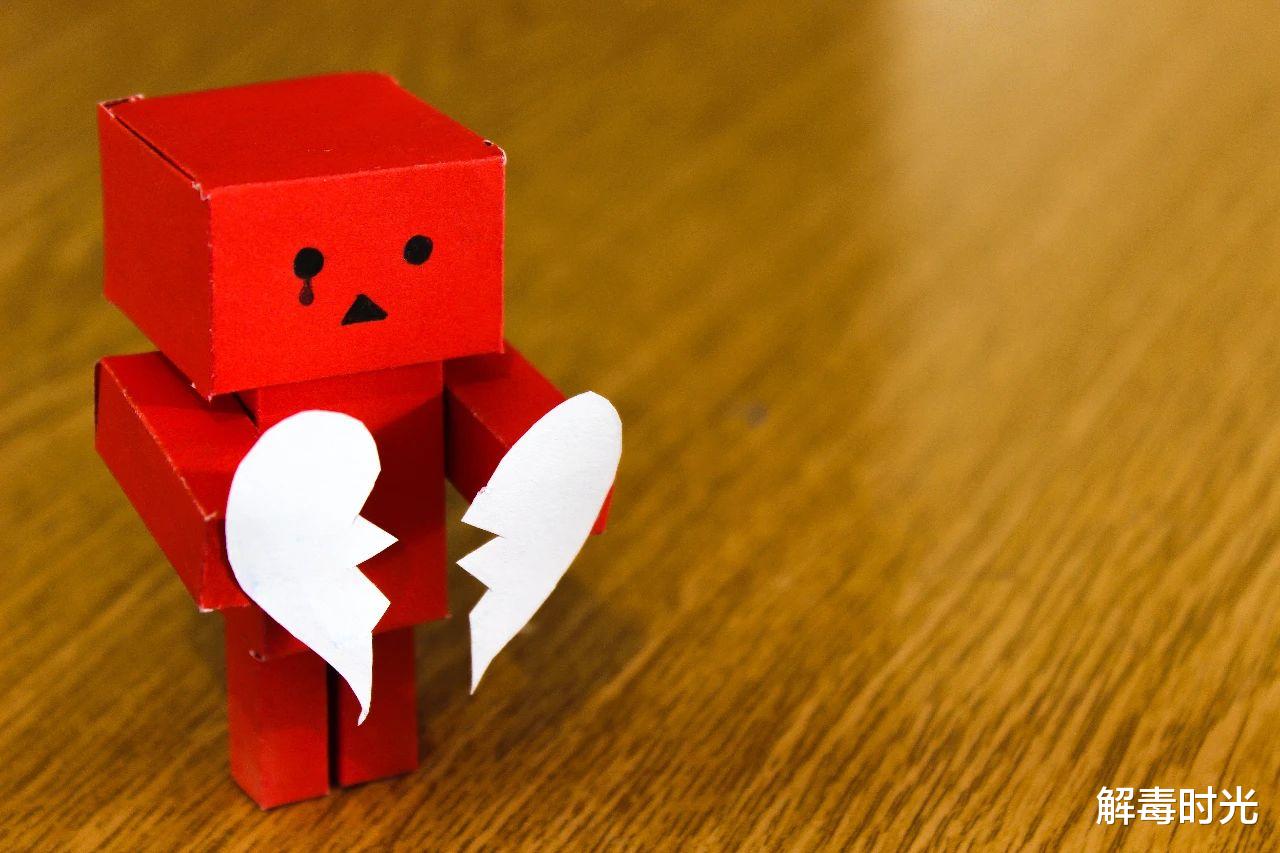
当然,如果比较起来这两种判断,明显说对方坏要比说对方傻更有杀伤力。美国一名律师迈克·戈德温就曾总结出一个论点——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纳粹或法西斯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简直没有例外。
“在线上讨论不断变长的情况下,把用户或其言行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100%)”。乔治·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中也曾提到,法西斯主义的新定义,已然在很多时候变成“任何你所不同意的东西”。过度的使用导致廉价,在将来,每个人都会成为15分钟的希特勒。
那么这种必然会升级为“骂街”式的讨论,究竟是参与讨论者的能力不足,还是另有其更深的原因呢?

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的一小段论述,在排除了参与讨论者的个别特殊情况之后,为我们揭示了人们在不同观念交锋当中可能走的束手无策的境地——
我用物理学里的命题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这样做错了吗?我应该说这样做没有好的根据吗?但这不正是我们所谓“好的根据”吗?
假设我们遇到一群人,他们不认为物理学是个强有力的理由。这种情景该如何想象呢?他们不是向物理学家咨询,而是求教于神谕。(因此我们觉得他们原始落后。)他们求教于神谕,并由神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这是错误吗?——如果这是“错误的”,那我们岂不是以自己语言游戏为基地,来打击他们的语言游戏吗?
我们这样打击,是对还是错呢?当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口号可以用来支持这样的行为。
当两种不可调和的原则遭遇时,一方都会把另一方称为傻瓜和异端。
我说我会“打击”对方——但我不是会告诉他们理由的吗?没错,可理由能一直给下去吗?理由用尽,就只剩下劝导。
原来这个“他们不是傻的就是坏的”,还可以追溯的维特根斯坦。但他所揭示的就已经跳脱出具体的某一些观点的交锋当中,维特根斯坦敏锐的发现了一个可能会带来一些绝望气息的观点——有一些讨论在根本的逻辑层面,不仅是无效的,甚至都是无法进行的。
在分析维特根斯坦的发现之前,可以先借用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争论,来去形象化的感受一下维特根斯坦的抽象思维。

在十六世纪之前,西方的宇宙观都认为宇宙是一个鸡蛋式的封闭空间,地球就像蛋黄稳居宇宙的中心,所有的天体就在蛋清的范围内围绕着地球转动。以托勒密为首的天文学家们以此将地心说发展成一套复杂的天文理论,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天体运动。
但在这个理论中,依然有很多无法解释的天文现象,针对这些无法解释的问题,哥白尼提出了一种新的设想。在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中,哥白尼提出,地球每天自转一周,每年绕太阳公转一周,由此很多已知的观测到的现象便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
又过了几十年,伽利略用最早的天文望远镜,为哥白尼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他揭示了月球上的山峦、木星的卫星,让人类第一次可以放眼地球之外,传统的宇宙观即将崩塌,新的宇宙观跃跃欲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伽利略被教廷指责为异端,并于1615年前往罗马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这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辩护。而他的对手,即代表梵蒂冈起诉伽利略的,是著名的红衣主教贝拉明。
据说当年伽利略请贝拉明用望远镜自己观察,答案贝拉明拒绝了,并声称自己对于宇宙的理解有更好的证据,即《圣经》本身。

对于每一个承袭了伽利略观念的现代人来说,都会直观的嘲笑贝拉明主教的做法。但哲学家罗蒂却对这一段历史发表了如下评论:
可是我们能不能就因此说,红衣主教贝拉明用来反对哥白尼的那些考虑因素(即《圣经》中对宇宙组成的描述)是“不合逻辑的、不科学的”?……(贝拉明)为自己的观点辩护道,我们有独立的(《圣经》上的)证据认为宇宙大致是托勒密式的。他使用的证据是不相干的吗?因而把证据局限于《圣经》就是“不科学的”吗?是什么决定了《圣经》上的内容不是研究宇宙构造的绝佳证据?
对此,罗蒂也并不是在为当年贝拉明的观点进行辩护,作为建构主义的罗蒂,实际上在强调的是贝拉明对自己观点捍卫的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能被看做荒唐的,我们不能用我们所持有的观念体系,来去彻底否认另一种观念体系。

再次回到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中,一切似乎就更加明晰。当物理的观念体系和神谕的观念体系相碰撞时,不考虑其中的具体的情况,在逻辑或者语言的范围内,当物理体系攻击神谕体系“不科学”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根据自己的物理体系,神谕体系“不科学”,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反过来,神谕体系同样也可以说,根据自己的神谕体系,物理体系“不神圣”,这也是无可辩驳的。
这样一来,就陷入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以自己语言游戏为基地,来打击他们的语言游戏”。
不过,维特根斯坦也没有仅仅把这个问题归结到语言上,语言是思维的表象、工具,同时也能够对思维进行塑形。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落脚点,还是在人类思维的模式上,即对因果关系的一种执着与幻象。
我们如果希望说服别人,那么就需要拿出一定的根据,这个根据最好是我们两者都认同的才行。但我只能提出在我的观念体系里,被我认可的根据,我怎么会拿出一个我不认可的根据来说服别人呢?
但问题就出在这,我体系中的根据,在对方的体系中可能有,但也可能找不到。一旦这个根据在对方的观念体系中不存在的话,这种说服就是无果的,其实本质上是不可能完成的。
就好比物理体系说神谕体系,在物理体系的规则下,神谕体系是不对的,这不等于用自己证明自己么?这依然没有证明,在物理体系之外,神谕体系是否不对。除非能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论证这世界除了物理体系之外,再无其他体系。但这等同于在物理体系内,去跟无数个神谕体系进行辩论,依旧是无果的。

这就回到维特根斯坦最终的结论,如果我们需要理由来说服对方,我们就要不断的去追溯理由,“没错,可理由能一直给下去吗?理由用尽,就只剩下劝导”。最终的结果,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体系的争论中,要么就是彼此说对方是傻的、坏的,要么就是劝导,想要用说理来赢得对方的认可,是完全不可能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类争论都是这个宿命,大多数时候,人们需要先取得观念体系的共识之后,再进行讨论,这样的讨论是有效的,也是有价值的。比如在公认的科学体系内,去探讨科学的问题,这有助于科学观念的增长。
但另一方面,还有很大一部分争论,参与者是站在河的两岸,一边都是植物类的,他们以土地为生,于是他们把土地丢向对方,一边都是动物类的,他们以植物为生,他们把植物丢向对方。双方都拿不到自己需要的证据,也就无法彼此说服,这种争论不仅是无效的,更是无价值、无意义的。

那能不能跳出观念体系,从某一种第三方角度来去衡量,比如效果。这种想法的确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但不同观念体系对于效果的认识、预期甚至判断也都是不同的。比如中医和西医,西医能够快速见效,但在中医的体系中,这种见效也是没见效,即治标不治本。所以一旦两个观念体系处在互相排斥的情况,就很难找到能够横跨此岸河边的桥梁,来去论证二者之间的对与错。
也正是由此,在那些无法融合的观念体系发生争执的时候,最终双方只能甩下一句狠话,要么就是你傻,要么就是你坏。虽然结果早已注定,但很多人在这些争论中乐此不疲,看看如今舆论场中那些针对中美关系、两种制度的比较等大放厥词的人,就知道有多人喜欢在一个“非傻即坏”的结论中寻求理性征服的快感了。
与其在这些源自人类思维、理性、语言中的根本性的无法调和的问题上纠结,倒不如在说对方傻和坏的时候,偷偷的看看他们聪明和善良的一面,可能会对自己所在一方的生活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