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这个词在生活中经常会用到,而且往往在一些很重要的语境中发挥作用。人们在争吵中,往往会去讨个说法,“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也会让整个交流陷入一片沉默,那么意义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日常遇到的大多数词语一样,意义也有着诸多的意义。最直接的可能是我们用以交流的语言背后的“意思”。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将词语区分出“能指”和“所指”。能指为语言文字的声音,形象;所指则是语言的意义本身。也就是说人们试图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叫"能指",而语言实际传达出来的东西叫"所指"。
比如,鲁迅这个词,他的能指就是“鲁迅”,而所指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是指向某一个人,那个人叫做“周树人”,有趣的是,周树人本身也是一个能指,它并不是最终的意思,也仅仅不过是一个符号,如果我们说鲁迅和周树人的意义,可能就要用很长一段话,比如?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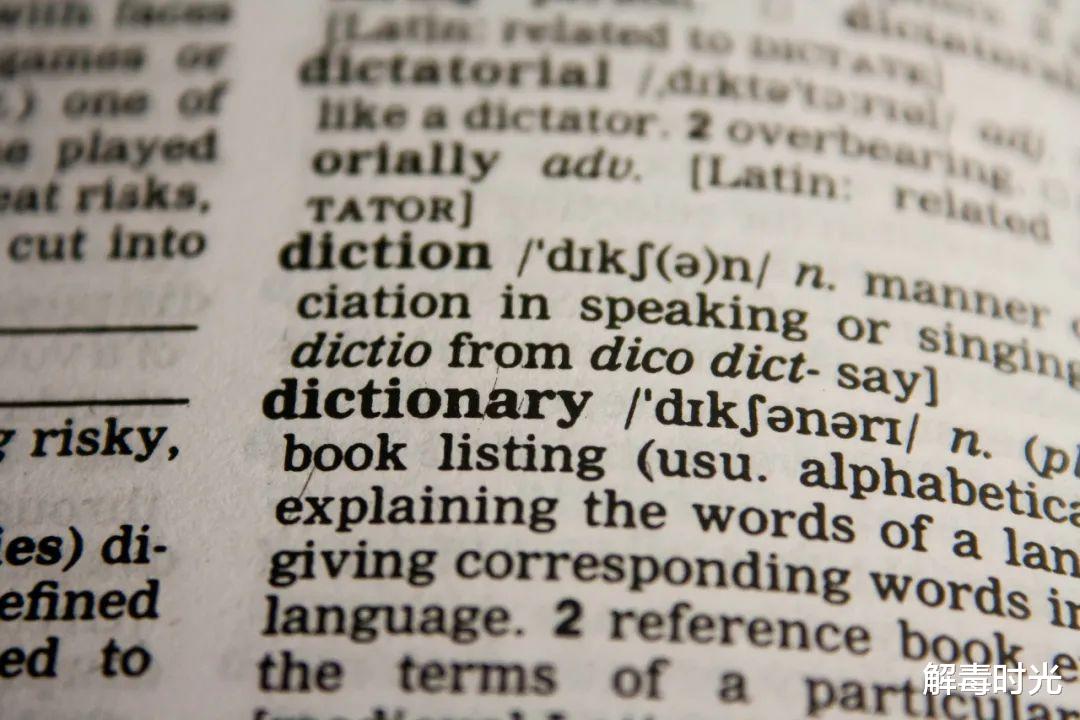
那么由此就引出了关于意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很多时候词语的意义并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一个词语有多种意义,以及多个词语表示一个意义的情况广泛的存在于日常交流中,这也就难免让人去追问“这究竟有什么意义?”
除了基本的词语的意义之外,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隐喻,比如国旗可能就代表着对国家的想象,也能延展出民族主义、爱国情怀等等。更别说将一些基本词汇进行组合后得到的语句,意义就会呈现出级数的增长,最终构成了一种意义的“可能性的空间”。
但神奇的是,大多数时候,人们日常生活是可以沟通的,这也得益于长期的教育以及教育背后那些日积月累的共同文化。文化是一面意义的背景墙,很多的固定用法都烙印在上面,就像“您吃了么”在北京一定不意味着问吃没吃一样。

所以在语言本身来看,意义的意义,就是词句的所指,是可能性构成的意义空间,也同时是所谓的文化背景与语境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但如果意义仅仅是这个意义的话,那还是太容易了,意义在语言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更为模糊的所指。
“你别费劲了,这么做没意义的”,经常还能听到这样的话,这个意义明显就不是词句的意思,而是另有玄机。简单的来看,这里的“意义”有一种“效果”的意思,强调的是做事没有效果,对未来没有影响。但同时也有一种“价值”的意义,就是这个对未来的效果体现在当下就是无价值的。
由此,“意义”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就会产生两个体系,一个是能够让人彼此交流、达成共识的“文化意义体系”,还有一个就是用来做出评判的“价值判断体系”。

这两个体系有着同样的结构,文化意义体系,是个人的意义体系和社会意义体系之间的互动。个人对一个词的理解,部分来自于文化、部分来自于语境、部分来自于个人的经历,而社会对一个词的解释,也不仅仅是在文化当中,也由某个人创造并被大多数人接受而来。
价值判断体系,也同样是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个人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排序,而社会也有一套公允的价值结构,一个人在社会中生存,必然要让二者和谐统一,否则就会出现从形式到内心的矛盾。比如对于不婚的价值判断,个人也许会将不婚视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但社会却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大规模的发生,否则社会就将解体,那么针对不婚的价值冲突就会导致一些深陷这些冲突中的人的生活困境。
不过,文化意义与价值判断又有着结构上的不同。文化意义仿佛是一种弥散的空间,只不过在这个空间中,有一些固定的搭配。但价值判断往往更像一条锁链,价值很多时候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得出结论,从而在人的很多价值体系中,意义就是一个不断咬合的链条,通过比较链条中的先后顺序,人就可以获得对意义更稳定的判断。

其实关于意义的探索,本可以到这就结束,但隐约中,还有一些内容似乎没有被涉及到。即便我们有着稳固的价值判断链条,不过一旦跳出某一个具体的事件、时刻来看对人生总体进行一个评判时,一切价值链条最终都会失效,关于意义的最终极的追问就是“人生有什么意义?”,当然也并不是每个人时时刻刻都会想着这样一个问题,不过这问题却被打散了呈现在人的日常中。
当我们面对崇山峻岭时,油然而生一种崇高的意义感;当我们完成一项工作被别人称赞时的那种满足感;当我们在午夜时分望着窗外细雨发呆的孤独感;当我们仰望星空畅想古今时的那种渺小感。这些统统都会指向我们内心那个深藏着的追问,人为什么而活?

但问题其实也可以反过来看,人为什么而活?不就是为了体验雄峰健岭的崇高、山川河流的壮阔、无垠宇宙的浩瀚、寂静一人的孤寂、众人相谈的满足、自我肯定的成就么?
明明意义都在身旁,怎么还要反复的去追问意义呢?问题可能要回溯到意义开始的地方——语言。
语言不仅是人们用来沟通的工具,也是内心思维的载体,甚至我们可以说语言能够代表绝大多数的思维。人每天脑子里有无数种想法,但大多数都一闪而过,只有将它们用语言的意义之网进行捕捉的时候,才能被固定下来。当我们说我们想到什么的时候,一定是用“语言”说出来的。

思维就好像一个不断流变的场所,而语言则是一种快照技术,能将思维快速的拍下来,并用抽象的概念符号,也就是词语将思想描述出来。就好比我们可以在头脑中想象一棵树,想象一颗巨大的,细节丰富的,随风摇摆的树,但如果想要去用思维操作这棵树的时候,就只能用词语“树”来概括。这时,树就变成了可被思维操作的东西,但也因此失去了大量的细节,以及在这个细节背后带给人的那种摇曳的感觉,甚至是春风拂面的那种感受。
如果说语言的抽象是提取意义的过程,不如说是提取出一些主要的意义,同时也消灭了其他细节的意义。当思维变成语言,一种可以被传递的意义,也就是文初提到的意思或所指就出现了,但同时更多的隐藏在那个思维背后的画面、情绪、感受的细节就消失了。
对此,我不想用简单的理性和感性的对立来描述这种状况。这种过于粗暴的归类对立方法,并没有给分析问题带来建设性。人类为了思考和交流的效率做出了牺牲,忽略掉了经验中的诸多细节,所以在面对一个由语言主导的世界当中,人又期待着复原那些被省略的东西,这可能就是人们在不断追寻“意义”的最终心理根源。

当我们把现实的经验浓缩为词语,我们自然要问词语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把人生浓缩为一个叙事,我们也会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词语的意义,实际上就是那些被我们省略掉的全部,是人的感官能接收到的一切;而人生的意义,也不过是人生所经历的一切,一切个人化的体验,由每一个感动或悲痛的瞬间组成。
海德格尔曾经说,存在的本质就是不隐藏真相。为了交流和思考,我们用语言代替了存在,而语言在抽象的过程中,隐藏了大量的真相。意义,就是对真实世界的还原,就是在语言和思维之上,去追寻人的体验的全部,用经历、反思、探索以及艺术化的呈现方式,将隐藏在语言之后的那些真相释放。

除此之外,意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